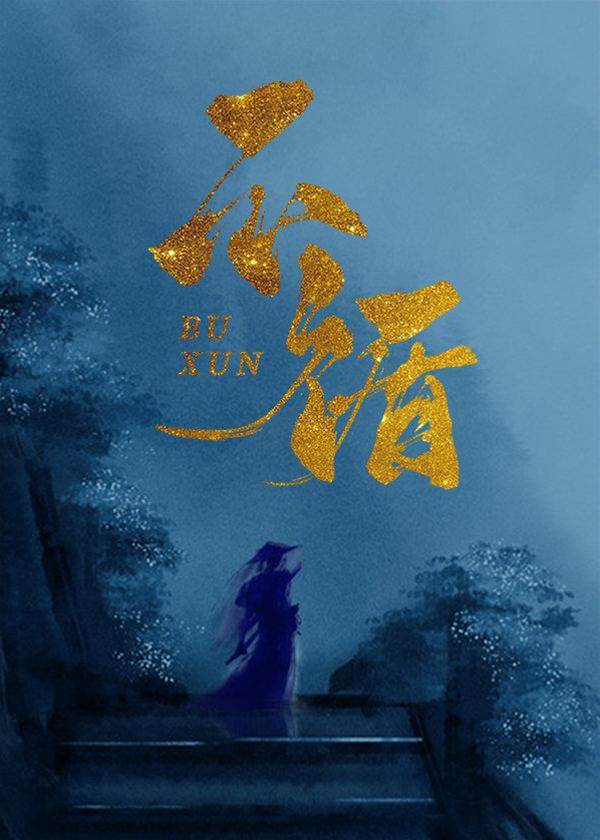《誤入春深》 第九章 真相
太妃聽後一怔,本以為是豫懷稷沒分寸,把媳婦欺負得太狠了,卻沒想過會是這事。皺一皺眉:“不會吧,可是哪裏有誤會?”
宋瑙將畫軸往前一送,繼續哭訴:“這次上山來,我怕山中風大,勸王爺帶幾件外氅,方才在收拾的時候,我發現包袱裏有一幅子畫像!”
“沒準兒是陸秋華塞進來的。”豫懷稷推得幹淨,並詆毀道,“嘖,你們別看這小子長了張無則剛的臉,可能私下好收羅發釵首飾、人出浴圖之類,他報複心又強,誣陷我也不是沒可能的。”
太妃接來畫軸,直往他的肩胛骨揮過去:“胡言語!”恨恨搖頭,“若不是你人高馬大,還會點功夫,就憑你這張,都不知道給人往死裏打多回了!”
太妃人的作分外純,因力道偏大,畫卷的繩扣鬆開了,一端滾向地麵。在展開一半的卷麵上,看見畫中是個布子,十來歲的模樣,渾上下沒一件飾品,娟秀的麵容上有一些獨有的拘謹怯。
當畫軸全部鋪開,太妃前一刻的惱火瞬間凝住了,盯子的眉目一瞧再瞧。
晚來又落起無邊大雪,呼嘯的山風拍打著門框,在嗚咽如訴的風雪裏,太妃遲疑不決地問出一個名字:“皎和?”似是有點迷,“你怎麽有的……”
可能時隔太久,太妃不能十分確信了,但下意識的第一反應已經可以證明一些事。
太妃手紙張,放在燭火下反複打量,一時忘記追問畫像的來源。
宋瑙雙手攥在背後,骨節輕微抖。
一周以前,說起皎和的名號時,還不會有多知覺。
但今時不一樣了,這是隨時會引的火藥,炸開激流之上的虛假平靜。
恍惚間,豫懷稷探手過來,以作遮掩,與扣住十指。
待太妃想到去問,豫懷稷用編好的理由搪塞,堅稱不知,全推到前一撥房客上。
太妃不見得會相信他,但也沒別的法子,隻能安宋瑙,再僧人把畫收起來,看有沒有人回來尋失。送二人下山時,站在金漆佛像的正殿外,笑著與兒子說:“你也總算娶到合意的了,家以後,日子過得還順心嗎?”
停頓一下,又問:“沒有遇到什麽坎兒吧?”
豫懷稷低眸看太妃。不論過去多歲月,的眉目依然大氣,但畢竟是隻走過一朝兩代,能一力穩住六宮安寧,備曆任君主敬重的人,自有種後天修煉的靈敏嗅覺。
也許在剛見到那張小像,會一時糊塗,但不會一直糊塗。
“順。”豫懷稷笑一笑,“您兒媳這麽乖,生起氣來也塌塌的,兒子能不順嗎?”
太妃側頭安靜地看他一會兒,才抬起視線,歎息一聲:“是啊。”向漫天雪舞,“那就……護好了。”
平靜地遠,忽然說道:“人生苦短,所能擁有的皆有限額,骨親,知己至,錯過一個一個。”眸中有點悲涼,“可一定要,護好咯。”
豫懷稷滯了一瞬。
他沒有回話,隻淡淡撤後一步遠,彎腰弓背,向深深一拜。
宋瑙收好包袱,遠遠從偏殿走過來,太妃目送他們離開山寺,直到人影被雪霧吞滅。
太妃想起有一年,豫懷稷在西北戰場挨了毒箭,險些斷去一條胳膊,但在往來信件裏,他用左手回信,一筆一畫,依舊穩重力勻。
信中寫道:前線戰事順利,糧草補給充足,預計來年開春,即可凱旋。
的大兒子,平日雖渾言渾語慣了,十分欠揍,但沒逢大事,從來是報喜不報憂。
遠比他父皇要有擔當,重義。
大雪中的下山路坑窪陡峭,幸而寺廟建得不高,他們並沒走很久。
或許是在風雪中行路,需要分外專注,兩人一路無話,隻有手始終握在一起。
在離王府百米遠、積雪覆蓋的長街上約傳出踏馬疾奔的響聲,由遠及近,正飛速朝他們近。豫懷稷略一皺眉,馬匹轉瞬衝過來,隨之看見馬背上的戚歲,他理應在王府留守,眼下卻一飛雪向前疾馳。
離得近了,發現王府的馬車,他拉韁停住,接著翻落馬。
宋瑙掀開車簾,雪灌進來,接著是豫懷稷的問詢聲:“找我來的?”
“是。”戚歲在馬下回話,“宋世子到訪,已候在府門外,著急的,要見王爺。”
宋瑙聞言一愣:“堂哥?見誰?”以為自己聽錯了,繼續問,“不是見我嗎?”
豫懷稷轉臉瞥一瞥:“聽夫人口氣,是有點憾?”
冷風裏飄來一抹酸醋味兒,宋瑙無奈極了,正強調:“我在說正經的,這王府裏跟堂哥有的,不該是我嗎?”
“不該。”豫懷稷想也未想,便冷冷反駁道,“沒聽過嗎,嫁出去的堂妹如潑出去的水,跟他有一文錢關係嗎?”
宋瑙來氣了,大膽頂撞他:“王爺自個兒的良心,民間諺語是這麽用的嗎!”
“我拒絕。”哪知他繼續冷酷不改,散漫地辯說,“我是武夫,能識兩個字就不錯了,我沒文化的。”
宋瑙心頭大怒,他寫得這麽一手遒勁好字,居然有臉裝無知。
在看來,這人不是沒學問,他是真無賴。
戚歲躲在一旁,他沒想到出去一趟,大雪天的有幸撞見主子們當街調,隻可惜還沒有上手幹些什麽,他家爺已放下車簾,開始趕車了。
王府養的馬全是軍馬出,撒開蹄子一個起步,很快便抵達府邸正門。
宋晏林站在門匾下。他沒有打傘,似乎是等久了,雖頭頂上方有門簷遮擋,但斜飛的雪仍沾滿了墨發肩頭,部分融化的雪水浸他的素白衫。
宋瑙坐車裏見時,眉心不由得一蹙。
前頭鬥歸鬥,但跟豫懷稷都明白,宋晏林本應人在河。
雪夜除夕,不恰當的時間,出現在不恰當的地點,他的突然造訪,必有什麽幺蛾子。
豫懷稷先躍下車頭,向後方的戚歲責問:“這麽大的雪,怎麽不讓宋世子去府中等?”
戚歲嘟囔:“屬下極力勸說過,就差生拖拽了,是宋世子不肯。”
他們說話時,宋晏林已衝到車前,不知是否是挨凍的緣故,他麵比起在皇後壽誕那時又難看許多,慘白中夾雜點淡淡的鐵青。他的確像有急茬兒的樣子,但礙於戚歲在場,他強忍住沒立馬說出口。
豫懷稷看在眼裏,先掀開車簾,扶宋瑙下來。他取出裏麵的紙傘,單手撐開斜在宋瑙頭頂,這才稍一擺手,戚歲便趕上馬車往後門去。
宋瑙前麵坐在車裏,飛快地想到數十種宋晏林此行的理由,甚至於他是否因歲數漲長,再靠掙錢難免力乏,繼而產生從良之心,卻遭遇到什麽難以啟齒的阻力。
可剛一站穩,足下半尺厚的雪還沒踩瓷實,就聽宋晏林以近乎哀求的語氣說:
“王爺,你救一救阿宿,如今隻有你能救了。”
那一秒,宋瑙幾乎以為出現幻聽,怕是日思夜想的,才會聽什麽都是那個人。
但迷惘地仰起臉,隔了匝匝的雪簾,見豫懷稷眼中一抹暈開的冷漠殺意。
仿佛對麵的不再是以往的宋家世子,或者潛在敵,而是臣賊子,當誅之。
豫懷稷盯住他,問:“人在哪裏?”
“在皇宮。”宋晏林回他,眼尾染似的紅,“被皇帝派出的影衛給抓走了。”
宋瑙瞬間如墜冰窖,哪怕前麵聽見太妃吐出皎和的名號,至早有準備,都不像這一刻仿佛無數冰刃在朝臉上。
“宋晏林。”宋瑙隨他闖河、賭茶行歌的那麽些年,今天還是第一回連名帶姓地喊他。
即便因他一時疏忽,摔過一個狗吃屎,在中央街上出盡洋相,也沒這麽憤怒過。
咬牙關,一字一句地問:“你可知道,你說的是什麽?”
對話過一個來回,宋晏林也終於平靜些:“看來,不僅我知道。”他漸漸反應過來,“王爺同王妃也認識阿宿?”
宋晏林笑起來,微彎的雙眸仍是無雙豔麗,可眼底猩紅,橫生道道紋,如同泣。
豫懷稷下外袍,裹宋瑙肩膀,摟住向前走。
“進去說。”
他斂起殺心,麵上沒什麽表。
他們邁進門檻,宋晏林隨其後。
風雪之下,朱漆大門緩緩合起,金釘門環在風中搖擺輕。
宋晏林坐在鐵梨木圈椅上,經室的熏爐一蒸,渾不住向下淌雪水。
盡管屋炭火旺極,熱煙自集的爐孔往外飄散,但他涼的料在上,依然有冷氣朝骨裏鑽。
而小心眼如豫懷稷,沒擰下他的腦袋已經算作仁慈的了,自不會再提供幹燥服與他。不過宋晏林也不在意,他拎起矮幾上的茶壺,腕子細微打戰,自斟半杯冷茶。
猜你喜歡
-
連載771 章

心有瑤光楚君意
陸瑤重生後,有兩個心願,一是護陸家無虞,二是暗中相助上一世虧欠了的楚王。 一不小心竟成了楚王妃,洞房花燭夜,楚王問小嬌妻:“有多愛我?” 陸瑤諂媚:“活一天,愛一天。” 楚王搖頭:“愛一天,活一天。” 陸瑤:“……” 你家有皇位要繼承,你說什麼都對。 婚前的陸瑤,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未來的皇帝老子楚王。 婚前的楚王,奸臣邪佞說殺就殺,皇帝老爹說懟就懟。 婚後的楚王扒著門縫低喊:“瑤瑤開門,你是我的小心肝!” 眾大臣:臉呢? 楚王:本王要臉?不存在的!
114.1萬字8 7666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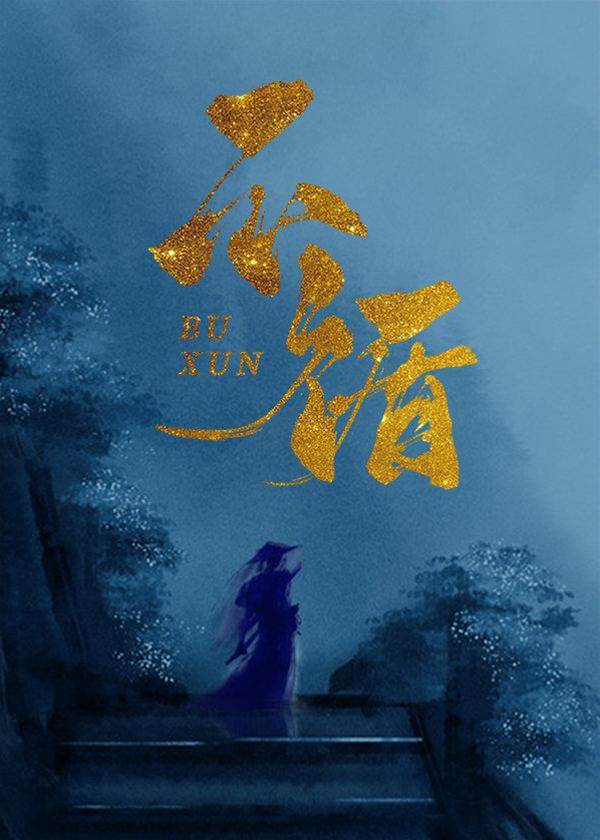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457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