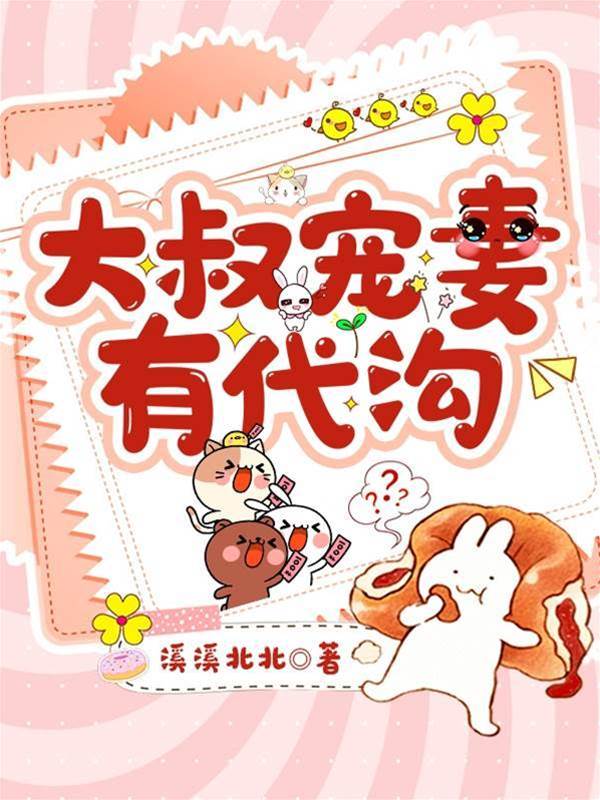《你被開除了!》 第40章第四十章
白端端並不知曉戴琴那邊發生的小曲,隻是覺得戴琴收拾完東西再出現的時候, 雖然臉看起來還是蒼白憔悴, 但眼睛卻變得不一樣了,怎麼形容呢, 彷彿看起來被注了活力,明明還是那個戴琴,卻又好像已經不是那個戴琴了。
不過白端端沒有多想, 把戴琴送回了家,這才又蹭著季臨的車往律所回去。剛才談判也好,談判後也好, 白端端都說了太多話, 現在隻覺得一句話也不想再說, 而另一邊,季臨顯然也沒有搭話的興緻。他的外表相當鎮定, 然而心卻正相反, 季臨覺得有點心煩意,白端端剛才的模樣在他腦海裡揮之不去, 的話也像烙印一樣的印在他心裡。
自己為改變了?這不可能。季臨幾乎是想也沒想就在心否認了白端端的這個說法。自己會為改變?嗬, 自己是絕對不會浪費時間去說這些廢話的,剛纔不過是一時鬼迷心竅而已。白端端不過是個有毒的下屬,自己絕對沒有對特殊化, 也絕對不會對特殊化……
季臨的心裡波濤洶湧,看向白端端的眼神晴不定,而車上這另外一個始作俑者卻毫不自知。
上車後, 白端端便和薛雯彙報了這次的「戰績」,然後兩個人便聊了聊別的,季臨突然急剎車的時候,白端端正和薛雯聊到最新的影視八卦。
「哎!」
這剎車實在太急太突兀,白端端一時不查,不僅手機飛了出去,額頭也差點磕到,抬起頭,這才發現季臨車前不知道什麼時候冒出了個人來。
要是單純突然冒出來的行人倒也罷了,至結果是有驚無險地避開了,然而對麵那人看向季臨怨毒的目,還有他手裡提著的棒球,都讓他的出現顯得並不巧合,而彷彿為了驗證這人的出現是有預謀的,很快,路的盡頭裡出現了十來個都戴著鴨舌帽和口罩的男人,一下子把季臨的車給包抄了起來。
通往盛臨所在的寫字樓需要穿過一條單行的小路,而如今季臨的車好死不死便是行駛到這條路上,一旦被這些男人包抄,本沒有其餘路可走,而這麼十來個壯年男人,季臨總不能直接開車碾過去。
白端端看了一眼季臨:「打劫的還是尋仇的?」
季臨微微皺著眉:「尋仇。」他言簡意賅地解釋道,「是我半年前接的一個案子的對方當事人,這人騙取加班工資,被我開了,也沒訛到經濟補償金,因為壞了口碑,在業大概是找不到工作,往律所給我寄了幾次恐嚇信和骨灰盒了。至於其他人,大概是他找來的烏合之眾。」
季臨說完,立刻報了警,隻是這裡位置有些偏僻,等警察來恐怕也要有段時間,而車外的十幾個男人已經開始朝白端端和季臨聚集了……
而為首的那個被開員工,也終於兇惡地喊了起來:「季臨,你出來!和我單挑!你要打贏我了,我胡老三願賭服輸,以後再也不糾纏你,但你要輸了,你給我跪下磕頭!」
這男人大約還喝了酒,此刻一臉醉態,聲音也帶了酒上頭的,罵罵咧咧道:「就因為你,害得我丟了工作,還沒拿到賠償!結果老婆也跑了,現在隻能做點臨工,老子就是爭一口氣,你給我跪下,從我-下鑽一遍,再把欠我的補償款賠給我,我就放過你!否則你這個頭烏再不出來,我就砸你的車!」
那男人紅了眼睛:「你下來!你放心!我胡老三知道江湖規矩,帶這麼多兄弟來隻是為了堵住你,你下來,我和你單挑,他們絕不手,但是你如果想跑,那別怪我和兄弟不留!」
……
這種時候,看起來勢必得有個人下車涉,直麵這慘淡的人生了。
白端端扭頭看向了季臨,卻沒想到,季臨抿了抿,也正看向了白端端。
「?」
外麵的男人踉踉蹌蹌走得離車更近了,看樣子這醉漢不理智之下真的要砸車了……
季臨抬了抬下,惜字如金道:「行了,你出去吧。」
「我出去???」白端端愣了愣,才反應過來,道,「不要了吧季臨,雖然他確實是沖著你來的,你覺得冤有頭債有主要找的是你,讓我下去趕走開遠離這個糾紛,但這男人看起來也不理智,我萬一下去了,他覺得我和你關係匪淺,也未必就放過我啊!」
「你坐在我的副駕上,他都失業大半年了,窮瘋心了,還喝得腦子不清醒,當然也不會放過你。」
白端端疑了:「那你我下去是?」
「你下去涉。」
季臨拍了拍白端端的肩膀,然後側開臉道:「表現和證明你自己的時刻到了。」
「你讓我用法律專業知識和他們通嗎?」白端端茫然道,「可我刑法和治安管理罰條例學的不好啊,而且要論專業能力,也是你比較強啊?」
季臨沉道:「我說的是你另一種專業能力。」他看了眼白端端,「你不是很能打嗎?上次見你打個醉漢打得不費吹灰之力,所以這種時候,不應該用你的專業能力,保護你的上司嗎?」
季臨一臉理所當然道,「他說了要單挑,你作為我的員工,我派你去和他單挑。」他說完,毫不真誠地對白端端道,「上吧,白端端,我相信你,加油。」
「……」
白端端簡直震驚到快失語了,瞪著季臨:「你認真的?」看了眼車外的醉漢,「這種程度對我確實沒什麼難度,但是季臨,需要我提醒你嗎?我好歹是個的。」
這男人他媽的懂什麼紳士風度,什麼做男人應當承擔的責任嗎?何況這本就是他自己惹出來的事,竟然這種關鍵時刻自己上?白端端簡直驚呆了,無法想象,沒多久前,自己竟然還覺得季臨溫?宛若神祇?讓人悸?媽的這就是個24K純種的狗男人啊。自己是被他下了毒才戴了那麼厚的濾鏡吧?白端端覺得自己真的該去看一看眼科了。
怒盯著季臨,都快氣劈叉了:「這種時候了,季臨,你好意思讓的擋在前麵?你還是男人嗎?!」
以為自己這番怒斥即便不能喚醒眼前狗男人的良知,也最起碼能讓他到愧,然而季臨卻微笑著對答如流——
「每個功人後都需要有個默默的男人,你可以把我理解站在你後的男人。」
「……」
見過臉皮厚的,沒見過臉皮這麼厚的……
白端端簡直氣得不行,然而車外那群男人還包圍著車,那醉漢也還在囂,這麼下去不是個辦法,最節省時間的辦法確實是自己下車把這個醉漢打服。
隻是這過程裡,季臨這狗男人竟然這麼鎮定!
然而白端端或許本想不到,此刻坐在駕駛位上外表鎮定的季臨,心其實本沒那麼鎮定,他的心裡煩躁異常。
季臨是故意讓白端端下車的。
他覺得自己最近對白端端的關注有點多的不正常了,他不應該這麼關注,也不應該總是幫解圍撐腰,這種覺很陌生,季臨從沒經歷過,以往他有一套完全的待人接準則,能讓他和他的錢都過的很好,然而最近在白端端上,他卻發現自己的原則在一點一點的改變。
雖然說不清也不願想是什麼原因,但這不是個好徵兆。
這太花錢了,也太不經濟了。
自己得對白端端更冷酷一點,對更保持一點距離,隻是這人太有毒了,季臨有時候完全控製不住朝靠近,那麼就隻能讓離自己遠一點了。
這次讓白端端下車,幾乎是季臨故意為之,他想,這樣總能反自己離自己遠點了。而自己還能這麼冷酷地對待,足以證明自己對沒什麼特別之,本不存在說的什麼狗屁改變。
照理來說這樣想來,季臨此刻應該釋然,然而沒有,他除了煩躁就是煩躁。冥冥之中有一種預,他覺得要遭。
而這種預在看到白端端瞪了自己兩眼然後一隻手向車門時候,終於了真。
*****
白端端手想要拉開車門,然而就在這一刻,駕駛位上一直鎮定沉默的季臨突然猛地側過,作近乎有些魯地拽回了白端端的手。
白端端皺了皺眉,看向了季臨,想問他又怎麼了,然而季臨卻連正眼都沒看,他微微轉開了頭,目則落在了白端端畔。
都讓自己去打架了,還不正眼看自己,這也太沒禮貌了吧!這男人真的太狗了!
然而季臨此刻不僅很沒禮貌,連聲音也有些煩躁不耐:「行了,你別去了,好好坐在車上。」
他甩下這句話,看起來有些氣呼呼的,然後轉開啟自己那側的車門,自己下車了,臨下車前才終於看了白端端一眼,狠狠瞪了一下。
猜你喜歡
-
連載958 章
俏皮甜妻娶進門
被送給活死人做沖喜小妻子的夏安然,隻想裝蠢賣醜,熬死老公後跑路。可是,躺在床上的活死人老公,怎麼轉眼變成了冷酷毒辣、心狠手辣的的商業帝王?最最最關鍵的是……她之前才一不小心、趁火打劫,將他吃乾抹淨了!!!肚子裡揣著的那顆圓滾滾種子,就是她犯下滔天罪孽的鐵證!夏安然抱著肚子,卑微的在線求救:現在跑路,還來得及嗎?淩墨拖著試圖帶球跑的小妻子回家,一邊親,一邊逼她再生幾個崽崽……
88萬字8 61175 -
連載768 章

婚婚欲睡:陸少夫人要離婚
童心暖暗戀陸深多年,最幸福的事就是嫁給陸深,結果……新婚第一天,陸深的白月光帶著孩子回來了,新婚第二天,她的父親死了,自己被逼流產,新婚第三天,她簽下了離婚協議,原來陸深從未愛過她,所謂的深情都是她自以為是而已。
170.3萬字8 38385 -
完結5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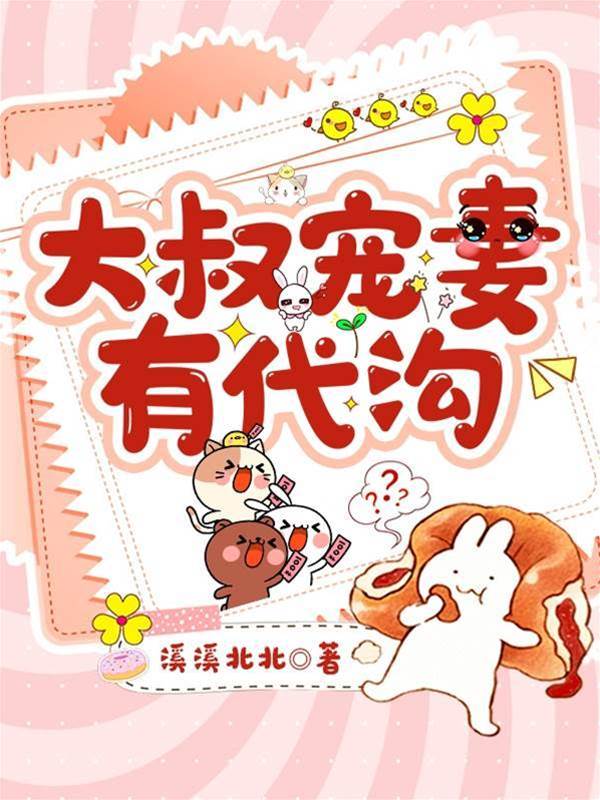
大叔寵妻有代溝
等了整整十年,心愛的女子終于長大。略施小計民政局領證結婚,開啟了寵妻之路。一路走下,解決了不少的麻煩。奈何兩人年紀相差十歲,三個代溝擺在眼前,寵妻倒成了代溝。安排好的事情不要,禮物也不喜歡,幫忙也不愿意… “蘇墨城,不是說,你只是一個普通的職員嗎?怎麼現在搖身變成了公司的總裁。” “蘇墨城,不是說,以前你根本就不認識我嗎,那你父親和我母親之間怎麼會是這種關系?”
55.3萬字8 51963 -
完結2072 章

幸孕六寶寵上天
一場陰謀,她被親爸賣了,還被人搶走孩子,險些喪命。五年后,她帶著四個孩子強勢回國尋找孩子,懲治兇手,沒想剛回來孩子就調包。發現孩子們親爹是帝都只手遮天活閻王顧三爺后,她驚喜交加,幾番掙扎后,她舔著臉緊抱他大腿,“大佬,只要你幫我收拾兇手,我再送你四個兒子!”三個月后,她懷了四胞胎,“顧南臣,你個混蛋!”“乖,你不是說再送我四個兒子嗎?”顧三爺笑的很無恥,逢人就夸,“我老婆溫柔體貼又能生!”她:滾!
198.5萬字8.18 5273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