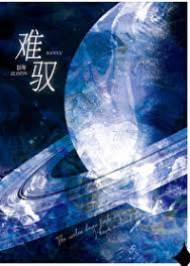《禍水》 第10章 后悔嗎
梁家祖宅位于環城區的壹山莊園,是當地首席豪宅,只開盤17棟,其中兩棟屬于梁家,一棟在梁延章名下,一棟在長子梁璟的名下。
臨近中午11點,車抵達老宅。
梁紀深沒立刻下去,有條不紊在后座了一煙。
保鏢沒催促,熄了火等候。
何桑很討厭煙味,職業習慣,飲食也清淡,上了臺,萬一嗓子啞了,保不齊被雪葬。
話劇這行,比任何行業的斗都激烈,尤其是a角,臺柱子,演軸的,耍手段取而代之,并不見。
好不容易站穩腳跟,更是打起十二分的神,避免被搞下臺。
但梁紀深是例外,何桑喜歡他手指和齒間的煙味,厚重,沉郁,清苦。
涌口腔,刮起鬼迷心竅的颶風。
“不進去嗎?”
煙氣濃,熏得梁紀深瞇眼,“進。”
他從車窗拋出煙頭,走向庭院。
何桑也下車跟著。
中式客廳擺放了一副金楠木的沙發,茶幾也是小葉紫檀,價值不菲,在沙發和茶幾之間,梁延章穿著一象牙白的唐裝,氣度不怒自威。
壽宴那日,距離遠,何桑只瞧個大概廓,今天仔細看,他完全不像六十的模樣,皺紋,毫不松弛,不愧是黎珍口中的男子,梁家這一脈的男人都英俊。
“長本事了。”梁延章在茶壺里添了一勺清泉水,“把帶過來。”
保鏢正要手拉何桑,梁紀深一拳撞開,活了幾下手腕,“梁氏和張氏競爭的那塊地皮,是我幫您談妥的。”
“那又如何?”
他攬住何桑肩膀,讓坐下,自己在旁邊,“您現在什麼意思。”
“我沒問罪你,你倒問罪起我了。”梁延章氣極反笑,“梁家沒你還不行了?”
“沒我行。”梁紀深氣定神閑卷著襯袖,“那您何必找我。”
“混賬你對誰撒火!”
煙灰缸飛馳而來,他側一躲,砸在后面的紅木屏風,一地的玻璃碴。
保鏢急忙打圓場,“梁董心疼三公子,特意出面保釋,不然您哪能這麼順利出來。”
梁紀深不吃這套,“不是保釋我,是保釋梁家的面。”
“托你的福,梁家早沒面了。”梁延章冷哼,端起茶杯,慢悠悠品茶。
喝完茶,他打量何桑,“你能惹麻煩。”
張繃直背,悶聲不語。
“最近低調些,不要胡作非為。”梁延章再次開口,“你大哥要回國了,多眼睛盯著梁家,稍有差錯,影響你大哥的名譽。”
梁紀深下外套給保姆,“這話您應該警告二哥。”
“遲徽比你像樣。”梁延章橫了他一眼,“起碼沒鬧到公司去。”
何桑并攏,難耐蹭了蹭屁,又扯梁紀深的角,“洗手間在哪。”
他偏頭,戶玄關鑲嵌了一座觀景式魚池,上面是鎏金的公用水池臺,“那里可以洗手。”
面紅耳赤,“我想方便...”
梁紀深看著,笑不笑,起帶上樓,到衛生間門口,他推開門,“我在這等你。”
何桑對陌生環境不適應,也知道梁家的人待不友好,速戰速決,洗手的時候,外面靜悄悄的。
“你還在嗎?”
沒回音。
慌了,飛快提上子,擰門鎖,“梁紀深?”
仍舊無人應答。
何桑探出頭,左右張,一道影子從墻角掠過,男人立在面前,領慵慵垮垮地敞著,皮帶扎得,腰又窄又拔。
他下胡茬的比上午更深了,味道也愈加渾厚。
何桑一抖,后仰,“你故意的。”
梁紀深眼眸漾著一笑,稍縱即逝,“完事了?”
松口氣,“嗯。”
“你怕什麼。”
何桑抬眼,“沒怕。”
他這方面有修養,不調侃人,也沒揭穿,只陳述事實,“忘了告訴你,這個衛生間的隔音不好。”
他聽到了里面的流瀉聲。
何桑臉臊紅,“你站那麼近干什麼。”
“你不是怕我離開嗎。”他手兜,個子高出許多,“我怎麼站遠。”
梁紀深說完,邁步走在前面,何桑亦步亦趨尾隨,經過客臥,打掃衛生的傭人截住他,“您夜里留宿嗎?”
“留。”
保姆越過他,看何桑,“兩間嗎?”
他余也瞥后,應了一聲,進臥室換服。
梁延章這會兒不在客廳了,只有保姆出忙碌,何桑獨自下樓,在一、二樓的轉角,遇見了梁遲徽和助理。
他一邊解領帶,一邊代公事。
空氣中彌漫一幽沉的,風韻的男香。
說不上來是木質調,還是花香調,亦或二者融。
何桑站定,“梁先生。”
男人也注視,語氣溫和,“你來了。”
仿佛很悉的口吻。
拘謹笑,“是梁董派車接我來的。”
梁遲徽將領帶搭在腕間,“和老三一起回來的?”
何桑抿,答不是,不答也不是。
好在他沒多問,并肩走過的一刻,男人忽然住,“何小姐,你是不是丟了東西。”
下意識口袋,鑰匙手機都在。
梁遲徽提醒,“你的耳環掉在醫院走廊了。”
復診當天確實丟了一只耳環,不過沒印象在哪丟的,“原來你撿到了。”
助理去車上取回耳環,先遞給了梁遲徽,何桑出手,男人極為紳士,沒有到,只著耳環懸在手上方,輕輕松開,冰冰涼涼墜掌心。
“多謝梁先生。”
梁遲徽頷首,“不謝。”
他在盡頭拐彎,似有若無的男香也隨之散去。
猜你喜歡
-
完結91 章

樑少的寶貝萌妻
【暖寵】他,宸凱集團總裁,內斂、高冷、身份尊貴,俊美無儔,年近三十二卻連個女人的手都沒牽過。代曼,上高中那年,她寄住在爸爸好友的兒子家中,因爲輩分關係,她稱呼樑駿馳一聲,“樑叔”。四年前和他的一次意外,讓她倉皇逃出國。四年後,他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而她歸國後成了正值花樣年華。樑駿馳是她想拒絕卻拒絕不
14萬字5 38724 -
完結517 章

婚不設防:帝少心尖寵
日久生情,她懷了他的孩子,原以為他會給她一個家,卻冇想到那個女人出現後,一切都變了。靳墨琛,如果你愛的人隻是她,就最好彆再碰我!
92.1萬字8 67365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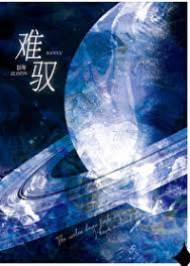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18 107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