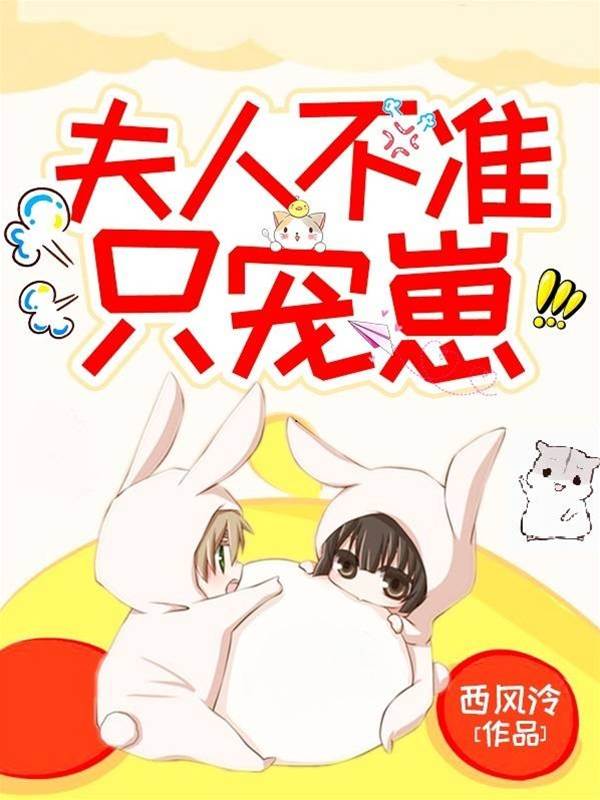《步步深陷》 第33章 馴服
馮斯乾摁住我吻了我許久,久到我不過氣,他離我的一刻,挨在我耳邊警告,“別耍花招。”
我齒微微開闔,吐出一縷氣,有來自他口腔的煙味,和似有若無的桃膏的香氣,的呼吸拂過發梢,縷縷環繞住他琥珀的頸扣,“我哪有耍花招,馮先生養我,我求之不得。”
他審視著我,指間銜著的煙到所剩無幾,他猛吸了最后一口,沒有對準我的臉噴出,可煙塵彌漫,熙熙攘攘也晃過我眉眼,他在煙霧的另一端,原本陷一團朦朧,又驟然吹開,他的眼睛那樣明亮深邃,猶如迷宮一般暗無天日的溶,盡頭乍現的天。
我摟著他,“馮先生給多錢呀。”
他力道狂野攬住我,扶著我坐在他腰間,我沒有穿,只穿了制服短,擺在廝磨中卷起,長發散開,白皙如雪的一寸寸浮,有萬種風泄在他膛,像無盡無休的細雨落在藤蔓上,曖昧又極盡人。馮斯乾在如此勾魂攝魄氛圍里下眼底依然清明理智,只生出零星幾分的迷離,“你要多。”
我豎起一手指,他角旋即溢出一笑,“一百萬。”
我搖頭,他笑容斂去一些,“一千萬。”
我仍舊搖頭,他甩下燃盡的煙,錮我在懷中,他又一次吻下來,吻得又兇又深,我嘗到他舌燒焦的煙,清苦得發。他語氣淡漠,“胃口倒是大,你值一個億嗎?”
我趴在他肩膀,緩解著四肢的癱無力,“我要馮先生一顆心。”
馮斯乾所有作戛然而止。
我吮著他結窄窄的棱角,“必須是真心。”
他滾了一下,我瓣停住,掀眼皮看他,“給得起嗎。”
他輕笑一聲,“比一個億的胃口還大。”
我說,“馮先生給不起,也別強求我真心,人對沒有真心的男人很難忠誠和認命。”
馮斯乾瞇著眼注視我良久,他撥開我癡纏他的手臂,“人的忠誠,是靠馴服。”
我著他,“像馴服寵一樣嗎。”
馮斯乾站起,撣了撣襯的褶痕,“我曾經馴養過一只西伯利亞獵鷹,用盡手段,它始終不臣服,后來我帶到擊場,親手擊斃了它。一切不愿意臣服的東西,我不會放生,更不會留存在邊,我會了結它。”
我渾一陣陣寒意,一個字也說不出。
馮斯乾俯下,干燥溫熱的手背我面頰,“寵不懂主人的脾氣,你懂,所以你能避免它的下場。”
我輕輕著僵的手。
馮斯乾松開我,去走廊接電話,這工夫保姆從帽間出來,問我行李在哪,我起上二樓,告訴過幾天搬來,跟在我后面,“韓小姐,士用品不方便擺在明,以后由我替您收拾。”
我頓時參悟了的暗示,“那有勞你了。”
我停在樓梯口環顧這棟別墅,每一裝潢都是抑的深系,即便馮斯乾在瀾春灣養人的消息泄,有人埋伏捉,從外觀看也抓不到人在這里生活的蛛馬跡,更像一個獨男人的居所。
他也許是防備殷沛東暗中下手,更也許是一個已婚男人對外的飾太平。
包小三要的,尤其沒打算離婚,越低調越好,真正聰明的男人周旋在婚姻和婚外中,有一萬種方法平衡和保,凡是餡的本就不謹慎,馮斯乾恰恰是很謹慎的這一類。
照現在的況看,他一時半會兒膩不了,我妄想獨立擺他的掌控非常困難,需要一個足夠有本事并且他不好輕易撕破臉的幫手。
周末馮斯乾在瀾春灣待了一天,傍晚才離開,他離開不久,趙書給我打電話,說自己在醫院做孕檢,麻煩我去公司取一份文件,送
#每次出現驗證,請不要使用無痕模式!
到春風路39號的江城名府,馮董晚上結束宴會要用到。
我折騰了兩個多小時,趕到酒樓的二層宴賓廳,一名迎賓小姐攔住我要請柬,我說我是給華京馮董事長送文件。示意我稍等,和會場的保安通確認后,取出一張臨時通行證,我看見上面標注著華京集團馮董夫婦,我蹙眉,“馮太太在?”
迎賓小姐說,“馮太太是陪同馮董來出席宴會的。”
我當即不想出現了,我和殷怡鬧到這步實在太僵了,何況大庭廣眾同臺,難堪的必然是我這個意圖破壞家庭的助理,而不是擁有名分且無辜害的馮太太。
我越琢磨越打退堂鼓,我問迎賓小姐,“酒樓能保存文件嗎?等馮董退場轉他。”
說,“文件太重要了,出差池我們沒法待。”
我不再為難,站在簽到的指示牌前整理好儀容,走進會場的主廳。
品相好的男人在一群頭大耳的襯托下總是格外醒目,我一眼便發現了馮斯乾,他側是穿著華貴晚禮服的殷怡,挽住他臂彎,兩人正和賓客飲酒談笑,我在數十米之外凝這一幕,想到一個很嘲諷的詞,天作之合。
我見過不權貴夫妻,貌合神離幾乎藏不住了,彼此配合的表象下裹挾著長年累月不接的生疏,馮斯乾和殷怡完全不是,他們的親給人覺很舒坦,是自然而然地意流,要不是我參與了他們之間驚濤駭浪的戰爭,我一定會被這副恩和諧的表面所蒙騙。
我深吸氣,走到他們跟前,馮斯乾這時轉過,從途經侍者的托盤上拿酒,我們四目相視,他顯然沒料到會是我,執杯的右手一頓,“你怎麼來了。”
聚集在周圍的賓客都不約而同停止談。
我把文件夾遞給他,“您的文件。”
殷怡在一旁面帶笑意,“韓助理辛苦了。”
我朝頷首,“馮太太,這是我分之事。”
殷怡喝了一口香檳,“分外之事韓助理其實做得也很出。”
我抿沒出聲。
圍觀的數賓客開始竊竊私語。
整局面比我設想好很多,殷怡好歹顧慮馮斯乾和殷家的面子,沒有當眾讓我太難堪,我正要速戰速決撤離現場,剛才和他們相談甚歡的男人突然住我,“韓助理留步。”
我閉上眼,殺千刀的。
我認得他,市里主管審批地皮的二把手季書文,和黃威是一個圈子的,據說私很不錯。我跟他之前沒來往,本來差點就有了,他老婆雇過我,我沒接單,因為傳言季書文有那方面的癖好,我們這行主打神,季書文是快餐型,他不玩那套虛的,只要上鉤就真槍實彈,有同行栽跟頭吃了大虧,我收到風聲直接拒絕了。
季書文端著酒杯靠近我,“韓助理今夜為何沒有陪馮董出席酒會,我有耳聞,你的印度舞跳得相當香艷啊。”
他架勢明顯不懷好意找茬,借著發難我,給馮斯乾和殷怡下不來臺,我保持微笑,“季主任真幽默,有馮太太在,哪還用得著助理呢。”
季書文大笑,“馮董啊,韓助理這朵解語花,難怪您搖了。只是花雖然解風,和酒一個道理,不能貪杯啊,后院還要維護好的嘛。黃主任那事,您沖冠一怒為紅,馮太太大度,咱們男人也得分清主次啊。”
殷怡面無表看著我和馮斯乾。
馮斯乾并沒接下季書文的敬酒,
眼神涼浸浸掠過他,“季主任是從哪里道聽途說這樣的傳聞。”
季書文故作驚愕,“莫非是子虛烏有嗎?”
馮斯乾冷笑,“當然是莫須有。”
季書文拍打自己腦袋,“瞧我,聽什麼信什麼了。馮董,馮太太,可別見怪啊。”
殷怡笑得十分溫賢惠,“我和斯乾不計較,好,風言風語是摧不垮的。”
馮斯乾默不作聲轉著杯里的酒。
我沒和他打招呼,一臉平靜走出宴廳,回到瀾春灣,保姆說先生來電話了,無論多晚會回來一趟。
我了高跟鞋,心不在焉倒在沙發上,臉發白,慘白那種。
保姆斟了一杯熱水放在茶幾上,觀察我的樣子,“韓小姐,您不舒服嗎?”
我答復,“沒事。”
很焦急,“您不舒服要講,先生叮囑我照顧好您。”
猜你喜歡
-
完結37 章

偏偏占有你
姜晚照年少時喜歡一個男人,為他傾盡所有。可惜,男人永遠都是一幅冷漠淡然,漫不經心的模樣。喜歡無果,姜晚照喪了氣。天涯何處無芳草,何必單戀一枝花。何況她還有一堆小哥哥寵,才不稀罕他!想明白后,她瀟瀟灑灑放了手,一心一意搞事業。 沒過多久,姜晚照發現——她所在的女團,人氣暴漲,資源逆天!她所在的星空娛樂,她成了最大的股東,享有絕對的掌控權。連續幾天,她收到了不動產若干處,豪車一大排,連帶著私人飛機,郵輪,名貴珠寶琳瑯滿目,應接不暇…… 姜晚照:“……”再相見的慈善晚宴上,姜晚照瞪著剛以她的名義拍下某條價值連城的項鏈男人,揚起明艷的小臉氣哼哼地質問:“廉總這是什麼意思?”男人黑眸沉沉,似笑非笑:“求你回來啊,這個誠意夠不夠?”直到后來她才知道,他所付出的一絲一毫,最后都會變本加厲地從她身上討回來。 一手遮天冷漠貴公子X膚白貌美破產千金
12.3萬字8 8410 -
完結375 章
隱愛100分︰惡魔總裁,強勢寵
一場意外,言小清被霸道的男人盯上。 他扔出協議︰“做我的女人,一個月,一百萬!你從今天起,專屬于我,直到我厭煩為止!” “我拒絕!” “拒絕在我面前不管用!” 拒絕不管用,她只好逃跑。 可是跑著跑著,肚子里面怎麼突然多了只小包子? 她慌亂之際,他如同惡魔一般出現,囚住她,他這次非常震怒,他說他們之間的一切都不能曝光。 她摸著肚子,告訴肚子里面的小包子︰“寶寶,你爸爸說不能曝光我和他的事,那我們也不告訴他你的存在好不好……” 某日,男人得知小包子的存在之後,立刻慌了。 他強勢的將她和孩子保護起來,從現在起,誰要是敢動她和孩子一下,他絕對讓對方吃不了兜著走。 她和寶寶,都是他的!
34.6萬字8.09 113731 -
完結10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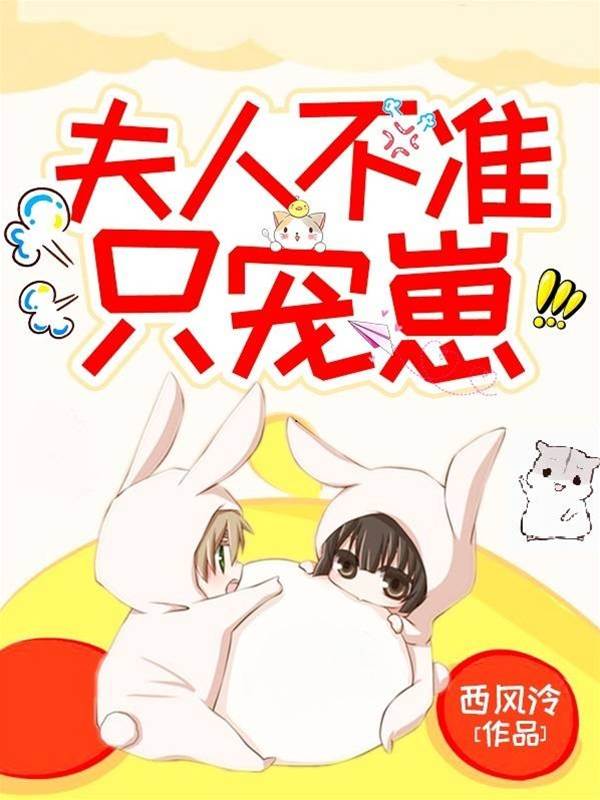
夫人不準只寵崽
南悠悠為了給母親治病為楚氏集團總裁楚寒高價產子,期間始終被蒙住眼睛,未見楚寒模樣,而楚寒卻記得她的臉,南悠悠順利產下一對龍鳳胎,還未見面就被楚家接走。
24.6萬字8 70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