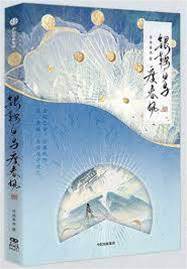《嬌軟美人和她的三個哥哥》 【64】
話音落下,那道修長的背影很快消失在異彩漫天的冬日黃昏里。
謝叔南怔怔地站在原地,撓了撓后腦勺,有些云里霧里,不是在說云妹妹的事麼,怎麼突然想到丟東西了?而且大哥這樣嚴謹的個,也會丟三落四?真是難得。
……
外頭傳來靜時,云黛手握著一卷書,正盯著人斛中那一簇緞做的羅缽蠟像生四時小枝花朵,黃花翠葉,栩栩如生,看得出神。
琥珀急急喚著“世子爺”,又一陣凌的腳步,人已到了書房里。
著驟然出現在屋的男人,云黛不由得怔忪,等回過神來,忙放下書卷,斂衽起,朝他行禮,“大哥哥。”
琥珀站在雕花屏風后,一會兒無措地看看世子爺,一會兒擔憂地看向自家姑娘。
云黛見一臉為難,再看謝伯縉面罩寒霜,抿了抿,對琥珀道,“琥珀姐姐去沏茶來吧。”
琥珀遲疑,在接收到自家姑娘寬的眼神后,才應聲退下。
云黛抬頭看了眼一凜冽寒氣的男人,默了默,輕聲道,“大哥哥請坐。”
說罷,自顧自走到落地霞影燈旁,準備點燈。方才在發呆,都沒覺著屋昏暗,這會兒見人進來,才驚覺天已黑了。
從燈盞旁取下火石,剛想取火,后有腳步接近。
一扭頭,鼻尖險些蹭到男人的膛,有沉馥馥的沉水香味,夾雜著淡淡的酒氣,云黛駭了一跳,腳步下意識往后躲,“大哥哥?”
謝伯縉見這般刻意的閃躲,下頜微繃,“我來。”
他朝出手,袒出修長的掌心。
云黛松口氣,自嘲自己大驚小怪,將手中火石遞到他的掌心里。
纖細的手指不經意的過掌心,只那麼輕輕的、短暫的,蜻蜓點水般,卻謝伯縉眸暗了幾分。
他握住那火石,仿佛上頭還殘著的幾分溫度。
云黛繞著霞影燈與他避開一段距離,回到榻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盯著那點燈的頎長影,心底直打鼓,這個時候他怎麼突然來了?而且還喝了酒,一副心不虞的模樣。
是在外頭遇到麻煩了?還是自己哪里得罪了他?
心頭惴惴間,燈已然亮起,琥珀那邊也端了茶盞過來,垂手在旁聽候吩咐。
謝伯縉將火石放好,扭頭見杵在柱子旁的琥珀,沉聲道,“你出去。”
琥珀驚詫看去,見世子爺神冷漠,心頭畏懼,巍巍應了聲是,垂著頭退下。
書房靜了下來,云黛無措地站著,面上出一抹不自然的笑,“大哥哥喝酒了,坐下喝杯茶醒醒神吧。”
謝伯縉看臉上的笑,又想到謝叔南說的,朝崔儀的笑——
他不聲地坐下,執起那青蕉葉紋茶盞,另一只手掀開杯蓋,清新茶香潤撲鼻,他嗅著茶香,略抬眼瞧見拘謹站著,恨不得與他隔個十萬八千里,出聲道,“站那麼遠作甚?”
云黛笑容一滯,旋即在他的注視下,隔著小巧案幾,沿著榻邊坐下。
謝伯縉淺啜一口茶水,放下茶盞,“妹妹與我生分了。”
云黛心底翻起一陣苦與歉疚,臉上的笑意愈發勉強,低聲否認,“大哥哥這說得哪里話,沒有生分。”
兩廂安靜下來,謝伯縉只輕叩著木質桌面,垂眸不語。
云黛只覺這份安靜實在煎熬,纖細的手指攥襦,默了兩息,試探地問,“大哥哥事務繁忙,怎麼有空來我這?”
謝伯縉側眸看向,“我過來,是討個說法。”
云黛清麗的眉眼間浮起迷茫,“什麼?”
“為何對崔儀示好?”
謝伯縉平靜地凝視著,仿佛要進心里,將的心思看個清楚徹底。
云黛怎麼也沒想到他這個時候跑來,竟是問這事。
錯愕之后,定了定心神,打著哈哈道,“大哥哥這是哪聽來的,我怎麼與崔家表兄示好了?今日雖是見了面,也只是尋常問候了兩句。”
“是麼。”
指節分明的手了鼻骨,他閉上眼,語調輕緩,“嗯,那是三郎誤會了。回去我就與他說,妹妹對那崔儀、對崔家不過是親戚間的禮尚往來,全無他意。”
他的語氣沒有任何起伏,平靜的像月下河流,清清淡淡,卻云黛有種被拆穿心思的無地自容。
閉口不言,又聽他繼續道,“不過先前我也與你說過,謝崔兩家雖是親戚,但崔儀到底是外男,還是來往為好。”
謝伯縉睜開眼,狹長的眼尾因著酒氣挾著一抹艷麗的紅,“至于送藥膏,妹妹跟著母親學規矩,應當知曉此舉不妥,很易惹人誤會。若是崔家會錯了意,那可不好。”
云黛臉一變,嫣紅的翕張,“我……”
他支著額頭看著略顯蒼白的臉,神著幾分慵懶,“不過你也不必擔心,我知你不是故意的。改日去崔家拜訪,我會替你解釋……”
手指掐掌心,云黛深吸了口氣,“不用勞煩大哥哥解釋。”
“嗯?”
云黛纖濃的眼睫微,細的面頰有些難堪地漲紅,避開他的眼,腦袋垂得很低,“我是故意的,我就是故意的。”
急急的語速帶著些破罐子破摔的意味。
謝伯縉黑眸瞇起,“為何如此?”
“我及笄了,也該考慮婚事了。崔家是個好人家,儀表兄人也很好,祖母和姑母也都滿意,這會是門好親事。崔夫人相中了我,待我有那份心思,我既也滿意這門婚事,與他稍稍示好,原也算不得什麼……”低低說著,自言自語般。
謝伯縉盯著一張一合的,只覺頭腦昏賬。
半晌,他道,“你覺著他不錯,那我呢?”
云黛心口猛地一跳,驚愕地看向他,及他直直看來的目,目閃躲,干地笑,“大哥哥,說什麼呢…你是吃醉酒了吧?”
他幽深的目黑涔涔的,照進琉璃的月般,清澈皎潔,分明沒有半分醉意。
無聲的對峙般,空氣都變得抑,云黛終是抵不住他的視,倉皇站起來,“我去人給你煮碗醒酒湯……”
謝伯縉長臂一,一把拽住的手腕。
在驚詫的目下,他臂彎一用力,就跌坐在他上,撲了滿懷。
男人的氣息和酒味劈頭蓋臉地將籠罩,云黛的心仿佛要跳出嗓子眼,雙手抵著他的膛,慌張的就要起,男人熾熱的手掌卻地握住了的腰,彈不得。
“大哥哥……”小臉煞白,心神不定從他懷中抬起頭。
太近了,兩人的距離太近了,的眼前就是他的下頜,他一低頭,連他睫數都瞧得分明。
“那天夜里,妹妹也是這樣坐在我懷中。”
謝伯縉垂下黑眸,一只手攫著的下,靜靜地看向,像是有些苦惱的問,“不記得了麼?”
溫熱鼻息拂過的臉,云黛的子止不住抖,尤其想到那日夜里的耳鬢廝磨,嚇得說不出話來,只睜著一雙霧蒙蒙的水眸盯著他,寫滿了驚懼與不可置信。
不明白他為什麼要將這層窗戶紙捅破,將他們倆置于如此尷尬的境地。
明明那夜的事,他們倆可以心照不宣地當做沒發生過,起碼還能維持一面——從此他回隴西、回北庭,留在長安,隔著千山萬水,一輩子也見不到幾次面,各自安好。
“大哥哥,那晚……那晚的事……”清甜的嗓音抖著,艱難地吐字,“那晚的事是我連累了你,我對不住你。五皇子往酒水里放了那種藥,我當時只想著盡快,我沒料到那藥效竟那樣強……我知道錯了……”
“你知道錯了?”
謝伯縉盯著漸漸盈著淚水的眼,冷下心腸,嗤笑道,“所以在我懷中索吻后,轉頭又去向崔儀示好?嗯,這就是你認錯的方式。”
云黛腦袋一片混沌,失神盯著他,淚珠兒直往下淌,“出了這樣的事,我不知該怎麼面對你,也再沒臉回去見國公爺和夫人,他們對我那樣好,養我一場,卻養出個不知廉恥的人來,纏著自己兄長做了那樣的事……我此生無法報答他們的恩,只想著躲得遠遠的……”
見哭得崩潰,謝伯縉糲的手掌拂過的臉,細細去的淚水,皺眉道,“誰說你不知廉恥了。”
云黛見他語氣溫和了些,潤眼眸滿懷請求看向他,嗓音又輕又,“我知道大哥哥一向待我好,那日的事就當沒發生過,你我就像從前一般,好不好?”
話音剛落,那摟在腰上的手驀得收。
吃痛一聲,對上男人闃黑的深眸,他薄輕啟,“不好。”
云黛淚一,不知所措。
謝伯縉寬大的手掌嚴嚴實實托著的臉,他緩緩低下頭,額頭抵著的額,鼻尖著鼻尖,溫潤的呼吸在這幾乎的距離里流竄,他低啞的嗓音著幾分冷意,“什麼沒發生過?”
手指按上囁喏的,他挲著的瓣,似漫不經心道,“今日在外頭喝了葡萄酒,還有玫瑰酒,混在一塊兒,就像那夜妹妹的味道。”
“大哥哥…大哥哥……”云黛渾不可抑止地抖,一顆心直直的往下落。
一切好像失了控,怎麼就了這樣的境地。
高的鼻梁輕輕劃過小巧的鼻尖,謝伯縉微微偏頭,薄落在的角,像往日那般溫和哄著:
“既然發生了,不如將錯就錯。妹妹何必舍近求遠,看我如何?”
猜你喜歡
-
完結1979 章

萌寶在上:邪魅王爺追妻忙
穿越成廢物如何?咱未婚先孕有個天才萌寶罩!不知道孩子他爹是誰又如何?咱母子聲名鵲起還怕冇人倒插門?萌寶:孃親,神獸給你牽來了!天材地寶給你搶來了!漂亮的男人給你帶來了!某女嫌棄:無錢無勢無實力,不要!某隻妖孽邪笑:錢財任你揮霍,大陸任你橫走,夠冇?母子兩人對視:美男在手,天下我有!成交!
177.5萬字8 130419 -
完結5533 章

冷王邪妃太逆天
救人一世,儘落個滿門抄斬,再世為人,她要逆天改命,毒禍天下!獲神劍,契神獸,修神訣,煉天下神器!欺我者亡!虐我者死!誅我全家之人,讓你連活都冇有可能!再活一世,就是這樣猖狂!他是世上最冷漠的九爺,戰場見到他的人,都已經死了,人送“活閻王”。本以為他是最無情的九王爺,卻變成了自己夜夜變狼的大師兄!“小師妹,我可以罩你一生!”“大師兄,我可以毒你全家!”“太好了!小師妹,我們一起雙修禍害全天下!”雙煞合併,天下誰人不抖!
363.3萬字8 119781 -
完結3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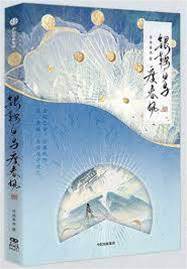
銀鞍白馬度春風
君主剛愎自用,昏庸無能,掩蓋在長安錦繡繁華之下的,是外戚當權,蟻蛀堤穴。 賢仁的太子備受猜忌,腐蠹之輩禍亂朝綱。身爲一國公主,受萬民奉養,亦可濟世救民,也當整頓朝綱。 世人只掃門前雪,我顧他人瓦上霜。這是一個公主奮鬥的故事,也是一羣少年奮鬥的故事。 ** 你該知道,她若掌皇權,與你便再無可能。 我知道。 你就不會,心有不甘嗎? 無妨,待我助她成一世功業,他日史書之上,我們的名字必相去不遠。如此,也算相守了。
55.4萬字8 187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