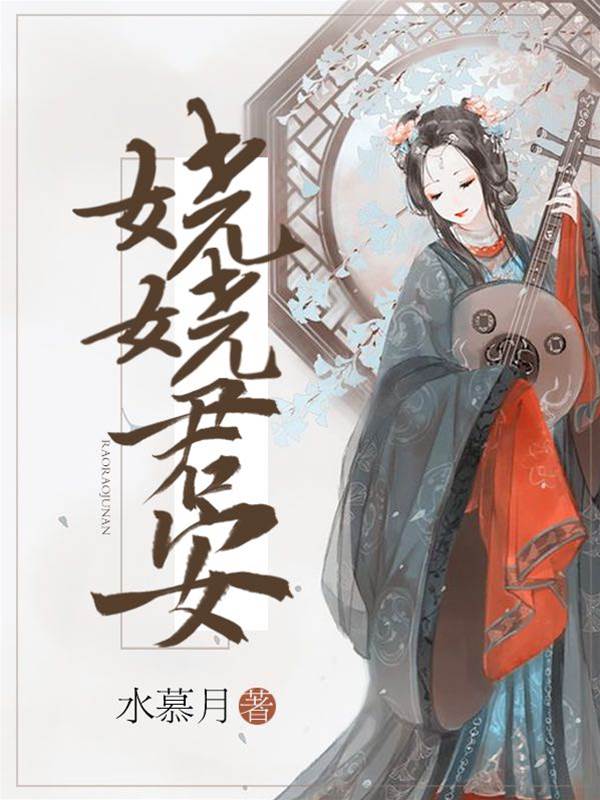《教不乖,佞臣替人養妹被逼瘋》 第1章 窩裏藏著隻白軟小兔
祥貞元年,戰不休。
大雍朝兩載崩三皇,死因謎。
朝堂之上黨派紛爭不斷、飛鷹走狗遍布,征戰在外的祁家將軍偏在此時殞命千裏之外。
大雍朝於風雨飄搖中又遭致命一擊。
氣數將盡。
京中北角一隅,院臘梅染了一樣的紅痕,婢伏地,磕紅了額頭。
“小姐,一切打理妥當……”
鵝絨大雪撲落而下,遮了滿院毯,這毯是的,卻非被雪打。
此刻踩上去,應是十分的,但因落著雪,不會輕易引人注意。
空氣中彌漫著淡淡油香。
院擺放著一張檀木製的案幾,古琴橫陳,白玉的香爐散開嫋嫋輕煙,點的是香氣濃烈的沉香,很快便遮掩了那子油膩氣味。
一院之隔,描了朱紅的門搖搖墜,外頭的虎狼之人調笑辱罵,似是頗為圍獵落單小兔的刺激。
祁旻重兵在手,得這群紈絝們抬不起頭,如今他石葬白骨,他們可是酒池林歡慶了一場又一場。
暢快夠了,又覺無聊,小廝為哄主子高興,便附耳低語,獻計一則。
祁旻是廝殺在外的狼,窩裏藏著隻白白的小兔,他得勢時沒人敢,生怕回頭再這將軍一劍砍了。
可如今祁旻死了,這小兔子不就是送到舌邊兒的玩,是是,還不是這臨門一腳的事兒。
半炷香後,轟——
一聲巨響,門被撞開了。
婢驟然一個哆嗦,懼紅了雙眼:“小姐……”
琴弦震,似狂風暴烈撕扯過境,又似浮雲悠然飄,兩種靈魂拉扯撞,好似一切都是碎的。
祁桑纖長的眼睫落滿了雪,瞧著抖的肩,輕笑:“哭什麽?怕我要你陪我燒死在這裏麽?”
婢一窒,漲紅了小臉。
螻蟻尚且生,自是不想在此丟掉命,可危難關頭拋下待自己恩重如山的主子,又愧不已。
可聽著外頭雜的腳步聲,男人們放浪不堪的調笑聲,明白小姐此番在劫難逃,留下也不過是白白送命。
磕下三個重重的響頭後,踉蹌著向側門奔逃而出。
似是忘了自己當初被當做陪葬丫頭丟進三米多的墓坑,是祁桑一錠銀子買下了,也忘了黃泥滿的自己是如何磕破了頭,承諾生死不棄。
祁桑白素縞,席地而坐,琴聲不。
日暮天寒,飛雪漫天。
“喲,公子您看,這祁大將軍的妹妹倒是個識趣兒的,早早在這兒候著您的雨恩澤了。”甜的小廝諂著哄主子開心。
後頭隨即傳來幾道不滿聲:“姚公子可別吃獨食兒啊,這祁家妹妹可是個人兒,三年前我曾在大街上見過一麵,嘖嘖,那腰段,那眉眼,看一眼骨頭都了,可惜那時候被祁旻護著,我也隻能幹過個眼癮。”
姚法生聞言嗤笑一聲,斜挑上揚的眉梢間盡是暴掠之氣:“爺是那小氣的主兒麽?這恩澤雨啊,今晚一並承了咱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不愧是咱們閣老的大公子,這氣度這襟,我等塵莫及啊哈哈哈……”
哄笑聲中進朱紅鏤花的兩扇門間。
寒冬臘月裏,隻見一席地琴,潑墨般的烏發被風吹散在後,右手邊擱著一籠微紅。
竟還有心思在這裏焚香彈琴。
院子裏黑地站滿了人,有主子,有小廝,此時俱是睜大了眼睛仔細瞧著。
聽聞這祁桑學藝於文人墨客皆敬仰不已的範老先生,是範老先生僅有的幾個閉門學生之一,盡得其真傳。
這琴藝百聞不如一見,竟是秦樓楚館的淸倌兒都攀不上。
一個不過及笄之年的姑娘,眼瞧著要被沾髒、撕裂、碾碎在泥濘裏,竟毫無懼,像一抹溫亮亮的月,清的人看著便心生歡喜。
偌大的院落中,一時竟隻剩積雪彎臘梅的吱呀聲。
琴聲驟停,祁桑在一片寂靜中挑燈而起,赤著腳走上前。
的臉很小,雪白,不做表地看著一個人的時候,像極了祁旻。
姚法生一時竟被這雙黑湛湛的眸子盯出了幾分寒意。
後小廝忽然附耳低語:“主子,聽聞這祁桑跟邢氏族長的嫡子關係匪淺,這……”
邢氏乃大雍百年世家,家底厚,在京中關係盤錯節,也算是名門中的族了。
但比起皇親貴戚,位同宰相的閣閣老,自是不值一提。
姚法生一邊打量著跟前的小人,一邊思忖著。
一來,來都來了,這時候灰溜溜走人不是他姚法生的風格,丟人。
二來,祁旻戰死距今已有月餘,邢氏既未將接府,也未曾派人來護一二,心思昭然若揭。
這第三嘛……
這小妮子不愧是祁旻的妹妹,一風骨看著就人牙,想起之前那祁旻三翻四次壞他好事,他今天還非要折了他妹妹這一傲骨,淪落到青樓不如的田地裏去。
風吹雪落滿肩頭,除了後垂落的兩肩長發,祁桑似是要與這天地一同融為漫漫雪。
姚法生冷笑一聲:“看來還得好好調教你一番,出來侍候爺,還穿什麽服。”
說罷,手便要撕碎衫。
後一群男人本能長了脖子,一雙雙眼睛氣畢現,急不可待地等著大飽眼福一番。
祁桑挑燈的手微微抬高……
“姚公子——”
隔著層層人群,遙遙傳來一道涼涼的,偏細的聲音:“您好歹閣老府出,這行事啊,還得顧著咱們閣老的麵不是?”
眾人一驚,轉間,集的人群已是自避讓開了一條路。
姚法生以為自己聽錯了,錯愕一瞬,轉竟真看到了西廠的仗隊。
且不是普通西廠太監,一眾錦華袍最首端的,竟是西廠提督徐西懷。
錦袍繡祥雲,腰間配玉環,那把令人聞風喪膽的咬風刀正正在腰間,走間於黑風氅下時時現。
倒是未曾聽聞,這祁旻跟西廠有什麽瓜葛。
猜你喜歡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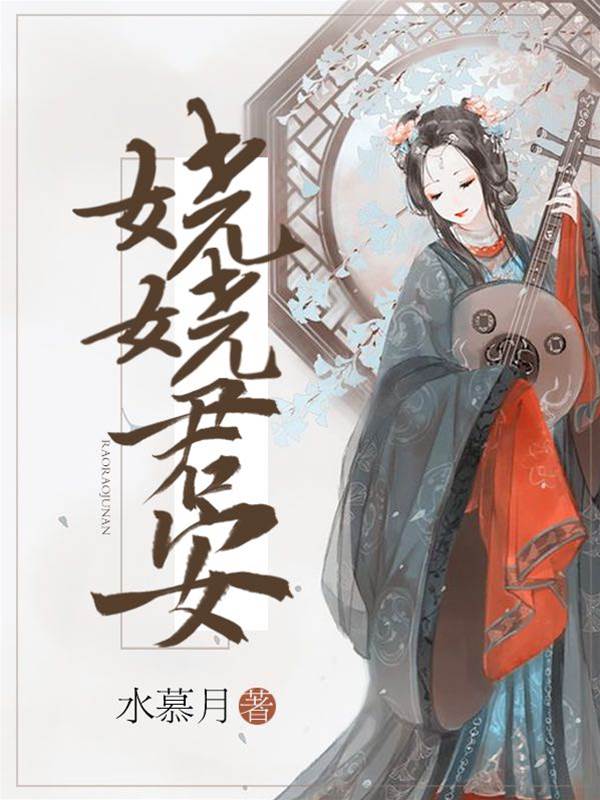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3997 -
完結244 章
綺夢璇璣
腹黑王爺與烏龜美女大PK。過程輕鬆小白,結局保證完滿。美女,身爲一代腹黑大BOSS的王爺趙見慎見得多了,沒見過謝璇璣這麼難搞定的…利誘沒有成效,雖然這個女人愛錢,卻從不肯白佔便宜。送她胭脂花粉首飾珠寶,拿去換錢逃跑。甚至許以王妃身份她都不屑一顧。色誘是目前看來最有效的,可惜還是次次功敗垂成。對她溫柔,她懷疑他有陰謀。對她冷淡,她全無所謂。對她刁難,基本上都無功而返,任何問題到了這個女人面前都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解決。這個女人對他的迴應就是一句:“除了金銀古董,別人用過的東西我都不要!”
53.8萬字8 26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