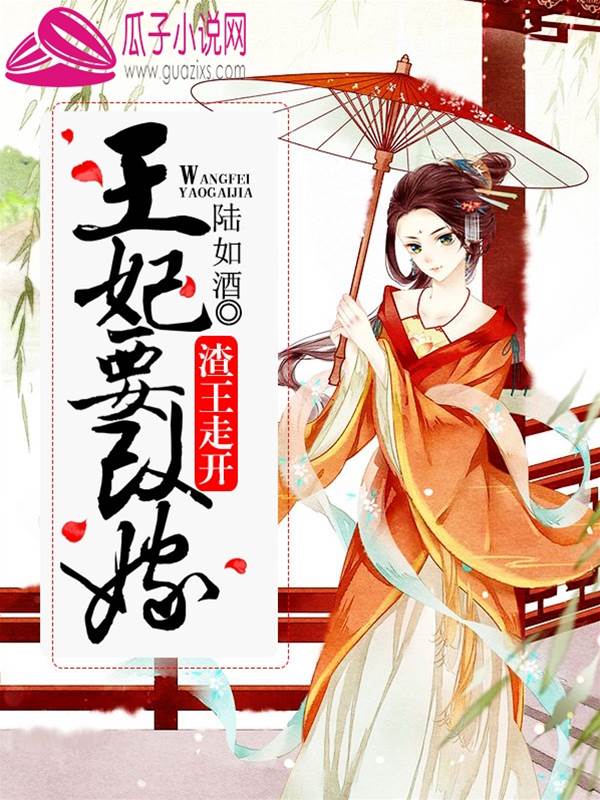《燈花笑》 第二百一十三章 生辰
時日過得很快。
進了八月,雨水連綿,轉眼又過了中秋。
殿帥府中卻很是忙碌。
祭典近在眼前,殿前諸班諸值及步騎諸指揮每日忙著訓練,以待十日後的祭典親閱。就連八月十五中秋當日,殿前班也增撥一倍人手守把諸門。
宮中衛森嚴更甚往日,有朝臣猜測,此事與陳貴妃宮中作有關。
加之太子元貞稱病,數日不現朝堂,有流言漸起。
殿帥府中,適逢下雨,演武場地溼,衛們今日休訓。
院中梧桐被雨水打落一地,段小宴揹著一隻竹筐匆匆進門,一進屋,抖淨上雨水,擱下雨傘,把罩在竹筐上頭的油布一掀——
“呼啦”一下,休憩的衛們全都圍了上來。
一竹筐裡全是三角紅符,其間還夾雜著些布頭紮的桃花樹枝、珠串什麼的。段小宴抹把汗,叉腰道:“排隊排隊,一個個來。”又抬手打掉一個衛來的爪子,不悅道:“都一樣,挑什麼挑!”
西街何瞎子請狐仙娘娘親自開的招桃花符咒珠串,買得多越便宜,段小宴自告勇替殿前班諸人代買,總算講了個雙方滿意的價錢。
吵吵嚷嚷的聲音隨著雨聲一道飄進屋裡,裴雲暎看了門外一眼,眉頭微擰。
“越來越沒規矩。”他冷道:“你也不管管。”
蕭逐風坐在桌前,端著杯熱茶,聞言道:“管什麼,你自己都買了一隻。”
他視線掠過裴雲暎的桌案。
厚厚軍文堆疊的下面,約出一角紅。
裴雲暎一哂:“你不也買了一隻?”
蕭逐風:“……”
他默默把木屜往裡推了推。
二人都沉默一下。
“已經半月沒來殿帥府了。”蕭逐風低頭喝了一口茶,“你倆吵架了?”
“不是。”
“那就是你沒機會了。”
裴雲暎不悅:“你有病啊。”
自上次下雨日後,他與陸曈已有半月沒見過面了。
宮裡事務繁忙,梁明帝這回似鐵了心罰太子,改立儲君之意朝臣心知肚明,太子一黨和陳國公一黨勢同水火,皇上已派兵數日前離京去往岐水,不知有意還是無意,梁明帝常召他夜談。
他出宮時已很晚,有時想去西街,又怕夜深耽誤對方休憩。聽太師府探子回報這些日陸曈一切都好,戚玉臺還算規矩,便暫且沒去與相見。
連著趕了好幾日大夜,手頭之事總算告一段落,出兩日旬出來。
“我是在替你擔憂,”蕭逐風站起走到窗前,看著簷下落雨,“畢竟,還有個前未婚夫紀珣。”
“那只是你臆測。”
“人家是君子,品行高朗。”
裴雲暎嗤笑:“君子又如何?在眼中,與埋在樹下的死豬也沒什麼區別。”
蕭逐風道:“你很自信?”
“當然。我和你不一樣。你喜歡默默祝福,但對我來說,喜歡就是佔有。”
年輕人笑意淡去,“別說和紀珣沒什麼,就算有什麼,要是真喜歡紀珣,我就……”
蕭逐風:“你就什麼?”
“……我就拆散他們。”
蕭逐風無言,道:“所以今日你特意岔開生辰不回家,就是要與見面?”
裴雲暎瞥他一眼:“你想見我姐,自己去就是,拿我做藉口,行不行啊?”
蕭逐風不理他:“你要跟表白心意?”
“現在不是時機。”
裴雲暎眸微,淡淡開口:“一心報仇,無暇分心,徐徐圖之更好。”
蕭逐風看了他半晌,擱下手中茶盞,輕蔑開口。
“行不行啊?”
……
門外雨下大了。
陸曈從屋裡出來,拿起牆角雨傘。
杜長卿見狀,懶洋洋對揮了揮手,“早去早回。”目又瞥見陸曈後的銀箏,神一僵,趕低頭撥打算盤,避開了對方的眼神。
鬱郁十幾日後,傷的杜長卿重新回到醫館,看上去若無其事,每日依舊照常罵人,但總會在某個時候不由自主流出一哀怨。
像是真的很傷心。
相比之下,銀箏倒是坦然大方得多。
銀箏送陸曈出了門,瞧見陸曈又如平日般簪上那隻木槿花簪,“咦”了一聲,奇道:“這幾日怎麼不見姑娘戴那隻梳篦了?”
木梳雖然不夠華麗,但戴在陸曈髮間也添清麗,不過似乎有些日子不見了,陸曈的妝奩裡也沒瞧見。
陸曈道:“壞了,已經丟了。”
“啊?”銀箏惋惜,“真可惜,還怪好看的。”
陸曈似乎沒聽見的話,低頭上了門口等著的馬車,“我走了。”
……
陸曈到太師府的時候,戚玉臺正與戚清派來的人說起天章臺祭典一事。
宮中祭典百儀衛在場,前些日子戚玉臺癲疾流言又鬧得沸沸揚揚,此次祭典,他需出現人前,力破謠言。
太師府對此很看重。
管家正對戚玉臺說明祭典當日的儀服和流程,戚玉臺不耐煩將對方手中文帖拍開:“又不是第一次去,有什麼好準備的。”
管家還想再勸幾句,一抬眼,見陸曈隨婢走到門口,於是退後一步,朝陸曈行禮:“陸醫。”
陸曈頷首,將醫箱放到桌上,示意戚玉臺坐下為他行脈。
待行脈結束,老管家問:“陸醫,爺近來如何?”
“脈象穩定,無不適跡象。”
老管家這才放下心來。
“行了行了,你快出去吧。”戚玉臺急躁道,“文帖我會看。”
老管家又看了一眼陸曈,溫言退下了。
待管家一走,戚玉臺便迫不及待朝陸曈手。
陸曈頓了頓:“先施針吧,戚公子。”
金針扎進皮,的疼,心底的卻得到徹底紓解。戚玉臺以袖掩鼻,藏在闊袖中的鼻翼翕,將一壺熱茶灌間,發出舒服的一聲喟嘆。
痛快。
實在太痛快了。
每日施針,是他最為盼的時刻。
陸曈製作的替代寒食散的藥散,極大滿足了他的藥癮,使他不至於憋在府裡發狂。他對這東西如癡如醉,難以自拔,為如今太師府裡唯一的藉。
何況這藥散並不似寒食散藥力強勁,不至於服食後衝失態,因此半月以後,並未被任何人瞧出不對,甚至是太師府另請來的醫。
這也是唯一缺點。
藥力微弱,意味著不夠過癮,彷彿隔靴搔,亦或是每到關鍵就戛然而止,令人意猶未盡。
戚玉臺了包著藥散的油紙,將最後一星末舐乾淨,不滿地開口:“陸曈,你不能多給我加點藥散,每次這麼一丁點,當我花子打發?”
陸曈收起金針:“戚公子,此藥散過量則有毒,眼下是對你子最好的服量。”
戚玉臺冷笑:“你是不是故意的?”
陸曈每日都來給他施針,但並非每日都會給他帶藥散。
有時覺得屋中護衛婢盯得,亦或是覺得他脈象出現變化,那一日便沒有藥散。
很謹慎,是以這麼長日子無人察覺。
但戚玉臺卻被吊起胃口,時時抓心撓肺。
“過不了多久就是祭典大禮。”陸曈道:“太師大人說過,祭典之前,不可出任何意外。”
“所以你想用這個拿我?”
戚玉臺將從上到下打量一眼,勾起一個輕佻笑容。
“放心,只要你藥散做得好,祭典過後,我可以保證讓你為我的侍妾。”
“你只要討好我就行。”
陸曈彷彿沒聽見他輕辱語氣,平靜收拾好醫箱,道:“下先行告退。”
戚玉臺無趣撇了撇,瞧見對方纖弱背影撐傘消失在雨中。
很冷淡。
卻無端讓人很有徵服。
從前戚玉臺只想殺了,為擒虎、為妹妹報仇,如今卻有了更好的主意。
他想摧折對方傲骨,看對方冷淡的眼神於自己下臣服,醫院中醫高明的醫,最終卻在自己後院搖尾乞憐,比降服擒虎那樣的惡犬更讓人興。
他心口,藥散的餘韻令他心中激盪。
誰是個平人?
幸好,是個平人。
……
陸曈離開太師府,轉角進了太師府長街盡頭巷口,平日裡,若無別的事,杜長卿僱好的馬車就在這裡等。
雨水綿延不絕,馬車靜靜在簷下等候。
陸曈撐傘走近,待看清前頭馬上之人時,不由一頓。
青楓戴著一頂斗笠坐在車伕的位置,見來了,把斗笠往上扶一扶,道:“陸醫。”
陸曈看向馬車後。
似是知曉心中所想,清楓忙道:“大人沒在車上,晌午進宮一趟,讓我先來接你。”
見陸曈無於衷,他又提醒:“今日是大人生辰。”
八月十九,裴雲暎生辰。
上回夜裡他來醫館時曾說過,後來明裡暗裡又曾許多次向討生辰禮。
陸曈問:“所以,找我做什麼?”
猜你喜歡
-
完結336 章

狂妃來襲:丑顏王爺我要了
殺手之王穿越而來,怎可繼續受盡屈辱!皇帝賜婚又怎樣,生父算計姨娘庶妹心狠又怎樣?淪為丑顏王爺未婚妻,她嗤笑:“夫君如此美如天仙,不知世人是被豬油蒙了眼嗎?”“女人,嫁于我之后,你還以為有能力逃離我嗎?”…
89.5萬字8 120887 -
完結905 章

空間娘子要馭夫
二十一世紀神醫門后人穿越到一個架空的年代。剛來第一天被浸豬籠……沒關系,她裝神弄鬼嚇死他們……又被打暈喂狼?沒關系,她拉下一個倒霉蛋……只是,這個倒霉蛋貌似很有性格,白天奴役她,晚上壓榨她……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五年翻身得解釋。雙寶萌娃出世…
127.8萬字8 22934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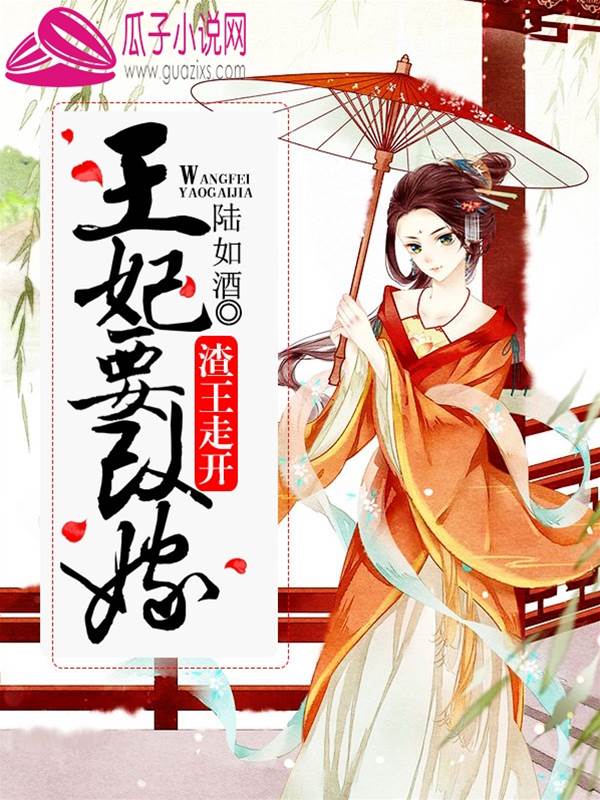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2790 -
完結163 章

嫁三叔
顧長鈞發現,最近自家門口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少年徘徊不去。一開始他以爲是政敵派來的細作。 後來,向來與他不對付的羅大將軍和昌平侯世子前後腳上門,給他作揖磕頭自稱“晚輩”,顧長鈞才恍然大悟。 原來後院住着的那個小姑娘,已經到了說親的年紀。 顧長鈞臉色黑沉,叫人喊了周鶯進來,想告誡她要安分守己別惹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卻在見到周鶯那瞬結巴了一下。 怎麼沒人告訴他,那個小哭包什麼時候出落得這般沉魚落雁了? 周鶯自幼失怙,被顧家收養後,纔算有個避風港。她使勁學習女紅廚藝,想討得顧家上下歡心,可不知爲何,那個便宜三叔總對她不假辭色。 直到有一天,三叔突然通知她:“收拾收拾,該成親了。” 周鶯愕然。 同時,她又聽說,三叔要娶三嬸了?不知是哪個倒黴蛋,要嫁給三叔那樣凶神惡煞的人。 後來,周鶯哭着發現,那個倒黴蛋就是她自己。 單純膽小小白兔女主vs陰晴不定蛇精病男主
25.4萬字8.18 1658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