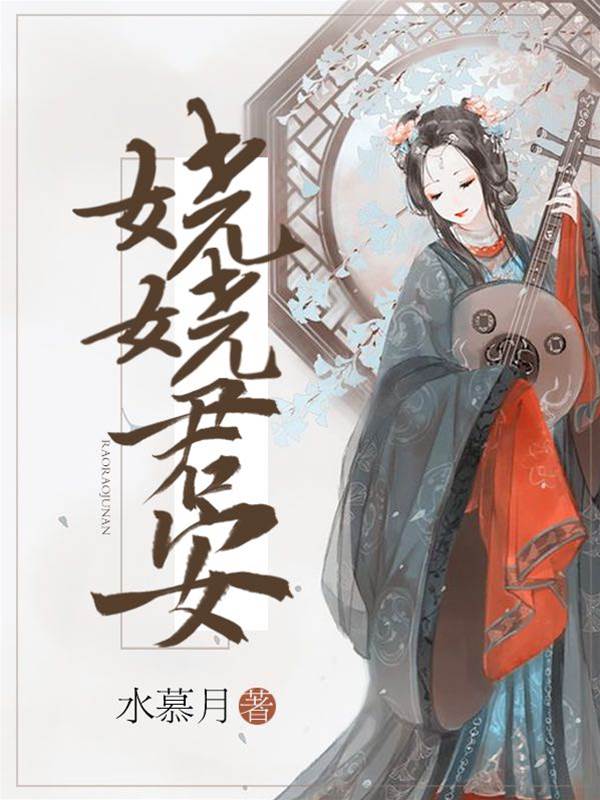《日升青鸞》 第112章 番外二_重臣攻略手冊
他這邊還在慢慢地喝,其他宴席各,青銅爵兩杯下去就是半斤酒,已經有量淺的朝臣頂不住。
眼看謝侍郎得了賜的醒酒湯,其他朝臣也紛紛向侍索要醒酒湯。
薛奪空過來,小聲問,“督帥,你還行不行?要不要給你也弄碗醒酒湯來。”
裴顯把喝空的大金樽往案上隨手一放,“不必。”
他斜睨了眼高那位。薑鸞向來行止都不怎麼規矩,年底的熱鬧慶功宴,端正坐了沒兩刻鐘就換了懶散的盤膝坐姿,托著腮,也在懶洋洋地瞄著他這邊。
裴顯抬手把薛奪招到側,問他,“今天又怎麼了?怎麼突然把半斤金樽拿出來了。”
薛奪低聲線,“聽文鏡說,早上看了督帥獻上的大禮,或許是被噁心到了,回去臨風殿就吐了一場。”
“……吐了?”裴顯一怔,抬頭又去看。薑鸞換了個姿勢,端起面前的半兩小玉杯,懶洋洋地沖他舉杯。
錦繡鸞華服的織金繡線在燈火下熠熠閃,黑漆長案遮掩住了君的平坦小腹。
電火石間,一個念頭不控制閃過腦海。裴顯的聲線難以察覺地繃了一瞬,
“怎麼個吐法?”
薛奪也是一愣。“被噁心吐了,還能有幾個吐法?反正文鏡說了,前後吐了兩,抱怨了一路,說人長了就是要說話的。那位把大金樽拿出來灌督帥的酒,估著也是和這事有關。”
裴顯默然不語,手指關節在長案上輕輕敲擊了幾下。
十二月初京。
京當日就下了詔獄,在裏頭待了五天。
京後第一次留宿臨風殿,是在登基當晚。那時已經臘月初十了。
今日才臘月二十九。
時間不對。再快也不至於。不可能是他想到的那個可能。
一時間過心底的思緒,引發了細微的緒波,說不出是期盼還是失。他擺擺手,薛奪退下了。
但心頭瞬間閃過的念頭,卻再也揮之不去,始終橫亙在腦海裏。
過了年,他就要二十七了。
家族裏有個侄子和他同歲,在河東娶妻生子,如今一雙小兒已經繞膝。
他放下金樽,再次抬頭,向丹墀之上的高。
薑鸞看膩了歌舞,正無聊地撥弄著自己的半兩小玉杯。察覺了下方長久凝的視線,詫異地回過去。
裴顯指了指面前的大金樽。
薑鸞眨了下眼,明白過來他的疑問,嗤地笑了,遙遙比劃了個‘五’。
早上猝不及防的五倍重禮,值得一個半斤金樽。
裴顯盯著面前金樽看了一會兒,思忖著薑鸞比劃的‘五’。他過侍,吩咐了幾句。
侍開始往空盞裏倒酒。
薑鸞遠遠地看著玉酒盛滿金樽,不等這邊賜酒,他那邊自己舉起金樽,開始喝第三杯。
“這麼自覺的嗎?”薑鸞納悶地和崔瀅說,“莫非裴相誤會了。以為我比劃的五,是讓他喝五杯的意思?”
“五杯就是兩斤半了。裴相剛才還和謝侍郎對飲了兩斤……”崔瀅嘶了聲,有點不放心,“今日宮宴的酒後勁不小,裴相的酒又喝得急。要不要把醒酒湯也給裴相一碗預備著?”
薑鸞把文鏡召來,“盯著點你家督帥。真喝醉了,早點把人扶下去休息。”
文鏡道,“是!”
他剛轉下了丹墀,還沒來得及盯住自家督帥,一道朱袍的修長人影出現在面前,差點和他撞了個滿懷。
謝瀾站在丹墀臺階下,視線往上,手捧一只空杯,
“臣請陛下賜酒。”
薑鸞:“……”
把人召上來,仔細瞧了瞧謝瀾的臉。
一張緋桃花面,星眸濛濛地起了霧,但嗓音清醒,一時竟不清這位是醉著還是醒著。
“謝侍郎,喝醉了?”薑鸞詫異問他,
“今日的慶功宴,慶祝的是大軍凱旋。但凡是單獨賜賞的酒,都是賜給你長兄,裴相,以及此次出征的諸位將領。你並未參與出征,為何也要單獨賜酒?”
謝瀾應聲而答,“長兄和裴相已經得了陛下賜酒。臣帶著空杯前來,請陛下賜酒。”
乍聽起來,似乎有理有據;但仔細想想,答得牛頭不對馬。
嘈雜的歌舞竹樂音裏,謝瀾舉起手裏空杯,口齒清晰地道,“去歲新年間,陛下當時還是東宮殿下,臣曾說過,殿下的將來長長久久。”
薑鸞見他雖然應對如流,但眼神迷蒙,形細微搖晃,顯然陷酩酊大醉。
“不錯,朕還記得。”薑鸞好言好語地勸他,“靜澤,你醉了。剛才的醒酒湯沒喝?回去喝了,下去睡吧。”
謝瀾不願走。
“去歲新年,臣當時說,暮去朝來,又是新春。願長伴殿下左右。今日臘月年底,眼看又是一年,臣還是這句話。”
謝瀾固執地舉著空杯,無論徐公公和崔瀅兩個怎麼好生勸說都不肯走,依舊口齒清晰地道,
“暮去朝來,又是新春。瀾願長伴殿下左右——”
薑鸞抬手了眉心。
“這是醉狠了吧?裴相剛才和他到底拼了多酒?稱呼都錯了。”
無奈把謝瀾杵到面前的空酒杯接過來,拿起案上的金壺,往裏頭倒了小半杯,塞進謝瀾手裏,安他說,
“你的耿耿忠心,我都聽見了。好了靜澤,你的賜酒在這裏,今日你喝的實在太多,趕回去歇著吧。”
謝瀾的視線迷蒙,黑曜石的眼瞳裏仿佛起了霧,盯著手裏半滿的酒杯,似乎在費力地思考。
下一刻,他又把酒杯拿起來,重新端正舉起,杵在薑鸞面前。
“區區二兩杯,賜酒都未倒滿。”他語氣平緩地道。
但不知怎麼的,薑鸞卻從那平緩語氣裏聽出了許多委屈。
薑鸞:“……”
“賜酒還得倒滿整杯,這是誰家定的規矩?”迷地問崔瀅。
崔瀅早已無話可說,眼風往謝征那邊拼命瞄。你們凱旋大軍的慶功宴上,管管你家發酒瘋的五弟吧。
謝征的坐在斜對角,翩翩歌舞的舞姬正好轉到他那,謝征被擋住了視線,沒瞧見這邊。
坐在近的裴顯放下酒杯,起過來。
“臣請登階。”
薑鸞抬了下手,允了。
裴顯幾步登上丹墀,直接把謝瀾手裏半滿的酒杯拿走。
“謝侍郎,天子賜酒,乃是臣下無上榮耀。哪有臣下強要的道理。”
他看了眼玉杯裏的清酒,隨手塞給徐公公。
徐公公站在兩步外,愕然抓著酒杯。謝瀾的注意力果然被吸引過去,往徐公公方向走過半步,手就要拿回酒杯。
裴顯卻搶先一步,把玉杯又拿回來,當著謝瀾的面,把那半杯賜酒喝了。
謝瀾:“……”
謝瀾出了吃驚的表,薄幾度開合,似乎想說話,大醉之中卻又不知說些什麼,站在原,直勾勾地盯著空酒杯發愣。
一個朝廷副相,一個吏部侍郎,眼前場景令人無語凝噎,崔瀅不忍直視,索轉開了臉,眼不見為淨。
薑鸞瞧得又納悶又好笑,“你欺負他一個喝醉的人做什麼。不就是半杯酒。”
徐公公眼疾手快遞過來一個空杯,薑鸞把空杯連同案上的金酒壺都推到裴顯面前,
“你把謝侍郎的酒拿過去喝了,你自己給他再倒一杯,做個補償吧。”
裴顯並不開口分辯什麼,直接奉命倒酒。倒得不多不,正好是剛才半杯酒的高度。
在眾目睽睽之下倒完了酒,他拿過酒杯,不是往前推過去謝瀾面前,居然端起來,自己又一口喝幹了。
薑鸞:“……”
剛才裴顯搶喝了給謝瀾的半杯賜酒,行事不太像他平日作風,薑鸞就有幾分懷疑。如今懷疑幾乎可以確定了。
神一振,立刻坐直,上上下下、饒有興致地仔細打量裴顯此刻的神,
“裴相,你也喝醉了?半斤的大金樽,剛才喝了幾杯?”
“五杯,涓滴不。”裴顯以極冷靜的口吻說,“臣沒醉。臣還能再喝五杯。”
薑鸞忍著笑,召薛奪過來說話。
“你家督帥今天喝了三斤半。半斤的大金樽喝了五杯,剛才和謝侍郎拼酒喝了一人喝了一斤。我看他醉了。”
薛奪吃了一驚,急得跳腳,“今天喝的何止三斤半!謝侍郎過來和督帥拼酒之前,全場赴宴的文武將早敬過兩了。二兩酒的玉杯,來者不拒,喝了至三五十杯!”
薑鸞估算了一下,二兩杯,八杯就是一斤酒。
自己都忍不住嘶地倒吸涼氣,“這是喝了七八斤烈酒了?徐在安,趕端碗醒酒湯來。”
猜你喜歡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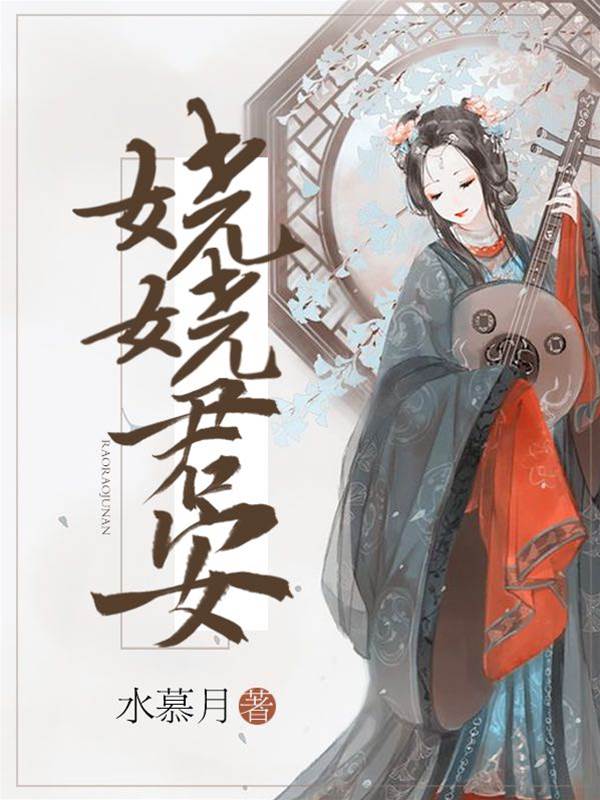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001 -
完結244 章
綺夢璇璣
腹黑王爺與烏龜美女大PK。過程輕鬆小白,結局保證完滿。美女,身爲一代腹黑大BOSS的王爺趙見慎見得多了,沒見過謝璇璣這麼難搞定的…利誘沒有成效,雖然這個女人愛錢,卻從不肯白佔便宜。送她胭脂花粉首飾珠寶,拿去換錢逃跑。甚至許以王妃身份她都不屑一顧。色誘是目前看來最有效的,可惜還是次次功敗垂成。對她溫柔,她懷疑他有陰謀。對她冷淡,她全無所謂。對她刁難,基本上都無功而返,任何問題到了這個女人面前都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解決。這個女人對他的迴應就是一句:“除了金銀古董,別人用過的東西我都不要!”
53.8萬字8 26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