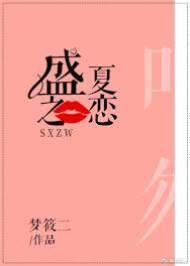《被綠茶搶婚後,頂級財閥為我撐腰》 第115章 你是什麼時候看上江晚的?
我從他懷裡微微退出一些,扭頭看向自己膝蓋。
可淚眼模糊,看不清楚。
蘇盛臨低頭瞧著我,竟出笑來:“還哭了?有這麼恐怖?”
我心裡恨他,恨他架著我遭這樣的“酷刑”,所以也不想理他。
他也不介意,從兜裡取出手帕遞給我:“自己還是我給你?”
我嘟著,恨恨地一把奪過手帕,眼淚。
等緒平復一些,我正想推開他假裝下堅強,結果醫生又上手,“針要一,放心,不疼的。”
我看著那細細的鋼針拉扯著紅腫的皮,在醫生手裡上上下下地起伏,生理上便本能恐懼,忙扭頭又埋進他懷裡。
“痛……嘶——”
蘇盛臨好像還在笑,因為我察覺到他腹部的震了。
“醫生,輕一點。”他低聲提醒。
“作很輕了,會有點酸酸脹脹的覺,是正常的。”醫生回覆。
我沒理會,因為本沒法說話,是忍那種難都耗盡了我的力氣。
治療持續了四十分鐘,我就抱著蘇盛臨狂落淚了四十分鐘,把他腹部的服都浸溼了。
最後等治療完,他看著服上的水印子,竟還有心思開玩笑:“我要是腹部著涼,就是你眼淚的功勞。”
我眼眶還是溼潤的,抬眸瞥他,此時的我,肯定淚眼汪汪又楚楚可憐。
我不滿地埋怨:“看我罪,你好像開心的,有沒有點人。”
他稍稍正,角斜斜一勾,狀似冷哼,“跑出去玩兒,不跟我代一聲,這就是報應。”
“……”我抿,無言以對。
離開醫院,已經是深夜十一點了。
我依然不能走路,蘇盛臨又把我抱回車上。
我也懶得掙扎了,反正剛才都抱著他哭了那麼久,現在再來撇清關係,太矯做作了。
“怎麼弄?是送你回家,還是去我那兒暫住?”
蘇盛臨坐上車後,看向我問道。
我耳子一抖,臉也驚呆,瞪眼看向他。
去他那兒暫住?
什麼意思?
這就直接“同居”?
察覺到我誤會了,蘇盛臨連忙解釋:“你別多想,我只是覺得你需要人照顧。”
我眨眨眼回過神來,低聲說:“回家,我自己可以的,實在不行,我找朋友過來。”
我跟顧宴卿的離婚案還沒塵埃落定,就算這時候我不抗拒跟蘇盛臨的來往,但“同居”這種事還是萬萬不能的。
這是原則問題。
蘇盛臨看著我,片刻後淡淡一笑,“行,那送你回去。”
路上,我昏昏睡。
白天一直被疼痛困擾,剛才治療時又神經繃,這會兒疼痛緩解,放鬆下來,我只覺得疲力盡,眼皮撐不住地打架。
“想睡就睡會兒,到了我你。”在我又一次瞌睡驚了下後,蘇盛臨的語調溫傳來。
我看了他一眼,連話都沒說,頭一歪徹底睡去。
迷迷糊糊中,我搖晃的腦袋有了支點。
濃濃的睏意讓我眼皮都懶得抬起,就很放心自然地把重量靠了過去。
路上睡了多久我不知,但就覺得醒來時,心裡格外踏實。
那短短一夢,香甜而心安,不知道是不是靠著蘇盛臨的緣故。
“能不能走?”車停穩,蘇盛臨先下車,繞到我這邊來開啟車門。
我抬覺了下,連忙道:“可以走的,針灸後好些了。”
不得不說,蘇盛臨出面找的醫生,確實醫了得。
那針灸看著恐怖,但效果奇佳,做完一次治療便覺得疼痛明顯好轉。
蘇盛臨應了聲,站在車門邊,等我挪下來後,小心翼翼地扶著我。
我走得很慢,他一手拎著藥,另一手鉗著我的胳膊。
短短幾步路,我挪了好幾分鐘。
上樓進屋後,他還是不放心:“你晚上洗漱,上廁所什麼的……一個人能行嗎?”
我心想,就算不能又怎樣?難道你要留下來幫我洗漱?扶我上廁所?
這話我說不出口,只能很有自信地回答:“可以的,放心吧。”
“那我走了?”
“嗯……”
我點頭答應,站在那裡。
因為腳不便,我就沒有再去門口送他,隻眼地看著他,心裡琢磨著一些東西。
蘇盛臨看了我幾眼,想必還是不放心。
但以我們目前的關係,他肯定也說不出留宿的話。
上次我醉酒,那是意外。
現在兩人都是清醒的狀態,他若留宿一夜,誰都不能保證會發生什麼。
氣氛短暫尷尬之後,他轉朝門口走去。
我心裡一急,下意識出口:“哎!”
他應聲回頭,臉似有起伏,“怎麼了,還有事?”
“我……”我吞嚥了下,看著他,雙手不自在地攪了攪,低聲道,“今天早上,那會兒你生氣了吧……我,對不起……我應該提前跟你說一聲的。”
蘇盛臨轉過來,正正地面對著我,但沒有朝我走近。
那張英俊的臉龐神平靜,連眸都斂深邃。
他盯著我,思忖片刻,低聲問道:“能告訴我,你這幾天又刻意對我疏離,是因為什麼原因?”
我一怔,眸停滯。
原來他又察覺到了。
也是,敏銳聰慧如他,怎麼可能覺不到。
他追問:“是因為二審沒到你為了避嫌,還是有誰跟你說了什麼?”
我心裡怔愣更甚。
他太聰明!
居然猜到是有人跟我說什麼了。
我越發糾結為難,想到小姨跟外婆的話,想到圈子裡最近關於我的種種風評,心裡左右拉扯。
“蘇盛臨,你說得對,我是膽小鬼……我認真思考過,我們之間差距太大,就算你不在乎,你家人也不在乎,可我們的關係一旦確定,一旦公開,外界會有很多流言蜚語,這對你和你的家族都很不利。”
蘇盛臨皺眉,邁步走向我。
淡淡的迫頓時朝我襲來。
可我不能,所以心在後退,雙腳依然困在原地。
他走到我面前兩步遠的地方停下,英的眉宇間出濃濃困和不解:“我的生活,為什麼需要外界公眾的認可?”
“不是說需要外界認可,而是至我不能給你抹黑,讓人淪為圈子裡的笑柄吧,否則我心裡……很難。”我努力解釋,但發現找不到合適的語言描述。
我覺得,但凡我不那麼喜歡他,我都不會考慮這麼多。
此時此刻,我總算明白那句——喜歡是佔有,是剋制。
我對蘇盛臨的,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裡,超越了我對顧宴卿六七年的相。
我上他了,才會如此戰戰兢兢,患得患失。
我不知該說自己移別太快,還是蘇盛臨魅力太甚。
“你這麼優秀,怎麼給我抹黑?”他抬手,竟在我臉上了,很寵溺地笑了笑,“江晚,適當地自私些,你會活得更幸福。”
我抬眸仰視著他,心裡的堡壘又在持續垮塌。
“不早了,你趕洗漱下睡吧,明天我再來看你。”他過我的臉之後,大掌落在我肩上微微了,低聲代。
我點點頭,“嗯,那你快回去吧。”
我著他轉離開,關上門後,才長長吐出一口氣,就近在餐桌邊坐下。
雙依然疼,但因為疼了一天,已經有點麻木了,痛苦程度比白天緩解不。
天冷,也懶得洗澡,我簡單洗漱了下,艱難地挪到床上,把兩條搬上床,緩緩直,直地躺下。
————
翌日一早,我醒來就看到微信上的未讀訊息。
蘇盛臨在七點鐘給我發了資訊,問我早餐吃什麼。
我雖然很這種關心,但又覺得麻煩他越多,就欠他越多,以後就更加還不清了。
於是,我回復:【李雲微今天過來,你先忙自己的事吧。】
訊息發出去,我心裡又忐忑不安。
覺得這話會不會又讓他生氣啊?認為我又在疏遠他……
手機突然響起,他打來電話了。
我遲疑了兩秒,接通:“喂……”
“你確定跟朋友說了,朋友去照顧你?”
“嗯,我昨晚就跟說好了。”其實我還沒來得及說,但只有這樣“撒謊”,他才能放下擔憂吧。
“行,那我就先去公司,等忙完工作去接你,你今天還要做治療。”
我一驚,這才想起今天還要去醫院做中醫理療。
“那個……我覺得今天好多了,能不能不去了?”我實在害怕針灸,回想那幅畫面就心驚跳。
“不行,你這傷若不能徹底治好,留下病以後就麻煩了。”他嚴詞拒絕。
“……”
“大概十點左右,我過去接你。”
“好吧……那你先忙。”
掛了電話,我想著還要做針灸,抱著枕頭哀嚎,哭無淚。
心煩悶,我還是跟李雲微說了自己倒黴催的破事。
李雲微得知,馬上趕來家裡。
看到我摔這麼狠,一臉瑟心疼:“你今年可真是倒黴了,找個時間去廟裡拜拜吧,轉轉運。”
我好奇問道:“有用?”
“哎呀,心誠則靈嘛。”
我一笑而過。
我更相信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
李雲微陪我吃了早餐,得知蘇盛臨會來接我去醫院做治療,免不了又是一番調侃八卦。
上午十點半,蘇盛臨果然準時出現。
李雲微太勇了,看到蘇盛臨進屋直接開門見山地問:“蘇先生,您是什麼時候看上江晚的?”
猜你喜歡
-
完結2295 章

都市至尊聖醫
一代武神葉修,靈魂重歸故鄉, 歸來時,重生日,兩世仇人,以牙還牙! 上一世,他慘遭綠茶未婚妻殘害,含恨而死。 這一世,守護親人,登頂神位! 逆天功法,至尊寶具,最強修為,唾手可得! 縱橫逆天霸血,登上至尊神座。 葉修微微一笑,“有些人血中有風,注定要漂泊一生······”
427.2萬字8 35916 -
連載1087 章

財閥小千金:老公,我吃定你了
首富唯一繼承人還需要聯姻?還是嫁給穆樂樂的死對頭?! 穆樂樂不舍得氣死爺爺,但舍得氣死老公! “總裁,太太新婚夜去酒吧。” 晏習帛:“卡停了。” “總裁,太太準備給你帶綠帽子。” 晏習帛:“腿砍了。” “總裁,太太準備和你離婚。” 辦公室一瞬間的沉默,晏習帛問:“她想懷四胎了?” 最初,穆樂樂用盡了各種辦法想離婚,后來,她在追逐離婚的道路上,逐漸迷失了自己。 本以為,穆家半路撿來的孤兒包藏禍心,欲要獨霸穆式集團。后來才發現,他煞費苦心只為了她。 穆樂樂當初寧可相信...
185.9萬字8.18 24479 -
連載400 章

訂婚宴,陸總偷偷勾她尾指
[又名:訂婚宴,被前任小叔親到腿軟]、[京圈佛子強勢上位!]京圈太子爺陸野的未婚妻顧言驚豔、勾人、脾氣好,圈內皆知有陸野的地方必有顧言,某天,聽說顧言提了分手。陸野散漫,“說了她兩句重話,不出三天,她會自己回來。”三天又三天。陸野醉酒沒人接,忍不住撥了顧言號碼,竟然被拉黑了。有八卦拍到顧言被神秘男人送回家,陸野驀地心裏空了一塊。後來,聽說陸野不顧暴雨狼狽,偏執的在前女友家門口站了一夜。第二天,那扇門終於打開。“言言!我想你…”一抹頎長的身影裹著浴巾走來。“小叔?……言言?”那個驕矜尊高的男人攬顧言入懷,睨向陸野,“你該改口了。”—那晚,顧言把陸野的小叔給睡了,第二天她又怕又後悔,轉身就逃。她辭了工作,換了住處。電梯遇到他,她假裝等下一趟。直到她在酒吧與人相親,直接被人擄走。逼仄的小巷,沉重的氣息侵入,強吻,“再跑,腿打斷。”—他一步步誘她深陷,怎麼可能逃出他手掌心。
70.5萬字8.18 27891 -
完結1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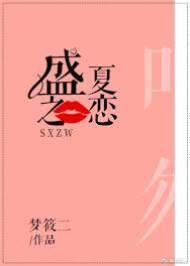
盛夏之戀
那天,任彥東生日派對。 包間外走廊上,發小勸任彥東:“及時回頭吧,別再傷害盛夏,就因為她名字有個夏沐的夏,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任彥東覷他一眼,嫌他聒噪,便說了句:“煙都堵不住你嘴。” 發小無意間側臉,懵了。 盛夏手里拿著項目合同,來找任彥東。 任彥東轉身,就跟盛夏的目光對上。 盛夏緩了緩,走過去,依舊保持著驕傲的微笑,不過稱呼改成,“任總,就看在您把我當夏沐替身的份上,您就爽快點,把合同簽給我。” 任彥東望著她的眼,“沒把你當替身,還怎麼簽給你?” 他把杯中紅酒一飲而盡,抬步離開。 后來,盛夏說:我信你沒把我當替身,只當女朋友,簽給我吧。 任彥東看都沒看她,根本就不接茬。 再后來,為了這份原本板上釘釘的合同,盛夏把團隊里的人都得罪了,任彥東還是沒松口。 再再后來,盛夏問他:在分手和簽合同之間,你選哪個? 任彥東:前者。 那份合同,最終任彥東也沒有簽給盛夏,后來和結婚證一起,一直放在保險柜。 那年,盛夏,不是誰的替身,只是他的她。
25.4萬字8.18 76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