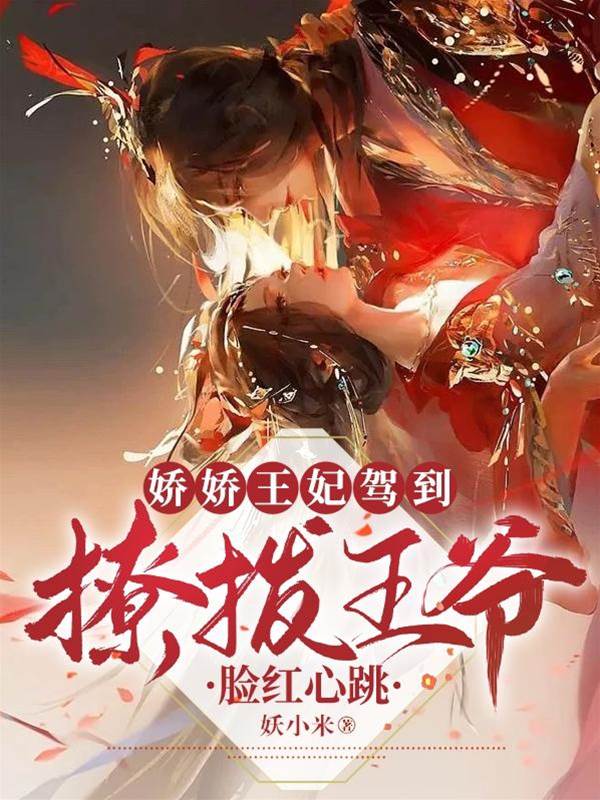《夫人救命,將軍又有麻煩了》 第357章 開誠布公
「開戰?」宇文晟並沒有因為鄭曲尺這一番可謂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話而神失常,反倒有一種順從著的意思去思索的意思:「你想怎麼開戰?」
鄭曲尺一說起這個,便轉過,正襟危坐起來:「以前都是鄴國承別國的欺辱榨,但這一次咱們鄴國主發起戰爭,你不是書信與我常聊邊關之事,常叔也與我分析過,蠻夷部落時常擾邊境,兵駐守與剿滅,便如治水一途,經防不圩堤,遲早會潰決。」
「嗯,說得很好。」他笑意盈盈地凝視著。
鄭曲尺沉浸在自己的思緒當中:「我認為,與其防,不如主出擊,蠻夷欺我鄴國勢弱,便如其它六國一般,我便想著乾脆抓住這一次機會,給九洲諸國一個嚴厲的警告!侵我國者,絕不容怠,哪怕殊死一戰,亦要展我國威。」
說得很是振與用力,彷彿這些話已經醞釀在心底許久,今日一吐為快,以往憐其工匠歧視,後來見識過更廣闊的地方,便哀其國家不爭墮落,憫其百姓陷於苦難無法自救……
不偉大,可以說是宇文晟一步一步將推至到如今這個地位、這個境的。
這些時間時常會回想過往,他不曾坦與待的那些過往。
會想,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便計劃著想要一生的?
他想要陪著,不樂意,他便拿一個國家來「綁架」,為了讓與他一起去面對這個千瘡百孔的鄴國,為此他都私下都做了些什麼?
或許他一開始給過選擇,選擇做一個小人,去當一個擁有自由、擁有自己一片小天地的普通人,只可惜命運卻沒有給選擇,無論怎麼走,都會被推到他的面前,然後落他的「掌心」中。
掙扎過了,「和離」是曾一度執著堅持的想法,以為沒有了他,就能夠生出翅膀,翱翔千萬里的天空,但他卻以事實告訴——不能。
他以一種絕對深刻而狠的方式失去了他,同時也是將淋淋一般的殘酷世界展示在的眼前。
在彷徨無助之際,他又將「矛」與「盾」通過離開的方式送到了手上,讓在失去了他的庇護同時,自己也擁有了武與護盾。
這個時候的,終於從被守護者,變了守護者。
曾經的如履薄冰,變了堅實堅定,有了力量,有了自信,有了自己……是的,這個時候的,才真真正正的是自己。
為什麼在面對宇文晟與元星洲兩人,的心態截然不同?
明明都是曾經需要仰的權力者,但前者唯唯諾諾、極力想要逃跑,後者卻能夠談笑風聲、平等而視之,其實人沒有變,都不是什麼善類,變的只是。
不再像一片被風吹著走的飄零落葉,也不是沒有系的隨水而飄的浮萍,在一點一滴的扎駐進了這片大地,與周圍人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聯繫,至此終於領悟了自己的存在價值與意義。
所以,哪怕知道元星洲是易容的宇文晟時,的第一反應只是不解、茫然,而不是被欺騙后的怨懟、被愚弄的氣惱,當然事後反應過來,該氣還得氣,但正因為這段時間的長、強大與獲得,讓長出了一顆緒穩定而堅強的心。
只有擁有很多的人,才能夠以包容之心去看待尖銳不公之事,以往生活一地,還隨時於危機當中的,肯定只會以尖刺去。
冷靜的思量所經歷的一切是不是自己活該,這一路走來的過程,是好、是壞,是值得還是冤枉……最後,看到了一個完好且寧靜的自己時,知道,沒有白走這一遭路。
這麼幾年了,他一直不肯回去,反而像是駐紮在了邊疆之地,不顧生死連年赴戰,傷痕纍纍,跟懲罰著自己一般過著苦寒放逐的日子。
也一直專註忙著的事業,不知疲倦,不分晝夜。
他們之間的距離隔得很遠,時間也不曾被對方佔用過,只偶爾通信一封,但這樣的相卻有一種莫名的默契。
他在等,知道。
一直不肯對他的等待屈服,不肯妥協。
但一旦最初那子怒氣被時間耗了,便開始在意起時間的流逝了,在聽聞他險些就戰死沙場時,明白……撐不了多久了。
「你就這麼想我戰死沙場,當一名寡婦?」他揶揄道。
鄭曲尺白了他一眼:「你胡說些什麼呢,我夫君早就死了,我本就是一名寡婦。」
宇文晟見眉宇間無端蓄起的慍怒,便也不拿這事打趣了:「你是認真的?」
當然是認真的。
要接他,還有那些長年苦戰在邊境的將士們一起回家,所以這一戰,是極為認真的看待。
「是,殺儆猴這個道理我們都懂,我們要以強有力的鐵腕手段來打破別人對鄴國的固有印象,就像拿一個卵石頭,所有人都會認為卵必碎,但咱們卻要以卵石頭,碎的卻是石頭!」
宇文晟直視的眼睛,慢悠悠道:「看來,你是有備而來的。」
「嗯,我特地來這裡只是想問一問你,敢不敢跟我拼一拼。」問道。
宇文晟也答得爽快:「我與你早就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了,有何不敢?」
「萬一輸了呢?你不擔心你好不容易搶到手的江山,就這樣丟了?」鄭曲尺有意試探他一句。
宇文晟眼神何其敏銳犀利,哪怕他刻意在鄭曲尺面前掩藏了令人害怕的察力,可當他微微瞇起眸子,依舊有一強勢之氣流溢而出。
「你忘了我說過,我的目的只為復仇,本就不在乎這個國家會變怎麼樣,只是因為你想要它存在,那便才是我願意它繼續存在的原因。」
他講得很直白,鄭曲尺也聽得很明白。
事到如今,也不妨將過往發生的那些事徹底說。
「行,正事我們已經談妥了,接下來就該你兌現你當初的承諾,你說過你只要活著回來,便會告訴我一切,現在你不僅活著,我還自己過來了,所以你是不是該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
宇文晟靠坐在墊上:「你想知道什麼?」
「當初你的死,是設計好的嗎?」鄭曲尺想都沒想問出。
「是。」他頷首。
饒是鄭曲尺以為自己有了一定心理準備,便能夠跟他平靜地談話下去,但此時還是忍不住怒了。
「從你當初在虎嘯關帶走我開始,到最後關頭放過公輸即若,你刻意調走所有兵力護送王澤邦他們帶著報回家,一路引來各路人馬追殺,然後……死於巨鹿軍與公輸即若的人共同獵殺,只為了將你的死變得理所當然,更有說服力對嗎?」
他輕聲道:「嗯。」
看著他那一張可惡的面臉,鄭曲尺費解:「你的死,究竟是為了算計誰?」
這一次,死魚一般的宇文晟神有了不一樣的變化,他薄輕啟,吐出一個字:「你。」
鄭曲尺怔然。
也是萬萬沒想到,會等到這麼一個答案。
「不是為了金蟬殼回王宮奪位嗎?」一直都是朝這方面去猜測的。
然而宇文晟卻微笑著道:「你以為憑鄴王那個豬一樣的腦子,以及鄴后那低劣不堪的下作手段,需要我這般大費周章詐死?」
鄭曲尺本該嚴肅的腦子忽然宕機了一下,下意識口:「不是,我覺得,我還比不上他們倆,你幹嘛這麼大費周章地來算計我啊?」
雖然這話貶低了自己,可這是實話,在宇文晟那兒看不上眼的劣把戲,擱鄭曲尺這裡就是高端作,換的話,分分鐘被玩死幾百次了。
「說算計或許不準確,應該是想看一看,我若死了,你究竟會怎麼做。」
「你這話什麼意思?」
「一對夫妻,一個死,一個生,有人選擇為其殉,有人選擇拋下一切另謀嫁娶,也有人選擇孤獨一生,更有人選擇瘋狂報復,我很好奇,你會怎麼做。」
「我不殉,也不另嫁,更不會癲狂報復,我只會好好的活著,餘生好好為我的事業發發熱。」就這況,哪款都屬實構不上、犯不著、不至於。
宇文晟本該是滿意這個答案的,可他又卻不太滿意這個無所謂的樣子。
「其實我一直在你的邊,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裡……說真的曲尺,我本無意與任何人糾纏一生,起初我打算在毀了了一切之後,放了你,隨你來去。」
他當著的面摘下了面,出了那一張屬於宇文晟的殊麗瓷白的臉,深紅的,幽深漆黑的眸子,他欺近——
「可或許是我太高估了自己,我本就是在自欺欺人罷了,從我選擇送上去參加霽春匠工會開始,我便謀了私心,開始了一切……」
宇文晟起了的下,風清雲淡的眼神終於被撕開了掩藏,出了底下的狼子野心與貪婪侵襲。
「我並不想你看我,因為我知道,一旦你知道了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你絕對會到噁心、厭棄,你會逃,於是我寧可捨棄掉屬於宇文晟的一切,我可以永遠為鄴國世子元星洲……」(本章完)
猜你喜歡
-
完結1055 章

侯府小啞女
燕云歌自末世而來,重生侯府,她給自己定了個小目標:每天吃好喝好樂無憂!然而……她爹一門心思造反,她哥一門心思造反,她嫁個男人,還是一門心思造反。燕云歌掀桌子,這日子沒發過了!
272.1萬字8 16625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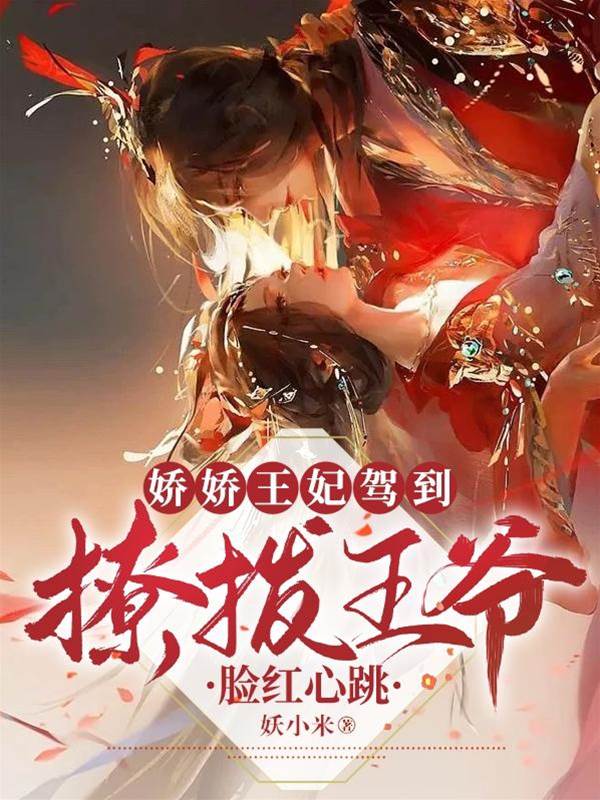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1698 -
完結372 章

穿成短命白月光后,和反派HE了
桑遠遠穿進一本古早玄幻虐戀小說裏,成了男主那個紅顏薄命的早逝白月光。男主愛她,男配們也愛她。女主因爲長了一張酷似她的臉,被衆男又愛又虐又踩,傷身又傷心。和男主的感情更是波折重重狗血不斷,虐得死去活來,結局還能幸福HE。桑遠遠:“不好意思本人一不想死二受不得虐,所以我選擇跟反派走。打擾,告辭。”反派長眸微眯,姿態慵懶,脣角笑意如春風般和煦——“我的身邊……可是地獄呢。”她沉思三秒。“地獄有土嗎?”“……有腐地。”“有水嗎?”“……只有血。”他想看她驚惶失措,想等她尖叫逃離,不料女子呆滯三秒之後,雙眼竟然隱隱放光——“正好試試新品種!”“……”他在最深沉的黑暗中苟延殘喘,從來也沒想到,竟有一個人,能把花草種滿一片荒蕪。
57.1萬字7.92 9525 -
完結313 章
亡國后成了反賊的寵婢
姜嶠女扮男裝當了幾年暴君。叛軍攻入皇城時,她麻溜地收拾行李,縱火死遁,可陰差陽錯,她竟被當成樂伎,獻給了叛軍首領霍奚舟。姜嶠捂緊馬甲,計劃著再次逃跑。誰料傳聞中陰煞狠厲、不近女色的霍大將軍竟為她破了例。紅燭帳暖,男人摩挲著她眼角的淚痣,眸色暗沉,微有醉意,“今夜留下。”*姜嶠知道,霍奚舟待她特殊,只是因為她那雙眼睛肖似故人。無妨,他拿她當替身,她利用他逃命。兩人各有所圖,也是樁不虧的買賣。直到霍奚舟看她的眼神越來越深情,還鄭重其事地為允諾要娶她為妻,姜嶠才意識到,自己好像是在作繭自縛——
49.2萬字8 68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