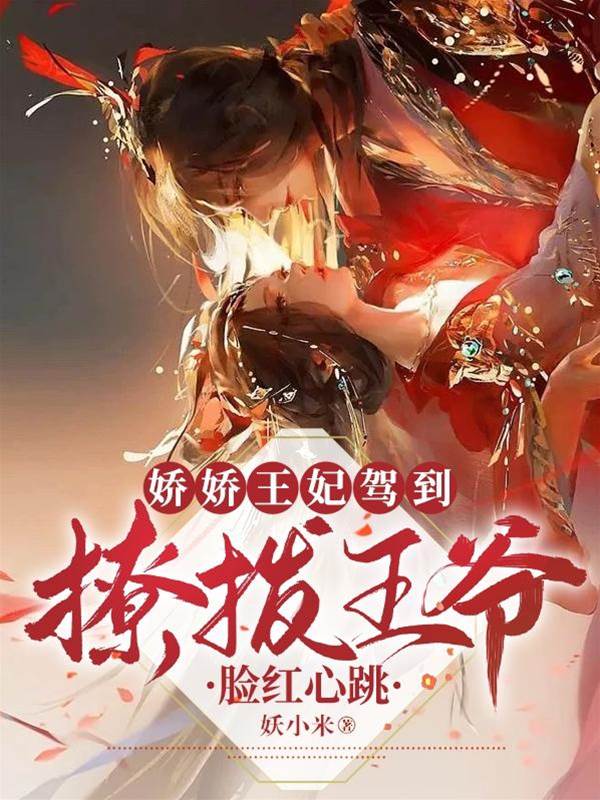《嫤語書年》 番外 徐後
“……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祗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
宗廟的大殿上,奉常陳徵聲音響亮,將禪讓詔一字一字唸完。
話音最後落下的時候,只聽低低的哭聲淅瀝一片,我看去,著素的宗族人等跪在地上,神容悲慼。
而我的前,天子神平靜,彷彿陳徵唸的不過是他此生聽過的所有詔其中之一。
哦……或許我不應再稱他爲天子,因爲禪讓詔剛剛宣讀。
我向階下,那些站立在殿殿外的朝臣,有人悲慼,有人平靜,他們的臉,我從前可能見過,但是將來,我大概再也不會見了。
還有正前方的那人。
十二冕旒,玄纁裳,新繡的紋章斐然。不得不承認,這裳穿在他的上,別有渾然的氣勢。
終於結束了麼?
莫名的,我上一陣輕鬆。
我姓徐,徐蘋。
我的母親曾告訴我,在我五歲那年,曾有相士到家中來。他看我的面相,說我有貴極之氣,日後可爲皇后。我的父親很高興,給了那相士一金。
此事只在大人們的口中津津樂道了兩年,因爲沒多久,父親升任府,帶我們一家去了長安。
長安很大,人也很多。
當我第一次站在大路上,看到馬車飛馳奔來,嚇得大哭。
父親和母親卻很喜歡這裡。我家中的境況富足,幾乎每隔幾日,父親便會在家中邀請同僚聚宴,母親也會帶著我到各與長安的貴眷們相識。
我長得不錯,也不錯。這是許多人都認可的,於是,我的朋友也多了起來。
們和我一樣,都是些宦家的兒。不過,們大多世長安,比起來,我便並不那麼出。們說的話,有時我聽不懂,們的架勢,也總教我到不適。
母親曾鼓勵我,不管自己從前生活在何,如今我是府的兒,便不會矮任何人半分。
“蘋將來也許會做皇后呢。”姊姊笑著說。
我哂然,心中覺得可笑又疑。皇后是什麼樣?我這樣麼?
母親並不理會我的這些怯懦,仍然帶我去各種地方,見各種人。我學著用們的口音說話,像們一樣舉止優雅,無論何人,高傲的、溫和的、吵鬧的、俏皮的,我都微笑以待,遇到爭執,也從不生事。等到我十四歲的時候,有一次姑母從汾老家來到,拉著我驚歎說:“幾年不見,蘋可是個長安人了。”
這話,我聽著有幾分自得。
說的是確實,如今的我,已經是個正宗的長安貴。
每到與姊妹們出遊,我的馬車後面總有年輕的紈絝子弟悄悄尾隨。而我的那些朋友之中,也有幾個曾悄悄地告訴我,們的某個兄弟對我有意。
當然,這些事也只能藏在心裡,無人之時拿出來想想覺得。徐氏在汾乃是大家,我的父親和母親,一直盼我能嫁長安的貴家。
“我要嫁投意合之人。”我對母親說。
母親卻不以爲意地笑笑:“是麼?那你告訴我,如何算得投意合?”
“就是我喜歡他,他也喜歡我。”
母親又笑,我的頭髮,意味深長:“你怎知道他也喜歡你?”
我想說那還不簡單,可仔細再想,卻發現答不上來。
沒多久,姊姊悄悄地跟我說,父親看中了傅司徒的長子,可惜他上月已經娶婦,剩下次子,父親也覺得不錯。
傅氏大名,我當然聽說過。淮南傅氏,天下響噹噹的大族,世長安。到傅司徒這一輩,家中做到九卿的人已經有十幾,而傅氏的家宅,就在貴胄雲集的城北。
我的父親雖是府,但是城北對於我們而言,是可不可即的。那裡住著的都是天下最有權勢的人,的確是父親的理想之選。
姊姊的話很快落了實,過兩日,我們闔家外出踏青,途中巧遇到了傅氏一家,父親人緣不錯,於是結伴同行。
我覺得赧,見到傅司徒的次子傅筠,也只敢隔著車幃瞥一瞥。
他長得很俊氣,騎在馬上風度翩翩,笑起來亦是迷人。他神悠然,與旁人說笑,未幾,卻又策馬奔至一輛安車邊上,笑著說了句什麼。
我看到車幃掀開一角,出半張臉來。那張臉我認得,是傅司徒的小兒,傅嫤。
傅嫤我也知曉,好幾次與貴們遊苑,我都曾遇到過。雖年,卻是公認的人坯子。不過以類聚人以羣分,長安的這些貴們也不例外,傅嫤的出比我更高更好,玩伴也無一不是貴胄之家。
傅嫤看著的兄長,似乎被逗笑了,明眸櫻脣,上穿著藕的服,襯得甚是俏。
車馬一路到了灞水邊上,只見綠柳青鬱。此地,已經案席俱全,錦帳疊疊。一名年從林間走出來,見到傅司徒等人,微笑行禮。
我看到他,倏而愣住,幾乎忘了子不可直視他人的禮數。
那是裴潛。
長安中最負盛名的貴家子弟,同齡貴們每日都要將他談論上幾次,而他每回與我們偶遇,都會引起突如其來的寂靜,然後一陣興的……我對他雖久聞大名,也覺得他長得賞心悅目,可是我並不像一些子那樣迷。因爲我知道,就算我也算高門,同他共一城,對於我這樣的人而言,他還是遙遠得像天邊的星辰。
因爲裴潛和傅嫤,在時就已經訂下了婚約。
不過,能與裴潛共宴遊玩,已經是一件教人歡欣的事。
他和傅嫤的兄弟們坐在一起,談笑風生。那般灑的模樣,是我從前匆匆一瞥不曾見過的。我還留意到,他每說到些有趣的事,都會往傅嫤那邊看看,似乎在打量高興不曾。
行宴小憩之後,衆人到水邊散步。我看到裴潛和傅嫤走在了一起。
他們其實看起來並不合襯,裴潛個子高出許多,而傅嫤還是個未長開的孩子。可是裴潛跟說話的時候,微微低頭,神間帶著幾分寵溺。頃,他像是說了什麼惹得傅嫤嗔惱,手往他臂上了一下,裴潛那張被許多人稱讚俊雅無雙的臉上,竟笑得似得逞一般。
“真是好事都讓佔了,是麼?”姊姊在我耳邊低語道,滿是嘆。
我笑笑,面上不以爲意,可一直到回家,我的腦海裡還想著那兩人在一起的樣子。
心中並非不羨慕,投意合,說的大概便是如此吧?
傅筠的事沒了下文,不過幾日後,父親回到府中,神卻有些不快。
“魏傕要來長安。”他對母親說。
“魏傕?”母親想了想,道,“夫君幫過的那個北部尉?”
“正是。”父親道,嘆口氣,將一封信擲在案上,看看我,“父親親自來信,要將蘋許給魏傕的兒子。”
此事,我到愕然,母親更是忿忿。
魏氏出河西族,與徐氏是故。魏傕的父親和我的祖父當年同朝圍觀,相甚好。而魏傕亦與我的父親有年之誼。但是,這遠遠不夠。
魏傕先前在任北部尉,曾得罪權貴,我父親多方幫助才得免罪。如今,他到長安爲,也不過是個騎都尉,比起父親有意結的京城貴胄,簡直不值一提。
無奈祖父畢竟是祖父,父親再不願意,也不敢違抗。
兩個月以後,魏傕一家來到了長安。他們舉家登門拜訪之時,我見到了自己那個傳說中的未婚夫——魏郯。
這一年,我十四歲,而魏郯與我同齡。
若論長相,他當然不及裴潛或者傅筠那樣雕琢般細。他的五很有些棱角,卻不突兀,看起來竟也十分英俊。當我第一次見到魏郯的時候,他立在魏傕後,眉宇神氣昂藏,教我眼前一亮。
我和魏郯的婚約,在我十八歲的時候定下了。父親一直以相士說我不宜早婚爲由拖延,卻奈何不得祖父催促,我的年紀也已經不能再拖了。
從相識到定婚,我和魏郯已經不算陌生。
母親告訴我,與魏郯定婚是權宜之計,若遇到時機,父親還是會退掉。
我並沒有把這話太放在心上。因爲對於這個未婚夫,我覺得還算合意。魏郯來到長安之後,不到兩年,就憑本事爲了年羽林郎。每當我與貴們到宮苑中游玩,年羽林郎們騎馬執戟奔過宮,總能引得不人顧盼生輝。
而他們之中,魏郯無疑出類拔萃。同是一的鎧甲,他能比別人穿得多出幾分颯爽之氣;天子常常在宮中讓羽林竟武或蹴鞠,魏郯也總能搶得頭籌。
猜你喜歡
-
完結1055 章

侯府小啞女
燕云歌自末世而來,重生侯府,她給自己定了個小目標:每天吃好喝好樂無憂!然而……她爹一門心思造反,她哥一門心思造反,她嫁個男人,還是一門心思造反。燕云歌掀桌子,這日子沒發過了!
272.1萬字8 16625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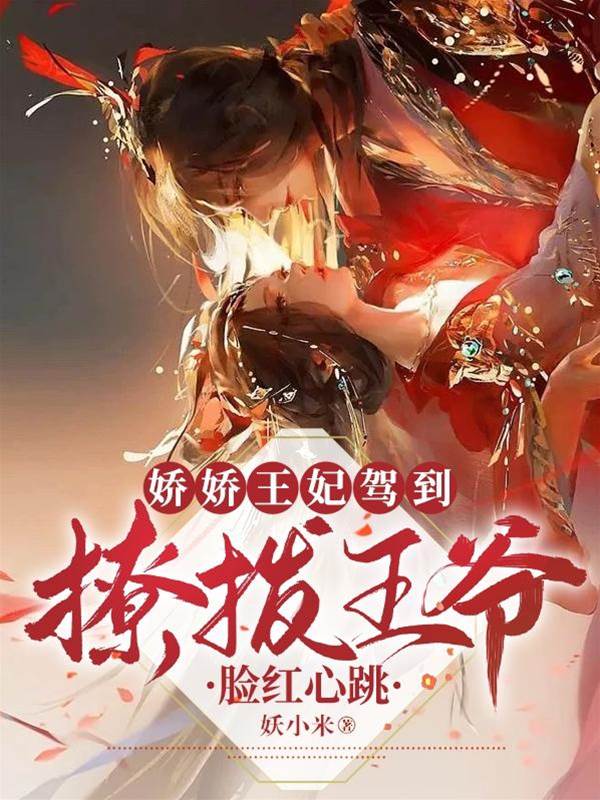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1640 -
完結372 章

穿成短命白月光后,和反派HE了
桑遠遠穿進一本古早玄幻虐戀小說裏,成了男主那個紅顏薄命的早逝白月光。男主愛她,男配們也愛她。女主因爲長了一張酷似她的臉,被衆男又愛又虐又踩,傷身又傷心。和男主的感情更是波折重重狗血不斷,虐得死去活來,結局還能幸福HE。桑遠遠:“不好意思本人一不想死二受不得虐,所以我選擇跟反派走。打擾,告辭。”反派長眸微眯,姿態慵懶,脣角笑意如春風般和煦——“我的身邊……可是地獄呢。”她沉思三秒。“地獄有土嗎?”“……有腐地。”“有水嗎?”“……只有血。”他想看她驚惶失措,想等她尖叫逃離,不料女子呆滯三秒之後,雙眼竟然隱隱放光——“正好試試新品種!”“……”他在最深沉的黑暗中苟延殘喘,從來也沒想到,竟有一個人,能把花草種滿一片荒蕪。
57.1萬字7.92 9525 -
完結313 章
亡國后成了反賊的寵婢
姜嶠女扮男裝當了幾年暴君。叛軍攻入皇城時,她麻溜地收拾行李,縱火死遁,可陰差陽錯,她竟被當成樂伎,獻給了叛軍首領霍奚舟。姜嶠捂緊馬甲,計劃著再次逃跑。誰料傳聞中陰煞狠厲、不近女色的霍大將軍竟為她破了例。紅燭帳暖,男人摩挲著她眼角的淚痣,眸色暗沉,微有醉意,“今夜留下。”*姜嶠知道,霍奚舟待她特殊,只是因為她那雙眼睛肖似故人。無妨,他拿她當替身,她利用他逃命。兩人各有所圖,也是樁不虧的買賣。直到霍奚舟看她的眼神越來越深情,還鄭重其事地為允諾要娶她為妻,姜嶠才意識到,自己好像是在作繭自縛——
49.2萬字8 68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