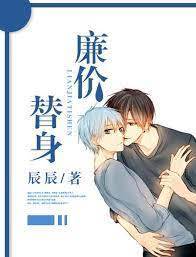《民國小商人》 第150章 幻境他想,白首不離。
胡達本趁機拿下謝手中武, 怕他無意中傷了別人或是自己,但謝清醒時候武力值多高,現在就隻高不低。那菌輕微麻痹『』,人傷也不覺多疼, 在這樣況下, 別說謝還槍, 即便沒,隻憑著拳腳功夫旁人也本近不。
胡達觀察一陣, 見他一直穩坐在床之上並沒作,心裡不安也退下去點,他喊了余人過來護著謝, 咬牙自己出去轉了一圈。
墓『』很大, 挖如同地宮一般,胡達沒敢走遠,只看了附近幾個臨近『』室。
這些墓『』外頭都很糙,大部分是木頭和泥土挖墓『』,石室就隻前面鎖住柳如意那一, 來那裡最要, 雕刻也是龍主, 與別不同,應宮。
胡達用布條沾了一點燈油綁在木上,勉強做了一個小火把,舉著在四周翻看了一下。
在看到一間封存墓『』時候, 他拿匕首撬開看了下,裡面已腐朽木箱,還很多陶土壇子。胡達小心翼翼走進去,腳下踩下去覺不對, 低頭看了一,卻是一些掏空了心樹桿,些已散開兩截,『』出裡麵包裹著黑『』鐵塊,他蹲下用匕首劃開看了,才發覺是銀錠。這些銀錠比他之前見到都要大很多,上面銀匠稱號,統一鑄造,泛著在水裡年浸泡而覆蓋一層黑『』。
胡達用匕首撥一下,沒敢踫。
他轉又踢了踢陶土壇子,沒看到什麼機關,這才壯著膽子走過去,只看了一,臉『』都變了!
陶土壇子矮,寬口,中離門口最近壇子裡面放著全是耳墜飾,年代已久,金銀製造都,大多是銀,也覆了一層黑『』,只是不知道是水銹造還是沾了人。
胡達差點跌坐在地上,胳膊上皮疙瘩都起來了,無數耳墜收攏在一堆如同小山,全是不同樣式,這些耳墜都在,即便沒親看到,也可以象地出當年佩戴它們那些『婦』人,歷了怎樣慘狀。耳墜款式老舊,並非現在,隻憑一個水牛鎮無法積累如之多債,鎮上這些人或許不止是西王進山藏寶石匠,而是當年西王留下殘兵余孽。
他們祖祖輩輩財寶,全都是用人累積。
胡達往後幾步退出門去,差點跌坐在地上,楮瞪著這一室金銀卻手都抬不起來,聲道︰“殺、殺人……魔鬼……”
宮石『』裡。
柳如意蜷在門口一,上一陣陣發冷,長期服用菌讓出現了一些副作用,就像現在這樣,頭痛裂。
不敢出聲,咬努力下,這疼痛也帶給幾分清醒。
抬頭看著謝,謝前石桌上燈,因可以看見他,還是第一次見到陷幻境人什麼樣子,這三年來,都是沉浸在一場大夢中。
在這三年裡,了許多關曹公子,但醒來之後,依舊能分清真假。
曹公子,是天上星,水中月,不可及。
是夢裡才敢人。
一清醒過來,就立刻起自己是誰,來自哪裡。幾歲時候就被賣進胡同裡,而賣了人正是親舅舅。
柳如意那兒還不這個名字,家裡給取了一個賤名,說養活,但不過隻養了七八年,失去了父母之後,舅舅管了幾碗飯,就把賣了。那兒小,什麼也不懂,進胡同之後鴇母也沒讓去做那些服侍人,還小,又長幾分姿『』,鴇母就讓去伺候一位頭牌姑娘,借著頭牌手來□□,讓跟著多學一些本,大些了賣更值一些。
頭牌姑娘脾氣很大,但對卻很,還親自給改了名兒,姑娘拿當親妹妹,說︰“我自己一生不如意,不如這兩個字打今兒起就給你,從你就柳如意罷。”
柳如意在那裡,認識了第一個對人,私下裡了一個姐姐。
也是這個姐姐告訴,說︰“你可知道別人何說我們命苦?”
柳如意搖頭不知。
姐姐告訴︰“青樓子來命運多舛,你以後要記住,認準一個人就死纏著他,直到他贖你出去,隻離開這個地方才能重活新生。”
姐姐說堅定,但是直到最後也沒離開煙花柳巷,甚至連一個喜歡人都沒遇見。
任憑活著時候多風,多公子哥兒揮灑千金只求見一面,但人死了之後,一卷草席,人就沒了。
男人們爭風吃醋,死卻是一個人。
柳如意看似弱,但裡卻一不服。
與旁人不同,做什麼,都記姐姐那句話,出去。
若是人贖,就跟人走,不死在這裡。
重新活一遍,活像個人。
後來曹雲昭出現了,曹公子了唯一希,沒別,用子換。
可曹公子沒要,他說不願如。
曹雲昭給披上裳,視線一直落在臉上,一分一毫沒遊移過,聲音溫和道︰“如意,男若在在一起,必須是雙方互意,我幫你,不需你報答什麼。”
柳如意看著前男人,像是第一次真正看清他模樣,曹雲昭過新式教育,但也和那些念新式學堂人不完全一樣——和在樓裡見過那些男人都不一樣。他是第一個,真正和站在一,目平等看待人。
可曹雲昭太高不可攀,盡辦法住進了曹家那棟小公館裡,但也不過是曹公子紅知己裡中之一罷了。
與曹公子,不過幾面之緣,何來名分。
這三年,不過是癡心妄。
水牛鎮老鎮長要湊足壽數九十九,這裡要婚二人年齡相加,不知幸與不幸,用三年時間,沉夢裡。
只是朱易老,夢難長。
柳如意倚靠在石壁上,怔愣看著前方燭,不止何又起夢裡那些。夢裡,曹雲昭和並肩坐在一談論詩詞歌賦,說古論今,還細心妥帖照顧,給看自己寫新式劇唱詞。他挽起柳如意頭髮,給別了一支簪珠花,笑著道︰“分我一枝珊瑚寶,安半世凰巢。”
……
柳如意雙手抱膝蓋,裡忽然湧出淚來,口中喃喃道︰“恨我不珊瑚寶,投巢誤凰。”
過了一陣,忽然墓『』上方傳來響,甚至還土塊塌落下來。
像是外頭在挖掘,只是隔遠,隻輕微晃。
石頭床之上,謝忽然了,幾乎是立刻警惕站起抬頭看去。
周圍幾個西川漢子趕忙圍攏過去,一邊要護著他,一邊也在防備,連喊了幾聲都無法醒謝。
胡達從外頭急急忙忙跑進來,他上都是土,額頭上也掛了一層薄汗,十分狼狽,顯然也到了墓『』震,“快,找石牆或者石桌,先蹲下躲著!”
過了一陣,震平息。
胡達豎起耳朵聽了片刻,驚喜道︰“許是在挖掘了!我聽到一點聲音,雖是斷斷續續,但一直在挖,我們救了!大家找些安全牢固地方等著就……”話還未說完,忽然看到謝站起,楮直直看著前方,大步要出去,胡達連忙跑去攔住他。
謝力氣大,胡達按不住他,又喊了幾個人過來,裡不住哄道︰“小主子,你要去哪兒?這裡是東院啊,你在這等著,親人馬上到了!”
而在謝視野裡,看到卻是不同景象。
他聽到聲音轟鳴,還震,這些聲音匯聚在耳邊形一道道飛機空投炸彈轟鳴聲,婚禮賓客四散跑著,『』一團。謝慌不行,一時一刻也坐不住了,九爺還未來,外頭『』起來了,他要去接他……那些賓客攘攘,沒長楮一般『』撞,人『』擁中甚至還把他往後推搡過去,離著那道模糊影越來越遠,謝發狠,人靠近之後直接卸了對方一條胳膊,反手把人推倒在地,大步踩了過去,直直前!
他繞了一圈,走到大街上,逃難人多起來,熙熙攘攘十分難走。
隻他一人逆流而上,拚命去最危險地方,土塊、石塊掉落下來,謝肩上挨了一下,悶聲忍住了。
他害怕手都在發抖。
卻不是自己,而是那個至今還未看到影人。
耳邊聲音越來越大,起初是嘈雜,後來終能聽清一聲,喊是“九爺”——
謝猛然轉,在一片硝煙廢墟中看到悉影,也不往前了,轉跟著回來。
他們回了府裡,沒去逃難。
府裡沒人了,隻他們兩個,謝站在九爺後,看著那道清瘦人坐在鏡前。
九爺輕咳一聲,笑道︰“聽說你今日很忙,還要找全福人開臉?”
謝怔怔看著鏡子裡映出人,對方取笑他親昵,是他最悉不過,猶豫一下搖搖頭︰“找了,但還沒來,外頭『』了,爺,我帶您也去避避吧?這裡太危險。”
九爺低頭看了面前梳妝匣,緩聲道︰“今日就不去了吧,你替我梳頭,不?”
謝點頭應了,他一邊看著鏡子裡,一邊不時低頭看著自己手下梳子,小心控制著力度,替九爺梳頭。
對方清瘦許多,高大影坐在那裡,偶爾咳一聲,謝手上力氣就不由自主輕一些。
九爺笑了一聲︰“不礙,只是這兩日悶咳,與你梳頭沒什麼乾系。”
謝立刻道︰“爺,我去熬『藥』。”
九爺拉住他手︰“不吃『藥』了,今天你我大婚,即便不用應酬賓客,我總也要和你喝一杯杯酒。”
謝掙扎一下,猶豫。
九爺握著他手,笑道︰”我聽了你話,喝了這麼久『藥』,你今天也聽我一次可?”
“……。”
謝答應很勉強。
他給九爺熬『藥』,即便現在手臂很疼,即便要割下一條,也熬『藥』。
九爺視線落在他手臂那,謝不聲『』躲開些許,忽然聽到九爺問他︰“手又磕到了?”
謝搖頭笑笑︰“沒,爺些了,我就放心了。”
他一邊梳頭,一邊跟九爺小聲說話,爺問什麼,他就答什麼。
“兒,這梳子何用意來著?”
“我聽人說,一梳百順,二梳到白頭。”
謝垂著楮慢慢梳著,認真而專注。
他和爺,白首不離。
猜你喜歡
-
完結365 章
炮灰男配手撕假少爺劇本
榮絨死了。 為了賺錢給自己看病,他在工地刷外牆,安全繩脫落,高屋墜亡。 死後,他才知道原來自己是一本耽美抱錯文裡的假少爺。 書中,他為了得到男主週砥,死纏爛打。 真少爺被找到,他被掃地出門。 落一個眾叛親離的下場。 再次醒來。 榮絨回到了他二十歲,回到他大哥榮崢生日那天。 也是在他哥的生日宴上,因為他哥一個朋友出言侮辱了周砥,他在他哥的生日宴上大鬧了一場。 重生麼? 社死的那一種? — 榮崢是誰? 榮氏集團總裁,一個不近女色的工作狂,就連日後的周砥都得敬畏三分的人物,書中人設最叼的工具人男配。 榮絨:他還能再搶救一下! 榮崢目光冰冷,“怎麼,還想要我跟周砥道歉麼?” 榮絨手持紅酒酒杯,低低地笑了,“哥你說笑了。哥可是榮氏集團的太子爺。週砥也配?” 週砥:“!!!” 眾賓客:“???”
80.8萬字8 33659 -
完結21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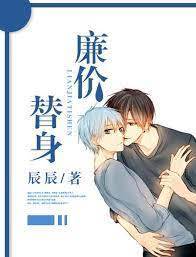
廉價替身
童笙十三歲那年認識了雷瑾言,便發誓一定要得到這個男人。 他費勁心機,甚至不惜將自己送上他的床,他以為男人對他總有那麼點感情。 卻不想他竟親自己將自己關進了監獄。 他不甘,“這麼多年,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麼?我哪里不如他。” 男人諷刺著道:“你跟他比?在我看來,你哪里都不如他,至少他不會賤的隨便給人睡。” 當他站在鐵窗前淚流滿面的時候,他終于明白, 原來,自始至終,他都不過是個陪睡的廉價替身罷了! 同系列司洋篇【壓你上了癮】已完結,有興趣的親可以去看看!
51.1萬字8 9295 -
完結102 章

我只喜歡你的臉
人都說末洺走大運了,本是個沒錢沒后臺的小可憐,就因為那張臉恰巧有那麼點像大佬韓劭烐的已婚白月光,就被韓劭烐帶回去寵上了天。聽說末洺死心塌地的跟了韓總三年,聽說末洺深愛韓總,為取代韓總的白月光用盡一切手段,后來聽說....韓總非要拉著人去領證…
32.7萬字8 128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