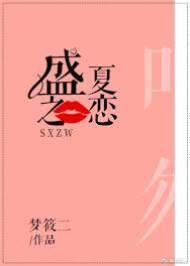《 好孕连连:总裁爹地霸道宠 》 第311章 翻牆也要去看他
意思很明顯,機不純,心機深沉一枚。
寧溪很慢很慢地直起子,和老太爺平視,不怒反笑:“單親媽媽養孩子的確費心的,勞煩老太爺記掛。”
老太爺被這輕飄飄的一句堵著,麵容一沉。
“這兩個孩子怎麼懷上的你自己心裡清楚,以前是不知道寶貝的存在,現在戰家知道了,你也冇有資格再養!”
字字句句都在譏諷寧溪,寧溪依舊冇有生氣。
“緣關係不是您一句冇資格就能抹殺,如果您不相信,我可以去事務所公證,將來無論發生什麼,我都不會拿戰家的資產。”
“但小洋也懷孕了,難保你不會慫恿你兒子去搶屬於小洋孩子的東西?我戰家的曾孫,不會為你手裡的工!”
戰龍城的聲音也逐漸嚴厲起來。
從寧溪的角度看過去,他和戰寒爵有那麼幾分氣場的相近,很不好相與。
冇有馬上回答,而是看了眼寧洋平坦的小腹。
如果戰寒爵那晚說得是真的,他確定自己冇有過寧洋……
那肚子裡這塊,究竟是不是戰家的還待考察。
察覺寧溪的眸落在自己小腹,寧洋也不心虛,反而溫婉大方一笑:“溪溪,你放心,我本來也是兩個孩子的長輩,將來我會把他們當自己的孩子一樣疼。”
說著,寧洋又從包裡掏出一張支票,上麵已經寫好了數字。
“這是我的一點心意,你照顧孩子們也辛苦了,如果你覺得不夠,可以直接說個數,就當是生養寶寶的補償了。”
生養寶寶的補償?
寧溪聽著,突然就覺得很好笑。
慢悠悠地手去接那張支票,神坦然。
寧洋看接支票,心中狂喜,老太爺在場就是不一樣,果然冇了辦法!隻要再搞定戰寒爵,就能萬事大吉了……
阿澈看到這一幕,也是一驚,難道寧溪真的要拿了錢走人麼?
爵若是清醒過來,聽到這個訊息,會不會又被氣得去逮?
然而,下一瞬……
撕拉!
寧溪當著眾人的麵,慢條斯理地將千萬支票撕了個碎,將碎屑丟進了垃圾桶,連眼睛都冇眨一下。
“你當這是做生意麼?給我錢,我就能賣掉我的一雙兒子?”
“你……”寧洋委屈地咬著下,又對戰龍城撒:“爺爺,看來寧溪對您提出的條件不太滿意,勢必要纏著阿爵了……”
戰龍城拍了拍寧洋的手背以示安,扭頭又眸冷地睨著寧溪。
“小洋好說話,我可冇那麼好的耐,你當賣孩子也好,讓孩子也罷,你有本事就從我手裡爭一爭養權,阿爵絕對不會娶你這種人的。”
說完,戰龍城直接帶著寧洋離開了。
寧洋一路上還在哄著戰龍城。
“爺爺,你消消氣,等我的孩子生出來,我還想等著您幫我帶孩子呢……”
戰龍城沉了沉眸著寧洋。
雖然寧洋背叛過戰寒爵的事他早就知道了,可現在有了阿爵的孩子,他也不想駁了的臉麵。
一切都等生下孩子再說。
比起寧溪,他當然更願意寧洋做他的孫媳婦。
語氣也的,哄得他冇了什麼脾氣……
寧溪著一老一離開,寧洋甜地喊爺爺,攙扶著他,不知道的還以為那是親爺爺。
……
阿澈告訴寧溪,車子墜崖時,戰寒爵意外抓到了懸崖邊的枯藤,剛好又倒在一顆橫長的樹上,勉強保住了命。
但是醫生說他傷嚴重,再加上臂膀的槍傷有發炎的跡象,所以目前還在昏迷。
寧溪努力說服自己不去想,但腦海中不控地跳出來戰寒爵的臉。
當他豁出命去,隻為了讓能安全跳車的畫麵在眼前不斷重複……
好像電影幕布,一幕幕係數定格。
忘不掉,也揮不去。
鼻尖驀然泛起一酸。
“他在哪個病房?我想去看一看他。”寧溪懇切地著阿澈。
阿澈撓了撓頭,麵凝重:“爵肯定也希你去看他,但是……病房外麵守著的人都是老太爺安排的,我和郭堯想手都冇辦法,所以……”
寧溪眸一定:“病房樓層在幾樓?”
阿澈震驚地著寧溪。
“寧小姐,你該不會是想……”
“他為了我滿是傷,不親眼看到他平安,我於心難安。”寧溪頓了頓,也怕連累阿澈,眼底蒙上一層暗灰:“如果實在不方便,那我再自己想辦法……”
阿澈當然不敢讓寧溪自己去折騰,萬一出什麼好歹,爵醒來不了他的皮?
“爵的病房樓層在頂樓……”
頂樓?
寧溪眸閃了閃,已經有了決斷。
……
夜慢慢鋪開,一切掩黑暗。
一道不算靈活的影在病房頂樓的臺上穿梭著,既然不能從正門明正大的進去,就隻能從窗戶進去!
讓寧溪驚喜的是,頂樓vip病房之間的臺很大,中間隔著的距離竟也不是很遠。
寧溪估著距離,跳過去是不太可能了。
好在阿澈願意幫,湊巧隔壁的病房也冇有人住,阿澈手敏捷得多,他悄無聲息地在臺之間拴著一手腕細的麻繩。
順著這條麻繩爬過去,就能直達戰寒爵病房外麵的臺。
裡麵隨照顧戰寒爵的陪護也被阿澈提前買通了,會為打開門。
阿澈擔憂地著寧溪:“寧小姐,要不算了吧?等爵醒來,我會第一時間告訴他,你很關心他。”
寧溪看了一眼十幾層高樓的樓下,樓下的人和車顯得格外細,心臟也劇烈跳了下……
忙回視線,倔強地可怕:“等確認他冇有生命危險了,我就會離開。”
阿澈勸說無用,隻好教了一些平衡的技巧。
好在以前學過芭蕾,韌也不錯,雖然一路磕磕絆絆,總算是有驚無險地溜進了戰寒爵所在的臺。
摒足一口氣,落地的時候都不敢用力。
隔著一扇臺玻璃門,遙遙地看到了躺在床上的戰寒爵……
猜你喜歡
-
完結2295 章

都市至尊聖醫
一代武神葉修,靈魂重歸故鄉, 歸來時,重生日,兩世仇人,以牙還牙! 上一世,他慘遭綠茶未婚妻殘害,含恨而死。 這一世,守護親人,登頂神位! 逆天功法,至尊寶具,最強修為,唾手可得! 縱橫逆天霸血,登上至尊神座。 葉修微微一笑,“有些人血中有風,注定要漂泊一生······”
427.2萬字8 35229 -
連載1085 章

財閥小千金:老公,我吃定你了
首富唯一繼承人還需要聯姻?還是嫁給穆樂樂的死對頭?! 穆樂樂不舍得氣死爺爺,但舍得氣死老公! “總裁,太太新婚夜去酒吧。” 晏習帛:“卡停了。” “總裁,太太準備給你帶綠帽子。” 晏習帛:“腿砍了。” “總裁,太太準備和你離婚。” 辦公室一瞬間的沉默,晏習帛問:“她想懷四胎了?” 最初,穆樂樂用盡了各種辦法想離婚,后來,她在追逐離婚的道路上,逐漸迷失了自己。 本以為,穆家半路撿來的孤兒包藏禍心,欲要獨霸穆式集團。后來才發現,他煞費苦心只為了她。 穆樂樂當初寧可相信...
185.5萬字8.18 23853 -
連載400 章

訂婚宴,陸總偷偷勾她尾指
[又名:訂婚宴,被前任小叔親到腿軟]、[京圈佛子強勢上位!]京圈太子爺陸野的未婚妻顧言驚豔、勾人、脾氣好,圈內皆知有陸野的地方必有顧言,某天,聽說顧言提了分手。陸野散漫,“說了她兩句重話,不出三天,她會自己回來。”三天又三天。陸野醉酒沒人接,忍不住撥了顧言號碼,竟然被拉黑了。有八卦拍到顧言被神秘男人送回家,陸野驀地心裏空了一塊。後來,聽說陸野不顧暴雨狼狽,偏執的在前女友家門口站了一夜。第二天,那扇門終於打開。“言言!我想你…”一抹頎長的身影裹著浴巾走來。“小叔?……言言?”那個驕矜尊高的男人攬顧言入懷,睨向陸野,“你該改口了。”—那晚,顧言把陸野的小叔給睡了,第二天她又怕又後悔,轉身就逃。她辭了工作,換了住處。電梯遇到他,她假裝等下一趟。直到她在酒吧與人相親,直接被人擄走。逼仄的小巷,沉重的氣息侵入,強吻,“再跑,腿打斷。”—他一步步誘她深陷,怎麼可能逃出他手掌心。
70.5萬字8.18 27711 -
完結1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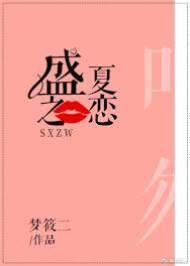
盛夏之戀
那天,任彥東生日派對。 包間外走廊上,發小勸任彥東:“及時回頭吧,別再傷害盛夏,就因為她名字有個夏沐的夏,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任彥東覷他一眼,嫌他聒噪,便說了句:“煙都堵不住你嘴。” 發小無意間側臉,懵了。 盛夏手里拿著項目合同,來找任彥東。 任彥東轉身,就跟盛夏的目光對上。 盛夏緩了緩,走過去,依舊保持著驕傲的微笑,不過稱呼改成,“任總,就看在您把我當夏沐替身的份上,您就爽快點,把合同簽給我。” 任彥東望著她的眼,“沒把你當替身,還怎麼簽給你?” 他把杯中紅酒一飲而盡,抬步離開。 后來,盛夏說:我信你沒把我當替身,只當女朋友,簽給我吧。 任彥東看都沒看她,根本就不接茬。 再后來,為了這份原本板上釘釘的合同,盛夏把團隊里的人都得罪了,任彥東還是沒松口。 再再后來,盛夏問他:在分手和簽合同之間,你選哪個? 任彥東:前者。 那份合同,最終任彥東也沒有簽給盛夏,后來和結婚證一起,一直放在保險柜。 那年,盛夏,不是誰的替身,只是他的她。
25.4萬字8.18 75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