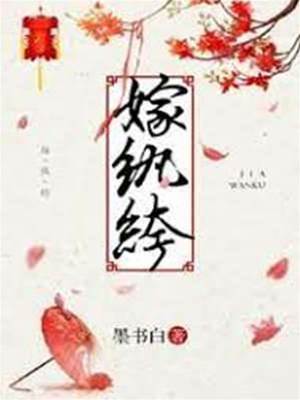《咬定卿卿不放松》 第69章 069
陸時卿正因元賜嫻此番拼命之舉心煩意,當真走了個神,未能第一時間察覺異,等刀尖近他前心三寸之遙才下意識手去擋。
但他手出卻忽地一滯,驀然停在刀鋒之外。
如此一息過后,匕首已刺他的膛,“哧”一聲響,一下寸許。
元賜嫻只來得及趕在之后沖到他跟前,踢開那名傷重之下強撐暴起的刺客,大驚失攙住他:“先生!”
喊完,詫異地看了眼地上已然咽氣的黑人,再看看陸時卿。
黑人到底是強弩之末,最后一刀全憑意志刺出,并不如何有力。他方才出手時雖晚了一步,卻尚且來得及住刀尖,大不了便是割傷掌心的事。
但他怎麼關鍵時刻出了個神?
陸時卿雙目一陣暈眩,下意識抓了元賜嫻的手腕,卻因知道不可能承他整個人的力道,強撐著沒有倒下去,直到約聽見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模模糊糊看到個人影沖上來。
是鄭濯趕到了,奔上前扶住了他。
陸時卿這才松了強撐的勁,借了他的臂力,咬牙跟他說:“走……”
到了這種關頭,他仍舊用了徐善的聲音。
鄭濯知道他是怕傷重暈厥,暴份,看了眼在他口的匕首,蹙眉道:“我知道。”又跟顯然嚇得不輕,打的元賜嫻道,“縣主的馬車可在附近?”
元賜嫻的眼直直盯著陸時卿口的刀子,本沒聽清倆人剛才一來一去的對話,直到聽聞“縣主”二字才回神,問:“您說什麼?”
鄭濯重復道:“我說馬車。先生傷重,不能在馬上顛簸了。”
聞言搗蒜般點頭,說了句“我去找”就轉狂奔下山。
等走后,陸時卿被鄭濯攙到一塊山石前坐下,盯著元賜嫻離去的方向問:“山中刺客……清干凈了?”
“干凈了,放心。”鄭濯答完,小心撕開他一角襟,避免牽刀柄,一面察看他傷勢一面飛快道,“沒傷到要害,但位置有點懸,現在拔刀太險,恐怕真得等找來馬車,你撐一會兒。”
他剛才是為避免陸時卿暴才支開了元賜嫻,眼下看來,馬車確實是必須的。
陸時卿卻沒先關心自己的傷勢,用力眨了下眼保持清醒,代道:“去看看那名刺客的死相……”他指的是最后暴起的那個黑人。
鄭濯問清是哪個后,忙起去察看,回頭答:“是失過多而亡。面朝下,雙蹬直,左手在口。”他說完似有所覺,補充道,“在跟你傷口一模一樣的位置。”
陸時卿低咳了一下,虛弱道:“把他的左手改住右手掌心……”
鄭濯趕照做,隨即走回道:“怎麼回事?”
其實他剛才就覺得不對勁了。他是習武之人,很明顯看得出這一刀出手綿,照理說,陸時卿不該中招的。
匕首還未拔出,陸時卿尚能勉強保持神志,答道:“平王對我起疑了……”
姜家倒得太過干脆利落,平王從中察覺不對,懷疑“徐善”并非布謀士,而很可能是藏在朝中的某位員。
今天這批刺客正是平王派來的,首要目的是除掉“徐善”,見計劃失敗則退而求其次,企圖驗明他的份。
那名黑人知道自己即便襲掀了“徐善”的面,看清他是誰,也已不可能有命回去報信,因此選擇在他上明顯留下傷口。假意使了看似兇猛的殺招,就是為了一個人作出遇險時的下意識反應。
但陸時卿卻臨頭醒悟,捱了他一刀,黑人便在臨咽氣時住了口,表明自己刺傷了“徐善”的這個位置。一旦平王派人來收尸,得到這個訊息,便有可能順藤瓜找出陸時卿。
“徐善”做謀士的事暴就暴了,甚至元家與鄭濯被證明有所牽扯也不是必死的絕境,唯有他的站隊被揭發,這多年潛伏,步步為營的一切才都完了。
所幸現在,他刺客留下了假訊息。
鄭濯聽罷想通了究竟,嘆口氣,揭開了他的面,看他臉灰敗,滿頭冷汗,反笑道:“不想守寡就撐住了,你這一死可是一尸兩命,陸子澍沒了,徐從賢也沒了。”
陸時卿嗤了一聲,這下倒跟回返照似的清醒了點:“死不了,脾氣大,命也大。”說完像是想講點能自己神些的事,“嘶”了一聲,問鄭濯,“你說是不是對‘徐從賢’太好了點?”
鄭濯覷他一眼:“不都是你?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陸時卿疲憊地笑笑。
他不是非要自己跟自己過不去。而是他扮演老師,本是全然照他言語習慣、舉止聲來的,甚至連好、理想與思考方式也是。后來雖因,數次在元賜嫻面前扭曲了老師的形象,但他實在分不清,這個“徐善”究竟有幾分是他自己,有幾分是老師。而元賜嫻對這個“徐善”的好,又究竟源于他那幾分,還是老師那幾分。
他靠著這個惱人的問題撐著昏沉的眼皮,直到聽見一陣慌的腳步聲才倏爾醒神,掙扎著想去拿面。
鄭濯當然比他更快一步,直接把面一把拍在了他臉上,以一種仿佛要毀他容貌的架勢,痛得他差點悶哼出聲。
是元賜嫻回來了。跑得氣吁吁,人未到聲先至:“馬……車來了……”
鄭濯一把攙起陸時卿,隨往山下走,將他架上了馬車。
車來得如此之快,其實還靠揀枝和拾翠。倆人在元賜嫻策馬離開后,當即趕去附近驛站重新弄了馬,一路往這邊追。往上的山路有一段崎嶇狹窄,原本不夠馬車通行,是經由主仆三人披荊斬棘,死命駕了上來。
得知徐善傷,兩名婢又慌忙拿了馬車里原先備有的去打來水準備好。
元賜嫻見狀也想掀簾進去,卻被鄭濯攔在外頭:“我得給先生理傷口,勞請縣主策馬護送。”
只好聽他的,點點頭:“那我拾翠給您搭把手。”
鄭濯怕再拒絕起疑,便點頭應下。
元賜嫻命揀枝駕車往長安城趕,自己則心驚膽戰騎馬在旁,片刻后,聽車傳出一聲極盡忍耐的悶哼,隨即響起很多窸窸窣窣的靜。
抿著一言不發,一路僵地揚鞭策馬,直到鄭濯的侍衛趕來接應他。
這個決定并沒有錯。元家的馬車必須還給元賜嫻。
元賜嫻眼瞅著幾名侍衛將已然昏厥的陸時卿扛到另一輛馬車中,遲疑問后腳掀簾下來的鄭濯:“先生如何了?”
鄭濯滿手的都來不及,簡單道:“暫且沒事,縣主放心。”
元賜嫻聽見這一句“沒事”卻也談不上輕松,只是看了眼他的手,勉強點了點頭。
照關系講,徐善跟鄭濯更親近,自然沒道理說拜托之言。而對大局的顧全又令哪怕再心焦也不可能親手送徐善回城照顧他。
實在什麼都做不了,也不合適做。
鄭濯剛才憂心陸時卿,全然沒注意元賜嫻,此刻才發現一狼狽泥,甚至連裳都破了幾,不由眉頭一皺,暗嘆自己心大意了,道:“你趕回府,一有消息,我會立刻送來。”
元賜嫻朝陸時卿的方向看了眼,頷首道:“多謝殿下。”然后轉回了馬車。
揀枝駕了車往城里去。
元賜嫻甫一掀簾里,便聞見一陣濃郁的腥氣,再一低頭,又被兩盆子目驚心的水一震。
拾翠正在里頭收拾,見來,忙騰了塊勉強干凈的地方示意坐,邊道:“小娘子將就將就,方才殿下給先生拔刀,況兇險,濺得到都是。”
元賜嫻“嗯”了一聲,木然坐了下去,似乎也沒太在意這點臟污。
拾翠當然是有眼力見的,忙安道:“小娘子別太擔心,殿下手法湛,是止住了,眼下他的侍衛也帶來了傷藥,想來先生不會有大礙的。”說罷拿了干凈的帕子給拭面。
元賜嫻一不由侍候,半晌問:“拾翠,先生這樣待我,我能給先生什麼?”
拾翠拭的作一滯。
小娘子的話,又怎會聽不懂。徐先生如此智慧的一個人,今日之所以輕易中了敵人的詭計,其實是因為關心則啊。
猶豫了下道:“小娘子,婢子知道這時候該勸您莫多想,但剛剛……”
元賜嫻偏頭盯住:“剛剛什麼?”
“剛剛拔完刀,先生暈厥過去,昏睡時說了胡話,似乎……”苦著臉道,“了您的全名。”
元賜嫻聞言一滯,垂眼盯著腳下的水不說話了。
拾翠說的確是實話。只不過陸時卿因傷重嗓音低啞,又是模模糊糊以氣聲道出的夢囈,就沒辨認出來。有鄭濯在,面自然是沒給摘的,而又對陸時卿的板不悉,因此打下手時也未發現端倪。
猜你喜歡
-
完結758 章

慕紅裳
個性活潑的女大學生謝家琪抹黑下樓扔個垃圾,不小心跌下了樓,再睜開眼,她發現自己變成了右相府的嫡小姐謝淑柔;榮康郡王正妃顧儀蘭絕望自裁,一睜眼卻發現自己回到了十四歲,一切都可以重頭再來。這一切的一切原本都與安國公家的小姑娘穆紅裳沒關係,紅裳怎樣都想不明白,她的人生怎地就從此天翻地覆……
123.8萬字8 6394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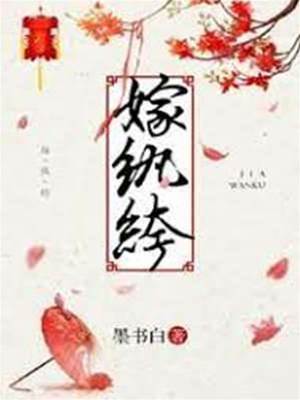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48689 -
完結283 章

代嫁太子妃
簡介: 一朝穿越,她成了出身名門的官家小姐,青梅繞竹馬,卻是三人成行……陰差陽錯,定親時她的心上人卻成了未來姐夫,姐姐對幾番起落的夫家不屑一顧。她滿懷期待代姐出嫁,不但沒得到他的憐惜,反而使自己陷入一次更甚一次的屈辱之中。他肆意的把她踩在腳下,做歌姬,當舞姬,毀容,甚至親手把她送上別人的床榻……
23.2萬字8 10724 -
完結74 章

投喂病弱男配
陸云初一朝穿書,成了一個癡戀男主的惡毒女配,欲下藥強上男主,卻陰差陽錯地設計到了男主名義上的病弱弟弟頭上,最后不得不嫁給他。 書中這個n線男配就是個工具人設定,存在的意義…
26.2萬字8.38 1017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