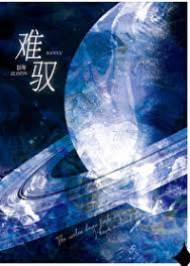《暗黑系暖婚》 第二卷 335:時瑾片場寵妻無度,徐家重大變故
江北市警局。
天已經完全黑了,霍一寧還在提審嫌犯。
“二十七號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你在哪?”
鄭避開霍一寧的目,回答得很快:“上班啊,還能干什麼?”
霍一寧也不急,跟他慢慢玩,扔了筆,好整以暇地瞧著他:“打卡和簽到記錄都沒有,你老板說那天你休假了。”
鄭眼神閃躲:“我忘了,這麼久的事誰記得。”又改口說,“我在家睡覺。”
“有沒有人能證明?”
“沒有。”
霍一寧了后槽牙,語氣懶懶散散的:“不認是吧?”
“認什麼?”他壯著膽子反駁,“我是冤枉的。”
語氣振振有詞,目閃閃躲躲。
虛張聲勢,有鬼。
霍一寧也不,慢慢悠悠地敲著桌子等著,約過了五分鐘,放在桌上的手機終于響了。
他接起來,一分鐘不到,就掛斷了,抬起眸子:“你家附近的垃圾桶里,找到了一把手槍,51式7。62*25MM手槍彈,與現場的子彈頭吻合,已經送去做指紋比對了,另外,現場采到的腳印,與你家里那雙專業防鞋的鞋印也匹配上了,這樣你還要狡辯?”
鄭眼里慌忙一閃而過,低著頭:“那種鞋很普遍,很多高空職業的人都會穿,說明不了什麼。”
不見棺材不落淚啊。
行,去搞個棺材來。
霍一寧扔了筆起:“要證據是吧?我去找。”他頂了頂后槽牙,笑得的,“讓我找證據,你得做好多坐幾年牢的準備。”
鄭面如土,抿著,沒吭聲。
窗外,已經華燈初上。
姜九笙接了個電話,緒不佳。
時瑾盛好了粥,喊回了餐桌,粥有些燙,還在晾著,他問:“是誰的電話?”
“老師的。”
“怎麼了?”
擰著眉頭,同時瑾說:“湯圓被查出了抑郁癥,老師想把博接過去陪陪它。”
時瑾拿著湯匙的作頓了一下,很意外:“那只二哈也會抑郁?”
印象里,那只狗子嗨浪得能蹦到天上去與月亮肩并肩。
姜九笙也覺得匪夷所思:“湯圓懷孕了,孕期狗狗比較容易抑郁。”
“……”
啪嗒。
時瑾的湯匙掉進了碗里,大概因為姜九笙也懷孕的緣故,準爸爸時瑾問了一句他平時絕對不會問出口的話:“博做了絕育,孩子是誰的?”
兩只狗都太通人,是以,兩邊主人都默認了它們是一對。
姜九笙眉頭不展:“老師說他也不知道,之前帶湯圓去遛彎,狗繩了,估計就是那次懷上了,還不知道懷上的是什麼品種,大概就是因為這個,湯圓得了抑郁癥。”突發奇想,“博這是被綠了嗎?”
“……”
時瑾有點頭疼了,兩只狗,戲怎麼這麼多。
第二天,謝大師就去徐家接走了博,徐老爺子不怎麼愉悅,說了老哥們幾句,主要是數落他怎麼不看好狗,讓湯圓被外面的野公狗給糟蹋了,平白讓博頂了一片綠,更憋屈的是以后還有小野種。
謝大師也很無奈啊,野公狗來強的,他家湯圓公主一介弱質母狗,還能怎麼辦?
這件事暫時就這麼翻篇了,不過,湯圓抑郁的事給時瑾敲了一記警鐘,孕期很容易抑郁,何況姜九笙有抑郁癥患病史。
不巧,就在當天,天北醫院婦產科有位產婦死在了手臺上,一尸兩命,時瑾親眼目睹,手心淌了一手的冷汗。
那之后,他的焦慮與日俱增,表現在他與姜九笙寸步不離的時間越來越長,而且,沉迷陪,不可自拔,日漸消瘦,夜不能寐。
次日。
早上九點,姜九笙吃完飯,發現時瑾仍舊沒有要出門的打算,不好奇:“今天周三,你不用去酒店嗎?”
每周三,時瑾都有酒店的高層周會。
時瑾還穿著家居服,在廚房給姜九笙沖孕婦,他說:“在家陪你。”
笑著從后面抱他:“可是我要去拍戲啊。”
時瑾回頭,給一個吻:“那就去片場陪你。”
“好啊。”
姜九笙還以為是酒店會議臨時取消了,時瑾沒事才留下來陪,可到了次日,發覺時瑾仍然沒有要去上班的意思。
因為嗜睡,中途吃了東西后,又去睡回籠覺,一覺醒來都十點多了,
時瑾看起來了,把手提放下:“笙笙,去刷牙,粥已經好了。”
姜九笙看了一下時間:“時醫生,你遲到了。”
他穿著與一個款式的白,牽去浴室洗漱:“沒關系,我今天請了假。”
“為什麼請假?”
時瑾好了牙膏,把牙刷遞給:“反正已經遲到了,干脆請了半天假。”
本來只是請了半天假的,到后來……
一點的時候,時瑾送去了片場,一個半小時后,發現他又折回來了。
“你怎麼回來了?”
時瑾說:“路上堵車。”
“哪條路?”
他坐到邊,化妝師正在給化妝,他看過化妝品的牌子后,才說:“錢江路。”
“……”
姜九笙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錢江路離醫院只有兩個紅綠燈,再怎麼堵,也堵不了幾分鐘,可他開回片場,回程也會堵車,最要一個多小時。
忽然想起了以前聽過的一個冷笑話,說的是兩個神病院的病友,約好了一起翻墻逃院,只要翻過了一百道墻就能出去,可兩位病友翻到了第九十九道時,一個病友累了,另一個病友就說那翻回去吧,于是,兩個病友就翻了九十九道墻回去了。
雖然不恰當,但時瑾的行為,與那兩個病友竟有異曲同工之妙。
姜九笙哭笑不得:“時瑾,你這是故意翹班嗎?”
“算是吧。”他不怎麼在意,反而問,“笙笙,我陪你你不高興嗎?”
就事論事:“高興。”
時瑾心愉悅了些:“你高興就行。”
這小兩口是高興了,可片場的人不高興啊,是真沒想到一貫溫和有禮的時瑾,竟然這般寵妻無度。
比如,姜九笙拍第一條戲的時候——
“這個戲服太薄了,請問有厚的嗎?”時瑾問服裝師。
雖然這語氣依舊禮貌,但就是讓人發憷,服裝師姐姐莫名就有點膽戰心驚:“……沒有。”
宮裝人,厚了就不好看了,所以,即便是大冬天,也是怎麼怎麼穿。
時瑾擰眉,思索了須臾:“麻煩請稍等二十分鐘。”
服裝師姐姐有點懵。
時瑾已經撥了電話了:“秦中,安排人送五臺制暖空調過來。”說完,改了口,“十臺。”
掛電話前,時瑾再一次改了口:“二十臺吧。”
服裝師姐姐:“……”
比如,姜九笙拍第二條戲的時候——
“你好,能不能把水換熱水?”時瑾問場務。
場務大哥沒準大佬的意思:“笙笙不用下水啊。”
時瑾掃了一眼人工蓮池里的水,眸與那波瀾不驚的水面一般,冷冷的:“手會到。”
場務大哥:“……”
再比如,姜九笙拍第三條戲的時候——
“這一段,能否改一下?”
這次到導演懵了:“時總覺得哪里不合適嗎?”
時瑾抬頭,看影視城的宮門:“城墻太高了,很危險。”他神態溫文爾雅,語氣卻不容置疑,“城下送別也沒有區別。”
有沒有區別也是他這個導演說了算啊,郭導笑:“行的,時總。”
誰讓他是投資最多的金主爸爸呢……
這樣的小狀況不勝枚舉。
時瑾寵老婆寵得有點過分了,這讓劇組的工作人員有點難辦啊,導演也不好直接說,就讓副導委婉地去跟姜九笙說。
“笙笙,時總是不是來片場太勤了?”
姜九笙就事論事:“是有點。”
連著幾天,到哪,時瑾便跟到哪,幾乎一步都不離。
金主爸爸也不能得罪,副導就旁敲側擊:“劇組這兩天的拍攝進度慢了很多。”
嗯,好像的確是。
翌日。
早上,姜九笙問時瑾:“今天也不去上班嗎?”
“嗯,我請了假。”
有點孕吐反胃,把粥推開:“請假理由是什麼?”
時瑾端過去,舀了一勺哄吃,回了一個理由,漫不經心地:“外面下了很大的雨。”
時瑾昨天請假的理由,是天氣好。
今天,是天氣不好。
最近,他黏人得特別厲害。
姜九笙啞然失笑,知道他的心思,隨他去了:“你還要陪我去片場嗎?”
“嗯。”
約法三章:“陪我可以,不準再干涉拍攝了。”解釋,“你太嚴苛了,我是去工作,不是去當祖宗,哪能萬事都依著顧著我一個人。”
時瑾心想,怎麼就不是祖宗,他家笙笙,是他的小祖宗。
不敢惹氣惱,他只好乖乖應承:“我盡量。”不過,他把勺子喂到邊,“若是忍不住,你就哄哄我。”
猜你喜歡
-
完結91 章

樑少的寶貝萌妻
【暖寵】他,宸凱集團總裁,內斂、高冷、身份尊貴,俊美無儔,年近三十二卻連個女人的手都沒牽過。代曼,上高中那年,她寄住在爸爸好友的兒子家中,因爲輩分關係,她稱呼樑駿馳一聲,“樑叔”。四年前和他的一次意外,讓她倉皇逃出國。四年後,他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而她歸國後成了正值花樣年華。樑駿馳是她想拒絕卻拒絕不
14萬字5 38726 -
完結517 章

婚不設防:帝少心尖寵
日久生情,她懷了他的孩子,原以為他會給她一個家,卻冇想到那個女人出現後,一切都變了。靳墨琛,如果你愛的人隻是她,就最好彆再碰我!
92.1萬字8 67367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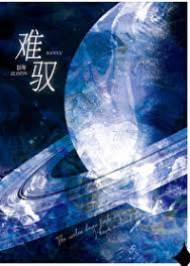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18 1080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