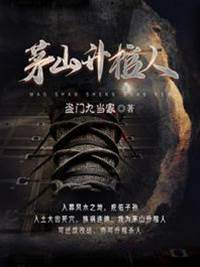《四大冥捕》 第13章 泥娃娃
驟雨歇,雲散。
月如鉤,晴空如洗。
這一陣雷雨來的急,去的也快,眨眼間已是一片晴朗星空,月照荒野。
玄殺,無命衫,夜風一吹,寒氣骨,不約而同同時打了一個寒戰。
“走,進城!”玄殺招呼一聲,抬步直奔夜深的城牆廓,無命猶豫一下,快步跟了上去。
荒郊野外,前不著村,後不著店。
他們衫盡,又無幹材生火,這樣一淋站在野外扛一晚,就算是一鐵骨也未必能夠撐得住。
二人快步如飛,上熱流轉,方才緩解了幾分刺骨寒意。
他們走的路,是通往城池的路,也是一群嬰靈追隨那一盞燈火的路。
朦朧月下,前面展開一條雪白的路,直直的延而去。
等無命看清那條雪白的路,背後一陣寒氣,雙居然有一些失控,腳步竟然抖。
那本不是一條人走的路,而是一條森森白骨堆積而的路。
而且都是一完整癱倒的骨。
剛剛圍困著他們的那一片黑的孩影,原來都是棄荒野,風化腐蝕後的一孩白骨。
能夠利用一盞燈,能夠指引調這一片荒野上,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留下來的夭折孩。
將它們聚集一起,圍一座嬰靈大陣,幕後作法之人果然一副好手段。
作法的又是什麼人?那個幫他離圍困的鬥篷人又是什麼人? 一路思索,不知不覺間他們已走到了那條森森白骨路的盡頭。
“師弟,你看!”就在無命冥思苦想,茫無頭緒之時,玄殺打破了他的思緒。
無命順著他的目看過去,頓時呆如木。
白骨盡頭居然立著一顆焦黑的枯樹,出一支焦黑的枝幹,掛了一只燒殘的燈籠。
殘存的燈籠骨架依然掛在上面,在夜風中搖曳。
這不是他們剛剛棲其下的那株枯樹麼? 還有那個延的枯枝,還有那盞搖曳的燈火? 顯然這顆樹,這顆枯枝,這盞燈火,都已經被雷劈過。
一擊之下,已被燒了黑乎乎的黑炭。
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剛才明明是一個黑鬥篷提著燈籠吸引了萬千嬰靈,被一道閃電劈中,怎麼閃電劈中會是一顆樹? 樹怎麼會行走,怎麼會咳嗽,那分明是一個人,一個躲在漆黑鬥篷裡的一個人。
這一定是另外一顆樹,一顆一一樣的樹,那個鬥篷人將燈籠掛在這顆樹上。
無命下意識的猛然轉,朝著他們剛才棲的那顆枯樹看過去,想到證實自己的推斷。
月照荒野,茫茫無際,一片荒蕪連接,除了一地荒草,本沒有一高木,就連一叢灌木都沒有,更別說是樹, “我已搜索一遍,我們棲的那顆樹已經走了,披著鬥篷走了。”
玄殺喃喃而語,目裡出一層深深的憂慮。
“那顆樹披著鬥篷走了?”無命也一臉愕然。
“那不是樹,是一個披著鬥篷的人,幫我們擺嬰靈圍困的那個人。”
玄殺目著無邊無際的荒野,驚訝之中多了一激。
無命沒有答話,默默低頭而行,玄殺也默默跟了上來。
不管是那個鬥篷人轉移了那顆樹的位置,還是轉移了他們兩個人的位置,反正他們已經離了困境,可以去幹他們要幹的事。
二人踩著夜迤邐而行,接近臨安一刻,也接近了黎明。
晨曦中,厚重的城門緩緩而開,一新鮮之氣撲面而來。
晨風撲面,夾帶了新鮮之氣,也夾帶了幾片飛舞紅花瓣。
花瓣隨風翩翩飛舞,盤旋二人眼前。
二人不約而同各自出一只手掌,每一個掌心,落了一片鮮紅的花瓣。
花瓣浸潤,瞬間化為一粒鮮紅的珠。
“是嬰花。”
玄殺目凝重,失聲驚呼。
“嬰花?”無命一臉疑。
“嬰花可驅避蚊蟲,蘇府已有了它,毒已不會繼續蔓延。”
玄殺頓了一下,繼續解釋,“花草會招惹蚊蟲,也可驅避蚊蟲。
蘇門大小姐果然聰慧過人,這麼快便找到了驅蚊蟲破毒之法。
只是如此邪魅之花,是如何弄到的?” “這蘇門大小姐酷花草,一定於種植,此花也許是就是培育。
一個豪門小姐,整日閉門不出,以花草為業,其中定有蹊蹺。”
無命語氣嚴肅,已將這位古怪的大小姐列了重點嫌疑。
“我等雖是法師,亦為捕快,凡事必要證據,不可妄加猜測。”
“既已城,上門一查便知。”
…… 二人一路說話,不覺已臨蘇府。
“雲州法師玄殺,求見蘇府主人。”
玄殺擺出一副大師派頭,自報家門。
無命蓋了一頂破鬥笠,住了面目,躲在玄殺後,在玄殺強大的氣場籠罩之下,儼然一個隨小跟班。
“你是?”匆匆而來的蘇天,被玄殺的氣勢震懾,疑地打量著這位不速之客。
“在下玄殺,雲州士,聽說貴府懸賞祛病,特地千裡南下,專程前來替貴府驅妖化邪。”
玄殺朗朗有聲,目已從敞開的大門掃視蘇家院落格局。
“嘿嘿,那些都是江湖傳聞,不過是幾只毒蚊毒蟲,現在已經有了驅趕之法,不必再勞煩大師。
本府最近諸事繁忙,上上下下一片混,恕不能接待大師。”
蘇天以為他又是一個聞訊前來騙錢的江湖客,勉強應付幾句,下了逐客令。
“已有驅蚊之法?莫非就是那株嬰花?唔……好新鮮的味道,果然著一邪氣。”
玄殺嗅了一下,目穿越重重庭院,落在正院中央的那一束紅的花。
“此花名蘇瑾,是本府長門大小姐親自為它取的名,是我們蘇家的守護之花。
這位大師可不要信口胡說,家丁,送客!”蘇天臉一寒,立刻下令家丁驅趕這位添的江湖士。
“且慢,我只要看看那些還沒有死的病人,如無法救治,立刻就走。”
玄殺手制止了兩名上前的家丁,目冷冷地落在蘇天臉上。
“大師隨我來!”蘇天猶豫一下,還是決定帶這位不速之客去看看那幾十條奄奄一息的蘇家命。
只要還有一希,作為蘇家主事便不應該放棄。
玄殺仰首,大步而,跟著蘇天直奔那個隔離小院。
蘇家幸存者見又有了希,立刻跟了一片,畢竟隔離別院的染病者都是他們至親之人,一旦有了希,他們自然希他們能夠起死回生。
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被玄殺吸引一刻,躲在他後的無命幾個箭步,竄了那株嬰花開放的院子,悄悄溜蘇傾城的閨房。
玄殺一路匆匆,了隔離小院,一濃重的**惡臭撲鼻,連這位當年經曆過氣沖天的毒陣的大師也不皺起了眉頭。
好悉的味道,這味道居然將他的思緒帶到了幾年前的那一場腥屠殺。
這味道不就是那一夜蘇大將軍布下毒陣,毒殺無數士兵和村民之後,遍地毒散發的味道麼? “大師,請!”蘇天停在了院門外,請玄殺進診斷。
玄殺穩住呼吸,大步了院落,卻並不進屋去看病人,而是一邊嗅著鼻子,一邊在空闊的院子裡轉悠一圈。
嗆啷! 一聲清脆的龍虎嘯,一道寒芒自玄殺背後升起,化作一道弧了他腳下的泥土,曾經種植花草的松泥土。
哇——哇——哇—— 一陣聲嘶力竭,令人骨悚然的嬰兒啼哭聲,劃破了蘇府寂靜的院落。
玄殺的劍已高高舉起,劍尖上居然著一個娃娃,一個糙的泥娃娃。
那淒厲的哭聲,居然是來自那個在劍尖的泥娃娃。
一個沒有生命的泥娃娃怎麼也會哭?而且哭的如此淒厲,如此真? 它不但會哭,而且還在流,被劍尖的傷口,居然不停的流,暗紅的汙。
啊噢—— 就在這邊一片驚怖一刻,一個病患竄出了房間。
口了一木,不停的順著木流淌。
他捂著口艱難的挪了幾步,跌倒在院子裡,一雙目死死的瞪著架在空中的泥娃娃,一只手朝著泥娃娃抓了一下,整個人已僵凝固。
那個泥娃娃的哭聲也嘎然而止,瞬間沒有了聲息。
玄殺眉頭鎖,掏出一塊金黃的黃布,纏繞了空出的左手,手上去輕輕的將劍尖穿了的泥娃娃拿下來。
捧著泥娃娃朝那剛剛自殺的走過去,對著端詳了片刻,那泥娃娃的面相竟然與死者有九分相似。
玄殺將那只泥娃娃輕輕放在死者出的手,那只僵死的手居然抓住了泥娃娃。
那一雙瞪著的眼睛緩緩閉合,死者角居然掛了一微笑,一詭異的微笑。
猜你喜歡
-
完結212 章

盗天之尸临万界
一睜眼,是迷茫,盡殺戮。殺戮非我念,安生難求! 不僅如此他的感官也變得靈敏起來,只是現在的他沉浸在吸血的快感當中,竟沒有發覺。 很快,籃世修的身體一點血液也流不出來了。易小天終於戀戀不舍的放開了幹癟的籃世修,轉向徐青而去,徐青流血過多,身體上的血液所剩無幾,很快就被易小天吸幹了。 不久易小天也從吸血的快感當中清醒了過來,當他看到這兩人的屍體的時候,他呆住了。 這簡直和三天前的老虎一般,“這還是我嗎?不!我還是我……
41.9萬字7.91 10869 -
連載83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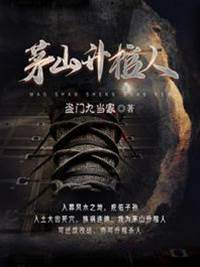
茅山升棺人
我從一出生,就被人暗中陷害,讓我母親提前分娩,更改了我的生辰八字,八字刑克父母命,父母在我出生的同一天,雙雙過世,但暗中之人還想要將我趕盡殺絕,無路可逃的我,最終成為一名茅山升棺人!升棺,乃為遷墳,人之死后,應葬于風水之地,庇佑子孫,但也有其先人葬于兇惡之地,給子孫后代帶來了無盡的災禍,從而有人升棺人這個職業。
153萬字8 9429 -
連載1229 章

民間禁忌雜談
殺豬匠不殺五指之豬。守村人不守有廟之村。風水師不點邪龍寶地。接生婆的雙手必須用公雞血洗。世間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規矩。
223.7萬字8.18 108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