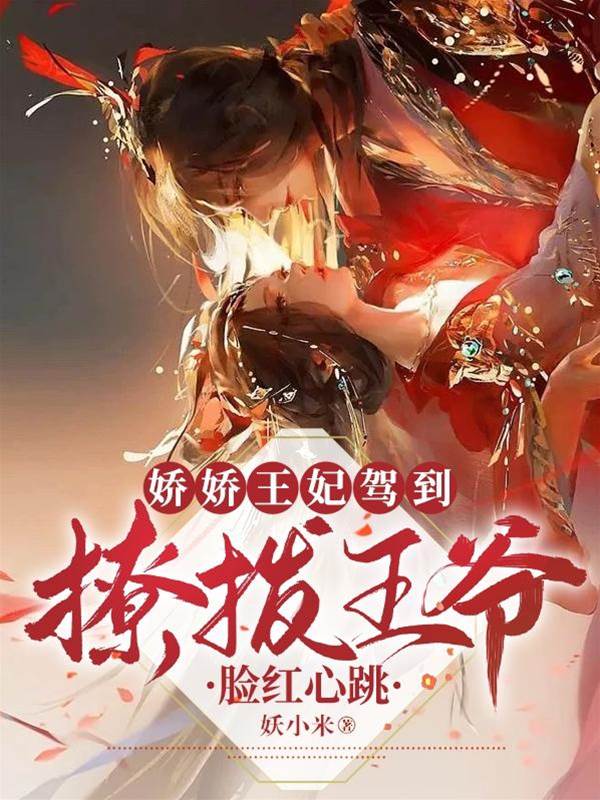《重生嫡女之藥妃天下》 第三百五十二章
蕭燕這段時間一直提心吊膽,就是擔心蕭燕會有孕,畢竟被人睡了和被人睡後懷了孩子,很顯然,有孕的節顯然更加嚴重一些,尤其孩子被要求生下來,那這事一輩子都過不去了,蘇傾楣有了這累贅,一輩子也是毀了。
蘇傾楣可能有孕的訊息,對蕭燕來說,簡直就是晴天霹靂,當場落淚,咬著,就哭出了聲。
“造孽啊造孽!”
秋靈冷冷看了蕭燕一眼,麵無表,繼續道:“二小姐隻說小日子沒來,現在還不確定,央著我家小姐給找個能守口如瓶的大夫,我家小姐念在姐妹一場的份上已經應了,明兒大夫就會來,至於怎麼見麵,你們自己想辦法吧。”
秋靈傳了話,轉離開,留蕭燕一個人繼續鬼哭狼嚎。
蕭燕現在自然是不能去王府的,思來想去,決定讓蘇傾楣從王府出來,約個蔽的地方見麵。
“小姐,二小姐確實已經懷了孕,和夫人想要神不知鬼不覺的打掉這個孩子。”
蘇傾楣那邊有結果的第一時間,蘇梁淺就收到了訊息。
“房大夫說,夫人當時要死要活的,就和瘋了似的,後來稍稍冷靜些,就央求他將孩子打掉,誰都不讓說。”
秋靈一五一十,一字不落的將話轉達給了蘇梁淺。
“打掉孩子,誰都不要說?”
蘇梁淺勾著的角滿是譏誚,這怎麼可能呢?
蘇傾楣恍恍惚惚的回到王府,坐立難安。
是一早就出的門,回到王府的時候,時間並不算很晚,蘇傾楣心慌意的,直覺得在王府,本來該是溫煦微涼的秋風,都變的冷冽起來,就和深冬的寒風似的,割的人發疼,讓人窒息。
蘇傾楣本就待不住,坐了一盞茶的時間,就又匆忙離開了。
蘇傾楣在王府就是個形人,出王府並沒有人管,但的一舉一,都是被監視著的。
“七皇子,那個人剛回來就又離開了,神慌張惶恐,應是出了什麼事。”
蘇傾楣前腳剛離開自己的院子沒多久,夜傅銘就得到了訊息。
夜傅銘讓人監視著蘇傾楣,但是如果沒有什麼特殊況,底下的人並不會上報,因為他對蘇傾楣厭惡憎恨至極,就是聽到的名字,都會產生極度的不適,大發脾氣,還是會極度不舒服。
“出事?能出什麼事?今後這樣的事,不要拿來煩我!”
夜傅銘臉鐵青,麵冰冷,口氣惡劣至極,呼吸都是急的,這種彷彿的本能反應,本就不控製。
要說夜傅銘最討厭憎恨誰,那非當蘇梁淺莫屬,但他最不能聽的名字,卻是蘇傾楣。
他是個自尊心那樣強的人,蘇傾楣讓他為全京城的笑話。
自宮中出事後,夜傅銘也是整日都呆在王府,閉門不出,沒臉出去,就是麵對那些什麼都不知道的百姓,他都覺得他們看的眼神都是帶著異樣的,讓他狂躁。
回報這事的下人看夜傅銘那樣子,躬著,嚇得戰戰兢兢,夜傅銘邊站著的一個僧人見狀,擺手讓侍衛離開。
那侍衛出了門,拍著口長長的舒了口氣。
眾多皇子中,七皇子的脾氣一直都是最溫良純善的,就是對下人也沒有架子,和善的好,最近不知怎的,喜怒無常,冷著臉的模樣,眼神狠,彷彿是要嚇人,看的人心驚膽戰。
那侍衛怕歸怕,不過對夜傅銘的印象還是很好的,很快將這所有的一切都歸咎到了蘇傾楣上。
之前蘇傾楣說是賑災發包子做善事,卻害死了那麼多人,現在沒人要了還非來王府,七皇子就是放進門了,心裡肯定也是不願的,脾氣大也是人之常。
他卻不去細想,若是可以選擇,夜傅銘對都厭棄到這程度了,怎麼可能會讓進府?
“七皇子近來喜怒無常,心緒很不平穩,到底是發生什麼事了?”
說話的是個頭和尚,三四十歲的樣子,一副慈善的模樣,可眼底跳躍著的卻不是出家人該有慈善,泛著明的,還有的野心,以及試探。
種種的緒,讓他完全沒有出家人的超,十分的世故,還有老練的深沉。
夜傅銘扭過頭去,低垂著腦袋,沒有說話,鼻孔裡撥出的氣息都是帶火的。
一個多月的時間過去,每每想起那晚上發生的事,夜傅銘都不能平靜,就算再怎麼讓自己沉澱,他依舊不能讓自己平復,反而因為什麼都不能做,還要娶蘇傾楣,為更大的笑話,越發的上火。
那種被的隻能就範的無奈,讓他對權勢更加求。
他的口,每天都是怒火燃燒,那燃燒跳躍著的火焰,幾乎每時每刻都讓他崩潰。
對夜傅銘來說,這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比他曾經最難熬的那幾年還要長久,讓他煎熬,他從來沒想過,自己忍氣吞聲,苦苦經營竟然會是這樣的結果。
本來,他度日如年,日子就已經夠難的了,慶帝居然將那個人強塞到他府上,完全不顧他的意願,更不顧他的尊嚴。
夜傅銘恨了蘇傾楣蘇梁淺,同時也恨了慶帝皇後,還有太子,他恨每一個將他害這樣的人,他想要報復他們,狠狠的報復,不惜一切代價。
而麵前這個人這樣的疑,在他再次陷了那些讓他沮喪又捉狂的回憶當中。
“七皇子。”
那和尚又了聲,雙手合十,“七皇子既然已經讓側妃進門,不如索讓自己接,不管怎麼說,他都是蕭侯爺的外甥,蕭侯爺曾經對是寄予了厚的。”
“你知道什麼?”
夜傅銘扭頭猛地看向說話的人,放在膝上的手因為握的太,青筋暴出。
他最近夜裡本睡不著,氣的也吃不下飯,短短時間,同樣瘦了許多,那雙眼睛沉沉的,完全沒了以往吸引人的溫潤和善,一的煞氣,儼然就是個讓你熱不敢靠近的惡人。
“殿下不說,我如何能得知?”
夜傅銘氣沖沖的說完這話後,很快意識到不妥,看著裴治,神了下來,沮喪又悲傷,“我裴治,你我算是什麼皇子,我到底是不是他兒子?同樣都是兒子,他怎麼能這樣對我?我淪為別人的笑柄,對他來說,又有什麼好?我不要臉的嗎?小的時候就算了,我都已經人了。”
夜傅銘氣憤至極,“王府的人裡麵,我最倚重的就是你,你說,現在我應該怎麼辦?”
裴治看著被怒火燒的失去了理智的夜傅銘,他敢肯定,蘇梁淺慶功酒宴那晚,定是發生了什麼,他或多或得到了點風聲,但是事的全部過程,他無從得知,更不敢在夜傅銘跟前證實。
隻是,夜傅銘這沮喪頹廢的樣子,實在讓他看不到什麼希。
“我不能就這樣算了,我不會就這樣倒下的,我裴治,你幫我想想辦法,隻要我能坐上那個位置,那你就是宰相,我還可以封你做王,賜你封地,或者你想像遠慧那樣,我可以讓你做國師,萬民尊崇擁護!”
夜傅銘最近這段時間確實頹廢,不但閉門不出,府裡那些以和尚存在的謀士,他也幾乎不見,今天要不是裴治大鬧,堅持要見他,夜傅銘也不會見。
他很清楚,自己現在這個樣子,還有這種狀態,隻會讓信任他的人喪失信心。
他朝堂上的助力已經幾乎沒有了,不能讓這些自己心搜刮來的智囊團,也離自己而去,那樣的話,夜傅銘真的連支撐都沒有了。
夜傅銘生多疑,他就是再禮賢下士,也不可能付自己的信任,所以那晚上發生的事,他藏在了心裡,全部都藏在了心裡,誰都沒說。
而他的這種瞞,自然也是很容易讓人生疑和不安的,畢竟夜傅銘招來的這些謀士,大部分都是有真才實學的,並不是傻瓜。
夜傅銘允諾的這些,對任何有野心的人來說,都有很大煽的。
夜傅銘不甘心,那些為夜傅銘籌謀效勞多年的人,何嘗不是如此?要不是為了他日飛黃騰達,為所為,誰願意整日窩在王府這片小天地,這都是為了將來!
“到底發生了什麼讓七皇子變這樣,您要不想說可以不說,但是現在,您已經失了聖心,應當傾盡一切,拉攏可以利用的力量,您最近太過失態了。”
裴治委婉的提醒道。
“不管發生了什麼,這麼久的時間過去了,您也應該平復收拾好自己的緒了,您這個樣子,就是我想再多的法子,您也上不去那個位置,我也不可能封侯拜相,府裡的那些人,除了想在您這裡混吃等死的,真正有本事的,都會離開。”
接下來,裴治和夜傅銘進行了長達一個多時辰近兩個時辰的談話,夜傅銘依舊沒有吐那晚的事,不過卻向裴治了自己因為被設計,慶帝和皇後對他不滿,他最近的頹廢沮喪,正是因此。
猜你喜歡
-
完結1055 章

侯府小啞女
燕云歌自末世而來,重生侯府,她給自己定了個小目標:每天吃好喝好樂無憂!然而……她爹一門心思造反,她哥一門心思造反,她嫁個男人,還是一門心思造反。燕云歌掀桌子,這日子沒發過了!
272.1萬字8 16626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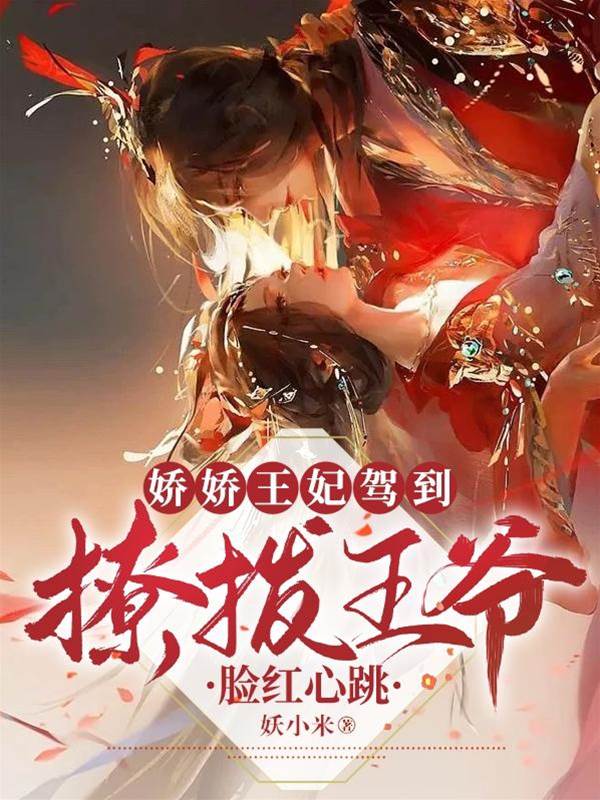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1760 -
完結372 章

穿成短命白月光后,和反派HE了
桑遠遠穿進一本古早玄幻虐戀小說裏,成了男主那個紅顏薄命的早逝白月光。男主愛她,男配們也愛她。女主因爲長了一張酷似她的臉,被衆男又愛又虐又踩,傷身又傷心。和男主的感情更是波折重重狗血不斷,虐得死去活來,結局還能幸福HE。桑遠遠:“不好意思本人一不想死二受不得虐,所以我選擇跟反派走。打擾,告辭。”反派長眸微眯,姿態慵懶,脣角笑意如春風般和煦——“我的身邊……可是地獄呢。”她沉思三秒。“地獄有土嗎?”“……有腐地。”“有水嗎?”“……只有血。”他想看她驚惶失措,想等她尖叫逃離,不料女子呆滯三秒之後,雙眼竟然隱隱放光——“正好試試新品種!”“……”他在最深沉的黑暗中苟延殘喘,從來也沒想到,竟有一個人,能把花草種滿一片荒蕪。
57.1萬字7.92 9560 -
完結313 章
亡國后成了反賊的寵婢
姜嶠女扮男裝當了幾年暴君。叛軍攻入皇城時,她麻溜地收拾行李,縱火死遁,可陰差陽錯,她竟被當成樂伎,獻給了叛軍首領霍奚舟。姜嶠捂緊馬甲,計劃著再次逃跑。誰料傳聞中陰煞狠厲、不近女色的霍大將軍竟為她破了例。紅燭帳暖,男人摩挲著她眼角的淚痣,眸色暗沉,微有醉意,“今夜留下。”*姜嶠知道,霍奚舟待她特殊,只是因為她那雙眼睛肖似故人。無妨,他拿她當替身,她利用他逃命。兩人各有所圖,也是樁不虧的買賣。直到霍奚舟看她的眼神越來越深情,還鄭重其事地為允諾要娶她為妻,姜嶠才意識到,自己好像是在作繭自縛——
49.2萬字8 68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