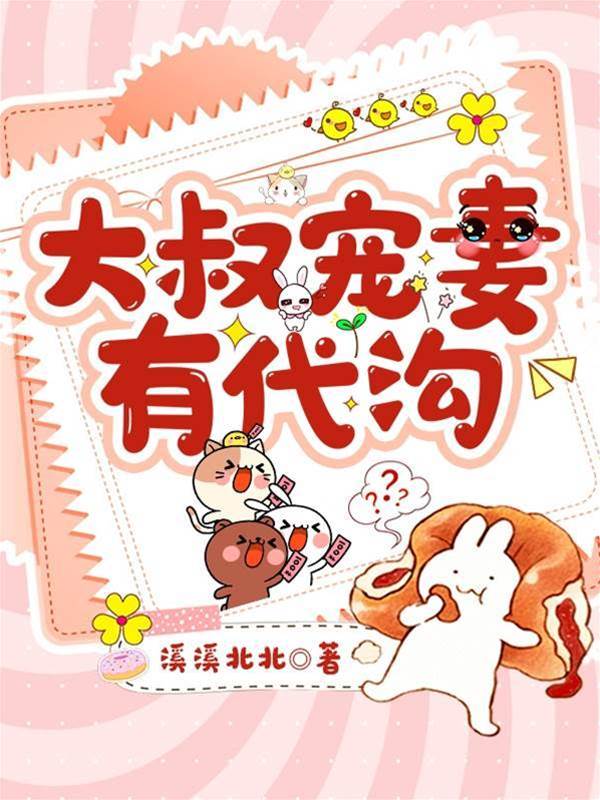《頑烈》 第29章 [VIP]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 傅言真每天都借著看服的名義讓過來。
他這個人找理由也沒想著認真找,裴照每次來轉達都忍不住笑場。
最后自己說不下去,就直接跟曾如初說“傅言真找你”。
但其實在傅言真這里, 能有個敷衍人的由頭就已經是難得給了面子。
沒兩天, 曾如初自己也明白事真相。
打籃球這種劇烈運, 每次都大汗淋漓,怕是恨不能把上的那點布料給扯個干凈才好。
哪里需要什麼外套。
他騙人也不好好騙。
不過傅言真每回占用的時間不長, 就吃晚飯那會的功夫。
最多也就二十分鐘左右。
他在打球。
在旁邊安靜守著他。
他忙的時候,從不開口打擾。
不過帶著外套也是有用的, 屋里快到十一月依舊開著冷氣。
他打球出了一汗,坐那兒不卻是冷的很。
最后傅言真的外套都穿在的上。
曾如初慢慢覺得, 這事像周瑜打黃蓋,一個愿打一個愿挨。
愿意甚至喜歡每天去陪著他。
待在他邊的那麼一小會,竟了一天最快樂的時候。
--
臨近比賽的最后一天。
吃完晚飯后,和趙允恬說去找傅言真。
趙允恬了腦門,一臉的恨鐵不剛。
曾如初不好意思地低下頭。
每回和趙允恬吃完飯后就跑,人也不在班上, 自然本不可能瞞得過。
趙允恬追問過兩次, 就說實話去找傅言真了。
“你又去找他?”趙允恬眉頭一蹙。
“……”
曾如初點了點頭,看到四周還有同學, 此地無銀三百兩地說了句,“你小聲點。”
“孩子,”趙允恬頗有些無奈,“你該不是喜歡上他了吧。”
曾如初想做解釋, 被沒好氣的打斷。
但也沒多言, 嘆了口氣, 難得在上饒過一次。
在趙允恬充滿打量的目里, 到底還是跑去找傅言真。
冒著被發現端倪被堪破真相的風險。
夕吻上后頸皮,慌無措的愫似在推使溫向上攀升。
整個人像正在經歷著一場高燒,腦子里熱烘烘的,混沌不堪。
眼下無暇去想那麼多,只想去找他。
--
籃球館有好幾個場地,傅言真一直在走廊盡頭的那一間。
發現傅言真很喜歡在最里面的位置,門外了人來人往,心理上可能會覺得清凈許多。
但他要真那麼清凈,也不會回回喊過來。
那一間,傅言真整租了半個月。
鑰匙在他手里,他想讓誰進誰才能進來。
回回去的時候,就他一個人。
但旁邊的幾個屋里都有很多人。
到了育館,在大廳的自主販賣機上買了瓶水。
冰的。傅言真要喝。
自己手里也拿著一瓶,在餐廳買的,不冰。
快到十一月份,覺得喝冰的對不太好,在電話里跟他說了,但傅言真又喊小唐僧。
知道是在笑話啰嗦,脾氣一來也就沒多言,還負氣地想著要是喝出病了可別怪,自己著吧。
走到樓上,不巧遇見陸州同和趙海他們。
幾個男生擱走廊上煙,煙熏火燎的。
陸州同還主跟打了招呼。
他們這些人都會玩,之前那點子小事都沒怎麼放在心上。
和打招呼的時候,他神也灑的很。
不過,陸州同現在倒是真有點佩服那姓傅的,這小學霸對他不理不睬的,現在倒也上趕著找傅言真。
他看到過來好幾次了。
趙海現在也不喊“嫂子,”客客氣氣地喊一聲“曾同學”。
曾如初也跟他們一一點過頭。
一旁的幾個男生,都不認識。
但幾個人明顯都認識,其中一個笑嘻嘻地同搭話,“又來找真爺啊。”
一個“又”字,讓曾如初確信,他應該看到很多次。
曾如初只好點頭,臉上有幾分不好意思。
很快有人接上話茬,問來找傅言真干嘛。
沒等曾如初開口,旁邊的門“吱呀”一聲從里面拉開。
傅言真站門口,手里還抓著籃球。
他手指寬大,球被輕輕松松的抓住。
廊上的燈一排排亮著,他手皮很白,被淬的發亮,手背上的青灰經絡清晰。
眼角余掃了眼這只手,心跳倏地加快。
想到這倆天,他教投籃時的作。
傅言真眸無波無瀾地看了過來,幾個人噤了聲。
最后他看著,微扯下。
“進來啊。”他說。聲音夾雜笑意。
曾如初著頭皮,從他側鉆過。
幾個男生擱門外笑的意味不明。
有人沒忍住揶揄了句說:“這門一關,有點東西啊。”
曾如初不用回頭看,聽都能聽明出他們話里話外的不正經。
又有個膽大的笑了聲,“真爺,讓我們進去瞧瞧啊。”
傅言真淡淡一句:“不喜人多。”
幾個人被攔在門外嘿嘿直笑。
高墻擋住風塵,木門一合,戲謔笑鬧也慘遭隔絕。
屋里和往常一樣,都是冷哐哐當當的聲響。
和傅言真在里面,真的沒做什麼。
傅言真做他想做的事時,其實很專心。
找說話也都是在休息時候。
這一周,他都沒上過晚自習,都在這邊練球,曾如初走后,他會喊育生過來陪練,因為怕不好意思,所以在的時候,這里沒有別人。
他很不喜歡輸。
痛恨那種滋味。
如果決定要做,就必須要贏。
他上衫早已被汗水打,料著背脊,映出肩胛骨的廓。
曾如初看了許久,忍不住說了聲,“你要不要歇一會兒?”
明天就要比賽,今天是不是應該留點力。
傅言真視線看了過來,這才發現曾如初還在,有些意外的挑眉。
今天在這里待了久,已經超過半個小時。
他眼下額頭都是汗,往下墜。
走過來時,扯了下領抹了下臉。
T恤整個上移,腰腹出一截,線條實利落。
曾如初不小心看到,臉驀地一紅。
傅言真松開手,領往下墜落,就看到盯著自己的腰。
撞上目,曾如初慌里慌張地錯開視線。
傅言真默不作聲地走到跟前,舌尖輕抵角,“好看嗎?”
曾如初想都不想:“不好看。”
傅言真笑出聲。
磁啞的一聲,帶著點輕浮。
曾如初這時也反應過來,剛剛那句泄了不小心看到的事實。
脖頸一彎,臉朝小臂里埋了半截。
傅言真看到不好意思,卻還不輕易饒,抬腳踢了下鞋尖,又揶揄:“得了便宜還賣乖。”
“……”
沒一會兒,他過手,朝遞過來,招了一下,意思是要拿個水。
曾如初順手拿起放在一旁的東西,擰開蓋子給他遞了過去。
手上沾著汗,有時候其實不太好擰。
曾憶昔之前打球的時候就讓擰好給他,養了習慣。
傅言真接過來灌了一大口,忽地發現不對勁,微皺了下眉:“不是冰的?”
“是冰的啊,我剛剛在樓……”
沒解釋完,傅言真將水遞到手上,“你。”
手了一下。
僵住。
“……”
傅言真低眸看著,也不多說什麼。
曾如初往一旁看了眼,差點咬到自己舌頭,“……我拿錯了。”
“對不起。”
他手里這瓶是的。
還喝過。
傅言真悶悶笑了幾聲,不聲地看慌無章。
忙拿起另一瓶,向他遞了過去。
傅言真沒接,仰頭將手里的這瓶喝完。
然后慢慢蹲下子,與平視。
曾如初不知道他為什麼知道是的,他還喝。
看著他,有些愣愣的。
須臾。
“曾如初。”傅言真喊了聲的名。
“干什麼。”曾如初說。
已經道歉了。
也不是故意的。
他也喝的香的,不是麼。
“你說說,這算不算。”傅言真著手里的空瓶子,塑料瓶在他骨節分明的指間咯咯作響。
“接吻啊。”
“……不算。”曾如初張到繃子。
傅言真卻還直勾勾地盯著,把盯的渾發。
兩手從膝上移開,起就想跑,卻被傅言真拉住手腕。
他一個用力將又拽落下來。
“是不是故意的。”他扣著手腕不讓。
“不……不是,當然不是啊。”
“我就當你是故意的。”他笑了聲。
“……”
他臉上的壞不加掩飾。
看著,放浪形骸地。
空的場館,被他上的氣息一點點填滿。
籃球滾落至墻角,抵墻靠著。
被傅言真按在跟前。
小到他的。
隔著布料,能到那灼人的溫。
“今天怎麼待這麼久,”傅言真著聲,存心逗,“舍不得走啊。”
猜你喜歡
-
連載958 章
俏皮甜妻娶進門
被送給活死人做沖喜小妻子的夏安然,隻想裝蠢賣醜,熬死老公後跑路。可是,躺在床上的活死人老公,怎麼轉眼變成了冷酷毒辣、心狠手辣的的商業帝王?最最最關鍵的是……她之前才一不小心、趁火打劫,將他吃乾抹淨了!!!肚子裡揣著的那顆圓滾滾種子,就是她犯下滔天罪孽的鐵證!夏安然抱著肚子,卑微的在線求救:現在跑路,還來得及嗎?淩墨拖著試圖帶球跑的小妻子回家,一邊親,一邊逼她再生幾個崽崽……
88萬字8 61172 -
連載768 章

婚婚欲睡:陸少夫人要離婚
童心暖暗戀陸深多年,最幸福的事就是嫁給陸深,結果……新婚第一天,陸深的白月光帶著孩子回來了,新婚第二天,她的父親死了,自己被逼流產,新婚第三天,她簽下了離婚協議,原來陸深從未愛過她,所謂的深情都是她自以為是而已。
170.3萬字8 38334 -
完結5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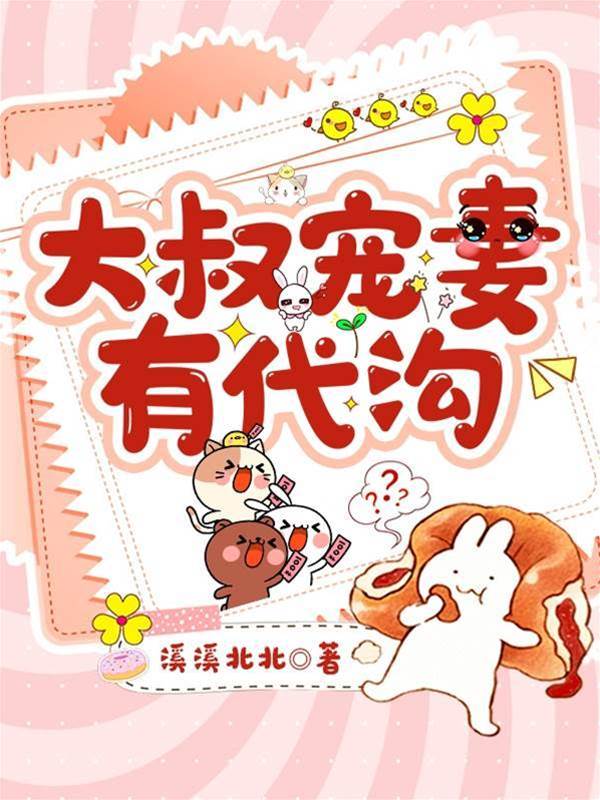
大叔寵妻有代溝
等了整整十年,心愛的女子終于長大。略施小計民政局領證結婚,開啟了寵妻之路。一路走下,解決了不少的麻煩。奈何兩人年紀相差十歲,三個代溝擺在眼前,寵妻倒成了代溝。安排好的事情不要,禮物也不喜歡,幫忙也不愿意… “蘇墨城,不是說,你只是一個普通的職員嗎?怎麼現在搖身變成了公司的總裁。” “蘇墨城,不是說,以前你根本就不認識我嗎,那你父親和我母親之間怎麼會是這種關系?”
55.3萬字8 51533 -
完結2072 章

幸孕六寶寵上天
一場陰謀,她被親爸賣了,還被人搶走孩子,險些喪命。五年后,她帶著四個孩子強勢回國尋找孩子,懲治兇手,沒想剛回來孩子就調包。發現孩子們親爹是帝都只手遮天活閻王顧三爺后,她驚喜交加,幾番掙扎后,她舔著臉緊抱他大腿,“大佬,只要你幫我收拾兇手,我再送你四個兒子!”三個月后,她懷了四胞胎,“顧南臣,你個混蛋!”“乖,你不是說再送我四個兒子嗎?”顧三爺笑的很無恥,逢人就夸,“我老婆溫柔體貼又能生!”她:滾!
198.5萬字8.18 525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