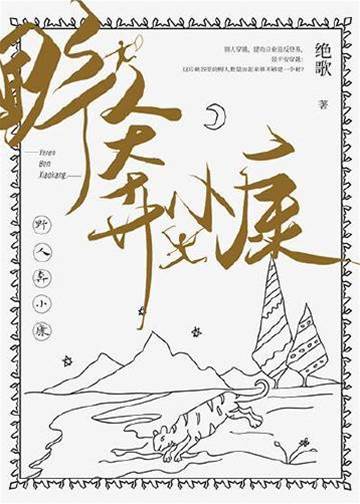《女商(大清藥丸)》 第32章
“哎呀哎呀, 怎麼弄這個樣子,你們這些后生仔喲……”
紅姑一邊劃船,一邊皺著眉頭嘮叨。
小船靜悄悄地離岸, 等兵趕到之時, 河灘上重新黑, 半個人影都不見。
林玉嬋找塊抹布,干凈手上上的泥水, 朝紅姑正正經經地行了一禮。
“謝謝你……”
“嗨呀嗨呀, 客氣什麼。”紅姑爽朗笑道,“惹著哪個老爺了?怎麼被這許多人追?”
紅姑夠意思, 明知兵在追捕, 還是爽快救人。但若知道兩人犯了什麼事,也許就笑不出來了。
林玉嬋猶豫了一下:“嗯……河邊鬧叛匪, 我們不合走得近些, 被流彈誤傷了。”
紅姑免不得又罵幾句狗不識相, 跟洋人一個德,敏爺這樣的好人也冤枉。兵不講理, 誤傷了平民也沒補償, 真真啞虧。
蘇敏靜靜臥在船艙里。長衫上盤扣散, 已經止住了大半, 浸了紅姑三四塊洋布巾。
他臉極白,如一尊西洋石膏像, 只比石膏像多出微弱的膛起伏。
凌的發懶洋洋的在他耳后。其實晚清時節, 男人們的頭發并不像電視劇里似的,前半邊腦門總是可鑒人——富貴閑人才有功夫倒騰這些。尋常百姓沒時間理發, 前面的腦殼經常茸茸,扣個帽子蓋上完事。
老古板們對此痛心疾首:如此儀容不整, 放在康熙爺乾隆爺那會兒,這樣是要殺頭的!
所以蘇敏甩了辮子的形象也并沒有很禿然——他自帶一層短短碎發,平時戴著帽子也不需要什麼造型,就是無拘無束地自由生長,隔一陣自己隨便拿剃刀一刮,刮出個清爽小寸頭。又襯著一傷,活像個剛伍就掛彩的年輕小兵。
讓他整個人仿佛從大清到民國,穿越了一個時代。
林玉嬋不由自主地微笑,心想再過五十年,滿街小伙子就都是他這樣了。
紅姑一看之下,卻極驚嚇,著自己后腦勺:“辮子呢?那麼長那麼的辮子呢?”
林玉嬋忙道:“被火燒了,你別害怕。”
紅姑問:“去哪?要不要先去我家?”
林玉嬋連忙擺手:“先在水上漂著吧。拜托。”
其實眼下最需要的,是給蘇敏找個洋醫館。但只要上了岸,哪兒都不安全。
好在沒傷及臟腑骨骼,命無虞。只是他遍泥污,急需清理。
林玉嬋請紅姑燒開一盆熱水,要了盒鹽,并一條干凈手巾,走進船艙,解他扣子。
蘇大舵主本來在裝睡,本著言多必失的原則,盡量跟紅姑說話。
裝睡慢慢變真睡,一片溫暖的黑暗包圍他,不能自拔。
他想起年母親的懷抱,臥室里的西洋自鳴鐘滴答響。
他約知道家里是“會黨”。大清立國以來,反抗力量不斷,尤其是南方,不愿屈服的人們逃去邊陲小島,逃去臺灣,逃去南洋、緬甸,或者干脆做了海盜,扯一張旗,四海為家。
剩下的留在家鄉,相互守,蟄伏待發。
清廷實行海,片帆不得下海,僅留了廣州一通商口岸,招攬行商,主要負責給京城的皇帝采購西洋珍寶。
正經人哪有機會做外貿生意。敢下海撈金的,多多跟那些法外之人有千萬縷的聯系。
這就是十三行的誕生之路。
等到十三行發展壯大,地方赫然發現,這些日進斗金的行商,竟然半數都了會,私下里拜的是大明朱家!
——老爺們聰明地選擇了不聲張。十三行是務府的錢袋子,沒了這些行商,他們的鐘表、花瓶、琺瑯、牙雕,還有東征西討的軍費……都從哪來?
況且,朱家脈如今已微不可尋。斗轉星移,心念舊朝的人也死得差不多。天地會對朝廷的威脅日益減,淪為一個尋常無害的江湖幫派。
但世事難料。隨著洋人炮轟國門,清廷基搖,這些“會黨”仿佛又看到了機會,開始蠢蠢,組織叛!
朝廷終于下決心理這個心腹大患。與洋人合力,慢慢絞殺。十三行一個接一個的倒下,縱然他們竭力撇清與會黨的關系,也擋不住那一雙雙貪婪的眼睛,從四面八方覬覦那富可敵國的財富。
年的小爺約記得,抄家之后一地,人的哭聲尖盈耳。各路真假債主都聞風而來,趴在巨富的死尸上,企圖吸到最后一滴。
當時他還是個孩,全無自保之力。世伯金蘭鶴把他救出來,給了他容之地,待他年紀稍長,流出家傳的做生意的天分,又介紹他去怡和洋行,吃面的洋人飯。
他其實不太喜歡那里。過去是洋人卑躬屈膝,求著十三行的紅頂商人,給他們一條東方淘金的門路;如今風水倒轉,到中國人向洋人低頭。
不過,好在他有能耐,會賺錢,洋人便能忍他的冷淡。
“天滅大清,送來洋鬼子。”他記得金蘭鶴說,“你別怕委屈,和洋人搞好關系,日后滅清之時,洋人說不定也能助我等一臂之力。”
在洋人手下當了幾天二等公民的蘇敏對此不以為然:“洋人只圖利,才不會真心幫我們。”
金蘭鶴斥責他不懂事。
等到他十五歲,會拜把子的時刻,又出幺蛾子。他指著畫像上的明太`祖,大言不慚地說:“佢系邊個,我不認識。不跪。”
把整屋子元老們雷得七竅生煙,連嘆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他的份一直尷尬,雖然背了切口,足了訓練,悉了天地會一切,始終沒上過那三柱半的香,未能為正式的會眾。
但造化弄人。當他尋到中數槍、彌留之際的金蘭鶴時,也不自地流淚,接下他的缽,剪發明志,發誓要將反清事業進行到底。
所以……他到底是誰呢?
“嘶……”
他從疼痛中驚醒。一低頭,發現自己上未著寸縷,林玉嬋拿著一條手巾,輕輕的,把他前的斑斑駁駁五六掉,出干凈的,和咧著的傷口。
他差點跳起來,抓起個裳就想往上蓋。手臂一,牽傷口,眼前一黑,不自覺弓起后背,抓手邊巾,抑住一聲悶。
“我……我自己來就行。”
林玉嬋眼皮不抬,輕手輕腳地把他四肢擺正,說:“別逞能,你今日勞苦功高,安心當一回病號。”
他脯結實朗,手下稍微重些,就引來一陣劇烈起伏。
他滿頭大汗,咬住臉旁邊的枕巾。紅姑繡的,還帶魚腥味兒。
他還是緩慢地抬起手臂,抖著到自己赤`的前,忽然臉微變,呼吸一下子急促起來。
“找這個嗎?”林玉嬋連忙把一小枚吊墜塞到他手里,“弄臟了,我摘下來洗了一下。”
那是一枚做工致的金鈕翠玉長命鎖,綴在紅繩上,他一直戴著,被揭開了裳才看見,可見珍視。
鎖片的一側被高速的泥沙擊中,缺了一個小口。
蘇敏握住玉鎖,拇指挲到那個缺口,朝輕微點頭,閉了眼。
“泥彈”把他的傷口弄得一片狼藉,玉鎖是沒法再掛上去了,林玉嬋小心收好。
仔仔細細地將他上的污一點點掉,一邊自語:“不怕疼吧?——你肯定不怕,那我就不客氣了。唉其實這種傷口是最好要打破傷風針的,現在好像還沒有……那對不住,用生理鹽水沖一下吧,0.9%,手工調配,希誤差不大……破傷風桿菌好像是厭氧菌,也不能包扎,先晾著吧……”
這些都是高考考點,新鮮熱辣,林玉嬋一點沒忘。
蘇敏被弄得半暈半醒,聽唔懂講咩,只能任其宰割。他悲憤地抬頭看天花板,發現過去在面前的高冷形象都白裝了,這丫頭現在看他就像看弟弟。
他半睜眼,看到小姑娘鼻尖冒汗,小耳朵珠上還殘留著沒凈的泥污。他上倒已干干凈凈,清爽得像剛沖涼。。
他干裂的,冷冷淡淡地說:“你再耽擱下去,別想平安回齊府。”
“去他老母的齊府!”林玉嬋突然激起來,重重放下水盆,“不回去也罷!”
原本對這個剝削吃人的大地主家就沒啥好,販茶葉起碼是合法生意,剝削就剝削了;但沒想到他們背地里還販奴,那個屎尿橫流、人摞著人的豬仔館,比齊府下人的廁所還要骯臟百倍。
事后想想,齊老爺肯定是主謀,負責疏通府;王全是跟買主牽線的,經驗富;其余的人不一定對此知。對了,賬房詹先生面對茶葉生意的巨額虧損,經常愁眉苦臉,而王全總是不以為意,說什麼“老爺還有放貸收、田產收,虧不死人啦”。
猜你喜歡
-
完結386 章

毒舌醫女穿越記
在古代,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是以,欠下賭債的父親要將自己賣了換取錢財,沈淩兒別無他法,隻能一死了之。誰知死人竟有復活日,沈寶善大喜:「既然沒死,趕緊嫁人去!」然而,這柔弱的身體中,已換了個接受現代教育長大的魂魄。什麼三從四德,愚孝夫綱,統統靠邊!憑著一手精湛醫術,金手指一開,沈淩兒脫胎換骨,在古代混得風生水起。誰知,穿越之初撿來的那個男人,竟越看越不簡單。毒舌女對戰腹黑男,誰勝誰敗,尚未可知吶。
101.3萬字8 22659 -
完結20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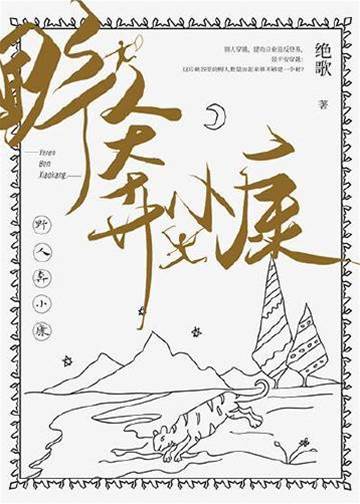
野人奔小康
景平安在職場上辛苦打拼,實現財富自由,卻猝死在慶功宴上,悲催地穿越成剛出生的小野人。有多野?山頂洞人有多野,她就有多野,野人親媽茹毛飲血。鉆木取火,從我開始。別人穿越,建功立業造反登基,景平安穿越:這片峽谷里的野人數量加起來夠不夠建一個村?…
80.8萬字8 5279 -
完結626 章

我,開局輔佐嬴政,成為六國公敵
張赫穿越大秦,獲得最強輔助系統,只要輔助嬴政,便能獲得十連抽。于是張赫踏上了出使六國的道路,咆哮六國朝堂,呵斥韓王,劍指趙王,忽悠楚王,挑撥齊王,設計燕王,陽謀魏王。在張赫的配合下,大秦的鐵騎踏破六國,一統中原。諸子百家痛恨的不是嬴政,六國貴族痛恨的不是嬴政,荊軻刺殺的也不是嬴政。嬴政:“張卿果然是忠誠,一己擔下了所有。”張赫拿出了地球儀:“大王請看……”
122.8萬字8 8437 -
完結293 章
這個將軍是我的
醫學博士洛久雲被坑爹金手指強制綁定,不得不靠占她名義上夫君的便宜來續命。 偷偷給他做個飯,狗狗祟祟盯著人家的手。 魏巡風:這個姦細一定是想放鬆我的警惕! 洛久云:悄悄拉過男人修長的手指,反覆觀看。 看著他矜貴又懵懂容顏,想,他可真好看。 面對時不時被佔便宜的洛久雲,某日魏大佬終於......後來,魏巡風:這女人,真香!
51.4萬字8 926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