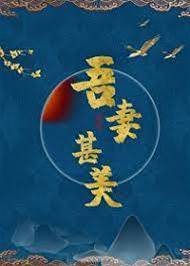《諸事皆宜百無禁忌》 第59章 忌飲茶 秋欣然叫他這反應逗樂了,瞇著……
青龍寺回來不久, 吳朋的案子似乎有了進展。沒幾日一隊兵查封了芳池園,樓中眾人都被府帶走問話,約傳出流言, 說是沒有什麼鬼作祟的事, 這一回吳家公子恐怕是園里的姑娘給設計了。
過兩日, 周顯已來何記飯館秋欣然忍不住同他打探此事。對方沉片刻,湊近了同低聲道:“看在你我的份上, 我倒是能同你說上幾句, 不過你可萬萬不能說出去。”
秋欣然忙也湊近了些保證:“我必定不往外說。”
周顯已得了的保證,這才神神地問:“你知道芳池園背后真正的主事是誰?”
秋欣然一琢磨, 小聲問:“蘭蕙?”
周顯已一愣,瞪著眼睛看,見無辜地瞧著自己, 又問:“那你知道蘭蕙真正的份是什麼?”
“前羽林軍統領章永的兒章卉?”
周顯已一下坐直了子, 氣呼呼道:“你都知道,你問我什麼?”他二人大眼瞪小眼半晌,他又忍不住湊近了問,“此事朝中都還沒幾個人知道, 你是從哪里得知的?”
秋欣然他這反應逗樂了, 瞇著眼笑:“天機不可泄。”
周顯已將信將疑地瞥一眼,撇撇繼續說:“錢主簿也不知從哪兒得到的消息,查出了章卉的份。他大約還想著去同左相邀功, 結果沒想到章卉當庭就認了, 還直接當堂呈上訴紙為章家喊冤, 還說自己手上有當年章永被人陷害的證據。當年夏世子行宮被綁本就是樁大案,何況里頭還牽扯到了迖越人,茲事大, 大理寺不敢瞞立即呈報上去。原本是個樂伶失蹤案,這會兒又牽扯出了羽林軍舊案,連圣上都驚了,下令刑部、史臺協同辦案。為這事我已住在舍幾日沒有回家。”他說完嘆一口氣。
秋欣然沉默片刻忽然道:“顯已還記得一年秋獵,談及章大人的案子,我曾說你剛直,日后出仕或許能當個秋,替忠良替百姓發聲。”
周顯已顯然也想起了那天的事,微微笑起來:“怎麼不記得,就是因為你那番話,那天之后我才了做秋的念頭。”
“那天你說日后若是出仕,必定不我失。”
周顯已像是聽出話里的意思,怔怔地看。只見秋欣然笑了一笑:“到今日,此案無論是什麼結果,我都相信顯已不會我失。”
著眼前子溫和如水的目,周顯已心中一熱,他袖下的手忍不住了下拳頭,也笑起來:“京中傳言欣然一卦不錯,我必不能你在我這兒砸了招牌。”
芳池園查封不久,蘭蕙即是章卉的消息也在朝中不脛而走。在長安幾年,接許多朝廷要員,手中拿到了一些證據,證明當年指證章永虧空賬簿、勾結迖越人的罪名蹊蹺,且直指羽林軍部貪污腐敗,黨同伐異。十年前的餉銀虧空一事,似乎另有。章家舊案被重新翻了出來,此案的矛頭直指現任羽林軍統領韋鎰。
宣德帝在朝會上聽大理寺呈報案,轉頭去問站在殿上的定北侯:“聽聞修言回京后也與此相識?”
穿朝服的年輕侯爵站直子,沉片刻之后,謹慎回稟:“確有此事,當年章家事發是因為臣行宮被擄,想來自臣京之后,幾番接近是想借此打探當年的事。”蘭蕙這幾年接不京中與此事有關的要員,主接夏修言倒也不足為奇。
宣德帝于是又問:“既然如此,關于此事你有什麼看法?”
夏修言諫言:“臣在北地駐兵多年,不通朝中政務。但若是尋常貪腐便罷了,如果牽扯到外敵,臣以為還需慎重。”
宣德帝點一點頭:“既然如此,此案就由大理寺刑部協同重審,務必查個水落石出。”
章永獲罪之后,羽林軍統帥韋鎰是左相一手扶持。如今章永案被翻出來,韋鎰首當其沖牽涉其中,下朝之后,左右傳言左相離開宮門時,臉鐵青,步履如飛。
朝中風云已起,勢力的天平開始發生微妙的傾斜,而這一切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哪?是從吳朋獄開始?還是從定北侯回京開始?
不知怎麼回事,秋欣然后知后覺地發現周圍的人都忙碌起來,好像只有一個人依舊無所事事。市井日子十分太平,原舟忙里閑來看一回,自打上回落水后,二人似乎已經許久不見。這回面,只見他眼下青黑,神倦怠,像是已有幾日沒有好睡。
“司天監忙這樣?”
原舟搖搖頭:“近來朝中事多,想來你也聽到一些風聲。圣上這兩年有擬定東宮的意思,師父要我提醒你,若是得圣上傳召,切記不要摻和到這件事當中去。”
“老師覺得圣上會找我去算命數?”
“圣上篤信鬼神,若當真找你去,雖不一定當真聽你相卦,但無論你說什麼,于你都是一樁麻煩。”
這種有關東宮的辛原是不應當對外的,秋欣然看他一眼:“這話對我說過一次也就算了,千萬別同其他人提起。”
原舟聞言笑了一下:“這我自然知道。”他有些慨似的:“當年還在宮里的時候,這話總是我對你說,沒想到有一天倒是你反過來提醒我。”
“我看你就是自己憋不住話,才跑來這兒說給我聽。”秋欣然替他倒一杯水, “師父師伯總覺得你比我老實,其實你都是心里憋著壞,就想我帶你干點什麼出格的事。”
原舟失笑:“這可冤枉,論出格我拍馬也及不上你,就說七年前定北侯那一次……”他話說一半自覺失言,倒是秋欣然不以為意。原舟打量著的神,還是不住好奇道:“當年你跟師父說的話,其實我都聽見了。那時候也就算了,現在你同侯爺解釋一下,未必不能解了這個過節。”
秋欣然搖頭:“他年時被帶到長安,宮里人當面稱他一聲世子,心里都清楚他來這兒是怎麼回事。他斂,心思又重,那幾年對他來說不是一段好回憶,要是再知道琓州之困時,圣上曾對他起過殺心……”
原舟一驚:“你怕他與圣上反目,生了反心?”以夏修言那睚眥必報的子倒確實不是全無可能,他想到這一節,心中也有些惴惴:“可你不說,他就察覺不到了嗎?”
“圣上對他不是沒有一點舅侄的分,當年那種況,若下定決心要除去他不是沒有別的法子,我敢算那一卦,也是賭圣上對他的還有幾分猶豫在。”秋欣然垂著眼,“此事系于我一人上最好,免得再旁生什麼枝節。”
說完這句,二人半晌無話。秋欣然平日里看著一副沒心沒肺的模樣,這種時候卻顯出幾分與往日不同的沉靜來。原舟打量著,最后面古怪地憋出一句:“你連這話都敢說,還敢說我議論東宮?”
議論圣上確實比議論東宮的罪名大得多,秋欣然不失笑:“那你說說東宮吧,免得只有我落了個話柄在你手里。”
“東宮……倒也沒什麼好說的。”原舟皺著眉在心里轉了一圈念頭,“你猜是誰?”
“論出,自然是三皇子和六皇子最有資格,但恐怕朝中大皇子與二皇子的呼聲也不小。”
原舟點點頭算是默認了的推測:“自從定北侯回京,圣上對他榮寵有加似乎已經勝過左相,我看應當也有借勢打淑妃母家勢力的考慮在里頭。”
兩相制衡,帝王之,無論何人了局中,皆為棋子。秋欣然著正東邊看不見的皇城,嘆一般低聲道:“左相不是只會被挨打的人,他應當很快就該做些什麼了。”
原舟走后,秋欣然心中總有些不安,近午驅車去了芳池園。前幾日還是笙歌鼎沸的清雅宅院,大門上已經被上封條。每個路過此的人都忍不住朝著里頭多看一眼,似乎想過磚墻的隙窺伺到白墻后的。
秋欣然方下車就瞧見正門口站了個紅的影有些眼,正想著就見那人轉過來,遠遠的也一眼看見了,皺著眉似乎正在心中回憶二人在哪兒見過。秋欣然見朝自己走過來,等走到近前又停住了上下打量兩眼,忽然開口道:“我是不是見過你?”
這子同高旸真是天差地別,秋欣然覺得有些好笑,于是好脾氣地回答道:“不久前在定北侯所住的邸確實與姑娘有過一面之緣。”
這樣說,高玥立即就想了起來,那一回拿鞭子甩人,差一點傷著了站在一旁的一個道士,哥哥罰了在府里閉門思過,也是今日方才解了門。想到這兒,不由悻悻:“上回不好意思,我那一鞭不是沖你去的。”
猜你喜歡
-
完結223 章
爆寵醫妃之病王太腹黑
賞花遊船之上,赫連箐慘遭未婚夫與嫡姐的背叛,被未婚夫一巴掌扇落湖底!再次浮出水面,靈魂互轉,已然不是曾經的她.她穿越而來,成爲了將軍府人人口中的醜顏庶女.嫡母設計,讓她嫁給那個終日咳血的殘廢王爺?她忙拍手叫好:不用生包子,不用被束縛,這婚事她實在是太滿意了.他是天聖皇朝的七皇子,被人欺辱、踐踏,卻從不敢反抗,外人眼中的廢物!卻無人得知,他這副身殘體弱之下,擁有著怎樣強大的力量,手中握著龐大的消息來源,更無人得知他是讓人聞風喪膽、殺人不眨眼的魔教教主!一紙賜婚,她與他成爲了世人眼中的笑柄:醜顏配殘廢!堪稱絕配!【婚前小劇場:】某女看著坐在輪椅上,卻依舊風華絕代的男人,霸道的開口."王爺,如果你答應我三個條件我就嫁給你了!""恩?""第一,婚後你不許碰我!拒絕生包子!""我身體殘廢!""第二,婚後你如果有喜歡的女人我就成全你!""我身體殘廢!""第三,婚後,我的錢是我的,你的錢還是我的!""恩!我是你的!"
72.4萬字8.33 161123 -
完結296 章

神醫殘王妃
父親失蹤,母親病倒,眾親戚粉墨登場,搶家產,爭地位,欲除她而後快。皇上下旨賜婚,許她榮華富貴,卻隻把她當棋子。敵國太子對她百般柔情,處處維護,卻暗藏驚天禍心。殘廢夫君對她視如不見,卻將她推入陰謀漩渦。羅剎門主半夜爬進她的房,誘她紅杏出牆,當真居心叵測。明槍暗箭,接踵而至。魑魅魍魎,競相登場。她輕蔑一笑,扭轉乾坤。鐵騎錚錚,縱橫天下。
79.8萬字8 16781 -
完結953 章

將軍的病弱美人又崩人設了
傅明嬌是知名網站作者,曾被評為虐文女王,后媽中的后媽。在她筆下be了的男女主數不勝數,萬萬沒想到她居然穿進了自己寫的虐文里,成了男主的病弱白月光。明明生的容色絕艷,傾國傾城,卻心腸歹毒如蛇蝎,仗著家世顯赫身體病弱,以治病為由百般誘騙男主,讓…
84.8萬字8 19440 -
完結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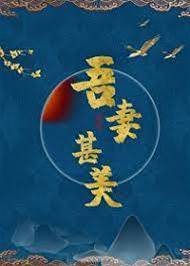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136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