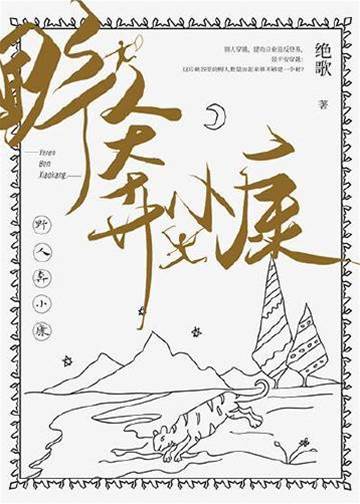《國子監小食堂》 第103章 酸菜豬肉餃子
過了子時,便是大年初一,時人常稱之為“元日”。
孟桑出來時沒披上厚實外袍,雖然有謝青章的大氅圍著、之間的甜氣氛烘著,但到底有些敵不過冬日寒冷。
等勁頭過去,手邊沒有熱飲、暖爐取暖,立馬就哆嗦了起來。
謝青章心細如發,在懷中人剛開始抖的那一瞬,就已經發覺對方的異常。
他一邊在心里懊惱自己沒有考慮周全,一邊將上的大氅解下來,作小心地將它披到孟桑上:“外頭冷,時辰也不早了,快些回去吧。”
孟桑著厚實的大氅,眨眼道:“那你現在就回宮了?”
謝青章頷首,溫聲道:“宮中宴席未散,今日還有大朝會,怕是要在宮中留許久。我與耶娘商量好了,等到今日下午再來給姨母、姨父拜年。”
聽對方這麼一說,孟桑忍不住嘆——雖然都是吃公家飯的,但本朝的文武百與后世的公務員相比,那可太累了。
與圣人親近些的員,除夕夜就得去宮中赴宴,陪著圣人一道飲酒作詩、守歲過節,興致高漲之時,某些員還得下場跳個舞。
待到熬到第二日,員們都來不及回府補覺,就得排起長龍一般的隊伍,準備一年一度、最為隆重莊嚴的元日大朝會。拜圣人、見地方員與藩國來使、拜皇太后……這麼一番冗長繁復的流程走下來,只怕雙眼都要冒金星,累到一回家就癱倒。
年都過不好,怎一個慘字得了啊!
孟桑這麼想著,忍不住打了個寒,拽著謝青章的服袖子,道:“如若你與姨母他們太累,明日再來,或是我們家過去,都是可以的。”
謝青章莞爾,放輕作幫整理好被寒風吹的鬢發:“還是要來的。畢竟我家耶娘一直盼著你早些嫁過來,尤其是阿娘,恨不得早些將姨母的耳子吹。”
孟桑心里頭甜津津的,故意問他:“那你呢?”
聞言,謝青章輕咳一聲,耳廓攀上一層紅意:“自然……自然也是期盼著的。”
孟桑輕飄飄地睨他一眼,笑哼道:“算算日子,從表明心意到現在剛好半月,哪有那麼快就開始談婚嫁之事的?”
話雖這麼說,但眼中、眉梢間的笑意卻怎麼都淡不下去。
而謝青章難得見這麼一副俏模樣,不免有點心猿意馬,只憑著骨子里的君子氣,強行下那子沒來由的躁。
借著星、月,以及周遭屋舍里躥出的沖天火,二人四目相對。周遭氣氛越發旖旎,仿佛連寒冷的風都在一瞬間放緩、相互糾纏。而懂事的踏雪,十分乖巧地站在一邊,馬尾輕輕甩著,幾乎不曾發出任何靜。
孟桑雙頰泛著薄紅,先是清了清嗓子,然后手將謝青章往馬兒那推:“時候不早了,你早些進宮,興許還能小憩片刻!走吧,走吧!”
謝青章牽起馬兒的韁繩,忍不住地上揚:“好,都聽你的。不過你先回宅子吧,等大門落好栓,我再離開。”
“哦,哦……”孟桑脖子,連忙提著角離開,合上大門前,沖著謝青章出一個明的笑來,“午后見。”
謝青章頷首,靜靜看著大門合上,一直等聽著落栓的聲響傳來,方才翻上馬,驅著踏雪離開此。
而大門另一邊,孟桑聽著馬蹄聲漸漸遠去,隨后滿面笑意地往院走,步伐輕快地回到正屋。
推開屋門時,特意將作放得很輕,以免將家阿娘吵醒。
哪曾想,進了屋、繞過屏風,還沒來得及將上穿著的大氅和其他冬褪去,立馬撞床榻上裴卿卿的雙眸里。
裴卿卿側臥在床榻上,面朝窗外,靜靜過來。借著床邊桌案上留的一盞燈,可以清晰地瞧見的眼底沒有一分一毫的睡意,顯然清醒許久。
孟桑著家阿娘那冷靜的視線掃過來,不由抿出一個乖巧又禮貌的假笑:“哈哈……阿娘你還沒睡呀?”
裴卿卿挑眉,完全不想配合孟桑轉移話題,而是微微抬起下,隔空點了一下對方披著的大氅上,似笑非笑:“謝青章走了?”
孟桑的眼睫眨啊眨,乖乖回道:“走了。”
聞言,裴卿卿點了點頭,只評價了一句“確實表里如一,人后都很有分寸”,隨后嫌棄道:“趕上來,這燭火晃得我眼睛都花了!”
見此,孟桑樂了,飛快將繁瑣的裳去,吹滅唯一一盞燭火,然后火速鉆進被家阿娘焐得暖乎乎的被窩:“阿娘最好啦!”
將四肢牢牢纏在裴卿卿上,笑嘻嘻道:“阿娘,你是不是也覺得阿章好的?”
裴卿卿上嫌,卻誠實地將兒摟住,十分客觀地說道:“這小子一招一式雖然很規矩,但卻不死板,十分靈活。”
“面對強和疲憊,他可以一直堅持握刀,不輕易言棄;對于旁人的批評,也能虛心教,在之后的練武中慢慢改正。”
“武學見人品,從這方面而言,謝家小子確實無可挑剔。”
聽著從家阿娘口中說出的夸贊之語,孟桑與有榮焉,笑意更濃。剛想說些什麼,就聽見了裴卿卿的下文。
裴卿卿嫌棄道:“不過,雖然他武風很正、悟亦佳,但明顯實戰不足,短短幾日沒法提升太多。”
“昭寧子單純,有時慮事不周也就罷了。怎麼謝君回也不曉得給自家兒子找個靠譜些的武學師父?嘁,我當年果然沒看錯,謝君回這個狐貍真是靠不住!”
“咳咳,現在不是有阿娘您嘛……”孟桑嘿嘿一笑,抱得更些。
裴卿卿哼笑一聲:“既然都曉得是為他好,那我練他時,你可別總是心疼。連昭寧和皇太后都沒說什麼,就你趕著勁兒地護著!”
“殊不知,與我當年吃的苦相比,他這可算不得什麼。那時候,阿翁見我鐵了心要學武,便花重金、托人,最后尋來數位武藝高強的師父,不帶停歇地教我。那時候啊……”
說起這些快活的往事,裴卿卿原本颯爽的聲音慢慢溫下來。
就這樣,孟桑漸漸閉上雙眼,摟著家阿娘眠。
一夜無夢-
翌日,孟桑是被屋外傳來的竹聲給吵醒的,隨之而來的還有說話聲。
“阿柏,再扔幾個!”
“啊?姑母,真的要這樣喊阿姐起來嘛?”葉柏顯然很猶豫。
“就這麼辦!你這阿姐慣會賴床,要是沒人管,定然要睡到日上三竿才起。這孩子真是,連阿柏你都起來,還能安心睡著,也不怕腦子睡糊涂了!”
“哦……那阿柏聽姑母的。”
話音剛落,又是一陣“噼里啪啦”的聲音響起。
孟桑睡意頓消,笑了,揚聲喊道:“快收了神通吧!吵得耳子疼!”
接著,就聽見裴卿卿笑罵道:“醒了就起來,一家子等你呢!”
孟桑本想再在暖和的被窩里瞇一會兒,怎奈外頭眾人鬧出的靜忒大,最后只能無奈地長嘆一聲,搖著頭起床。
等捯飭完自己,回到正堂坐下時,庭院里的火堆已經熄滅,婢子們各自干著活。有去到外頭大門邊上掛起兩片桃符,有在庖屋準備待會兒所用吃食的,有圍在銀杏樹旁往土里扎竹竿。
竹竿細細長長的,底部扎進土里,頂部掛著一塊長條幡子。寒風獵獵,那長條隨之在空中舞,很是靈巧。這也算是本朝的習俗之一,每年的大年初一,各家都會在庭院里掛起旗子,借此來為全家祈福。1
伴著幡子被風吹的聲響,孟桑一家三口、葉柏與阿蘭在堂中落座,婢子們從前院端來各種吃食。
依照習俗,元日的飯食還有些講究,須得先飲酒,再用正經吃食。而飲酒之事,得從家中年歲最小的飲起,為的就是慶祝家中小郎君、小郎又長大一歲。2
孟桑從婢子手里接過兩壺酒,笑瞇瞇地看向葉柏:“來來來,阿姐給你滿上。”
元日飲的兩種過年酒分為兩種——以各中藥草制的屠蘇酒,以及用花椒、柏葉浸泡的椒柏酒。這兩種可比不得平日席面上的新酒、郎清,喝在口中的滋味很是奇怪。
往年在孟家,孟桑作為家中最小輩,一向是頭一個這苦楚的。今年家里添了葉小郎君,孟桑得以多瀟灑片刻。
是快活了,而葉柏的臉就不好看了。
小郎君面泛苦,可憐兮兮地接過小碗一看里頭得可憐的分量,頓時笑了:“阿姐疼我!”
原來,孟桑上說著滿上,手下還是留了,只倒了些許酒,擺明是“意思一下得了”的態度。
孟桑笑道:“好了,快點喝,都等著祝賀你長大一歲呢。”
猜你喜歡
-
完結386 章

毒舌醫女穿越記
在古代,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是以,欠下賭債的父親要將自己賣了換取錢財,沈淩兒別無他法,隻能一死了之。誰知死人竟有復活日,沈寶善大喜:「既然沒死,趕緊嫁人去!」然而,這柔弱的身體中,已換了個接受現代教育長大的魂魄。什麼三從四德,愚孝夫綱,統統靠邊!憑著一手精湛醫術,金手指一開,沈淩兒脫胎換骨,在古代混得風生水起。誰知,穿越之初撿來的那個男人,竟越看越不簡單。毒舌女對戰腹黑男,誰勝誰敗,尚未可知吶。
101.3萬字8 22668 -
完結20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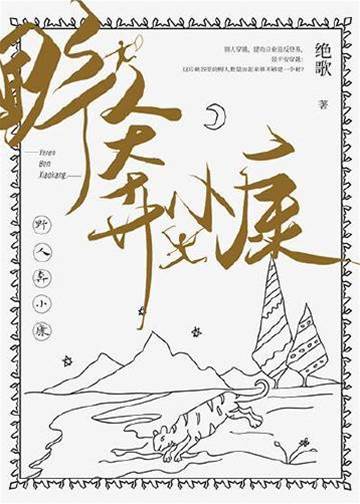
野人奔小康
景平安在職場上辛苦打拼,實現財富自由,卻猝死在慶功宴上,悲催地穿越成剛出生的小野人。有多野?山頂洞人有多野,她就有多野,野人親媽茹毛飲血。鉆木取火,從我開始。別人穿越,建功立業造反登基,景平安穿越:這片峽谷里的野人數量加起來夠不夠建一個村?…
80.8萬字8 5279 -
完結626 章

我,開局輔佐嬴政,成為六國公敵
張赫穿越大秦,獲得最強輔助系統,只要輔助嬴政,便能獲得十連抽。于是張赫踏上了出使六國的道路,咆哮六國朝堂,呵斥韓王,劍指趙王,忽悠楚王,挑撥齊王,設計燕王,陽謀魏王。在張赫的配合下,大秦的鐵騎踏破六國,一統中原。諸子百家痛恨的不是嬴政,六國貴族痛恨的不是嬴政,荊軻刺殺的也不是嬴政。嬴政:“張卿果然是忠誠,一己擔下了所有。”張赫拿出了地球儀:“大王請看……”
122.8萬字8 8438 -
完結293 章
這個將軍是我的
醫學博士洛久雲被坑爹金手指強制綁定,不得不靠占她名義上夫君的便宜來續命。 偷偷給他做個飯,狗狗祟祟盯著人家的手。 魏巡風:這個姦細一定是想放鬆我的警惕! 洛久云:悄悄拉過男人修長的手指,反覆觀看。 看著他矜貴又懵懂容顏,想,他可真好看。 面對時不時被佔便宜的洛久雲,某日魏大佬終於......後來,魏巡風:這女人,真香!
51.4萬字8 926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