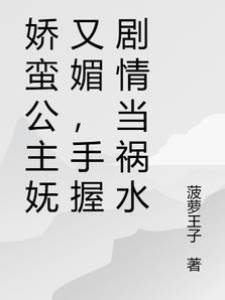《姑母撩人》 第59章 第59章
桃夭凝笑, 塵夢迷離,韞倩躲在屏風后頭,將如何與施兆庵相識相知同花綢細細講來, 說到, 眼波流,笑臉溢彩,仿佛是世間最幸福的人, 仿佛,是蜂蝶簇擁的鮮花。
溫盡, 爛賞天香,花綢靜,也的確似千里隔一株懸崖底開出的花,金谷里蕭蕭過境的風從不曾摧毀,花綢又何堪忍心再添苦雨來敲砸?
終歸只是笑一笑,閉口不提那些風暴, 只是握一握的手, “你高興就行, 我走了, 不妨礙你們兩個幽會。”
“去你的。”韞倩地將嗔一眼,攜手與走出屏風前, 招呼蓮心使丫頭往廚房里裝了好些螃蟹, “帶回去, 替我孝敬姑。我曉得你府上也不缺吃的, 可這螃蟹是盧正元在南邊買賣上的人孝敬來的,京里的到底比不上。”
“多謝你。”花綢招呼椿娘提著食盒,把施兆庵一眼,順口打趣他, “林裁改日也請到我家去替我裁裳啊。”
施兆庵忙訕笑拱手,“姑媽取笑。”
“不是取笑,真格的事呢。”
韞倩見施兆庵有些笑不是不笑不是的尷尬,便推花綢,“你快去吧,吃這麼些還塞不住你的,要你在這里多話!”
等人走了,韞倩便蓮心掣了席,請施兆庵屏風后頭坐。蓮心照常搬了杌凳在門口坐著扎絹花哨探,豎起耳朵一聽,屋里卻是靜靜的。
兩個人眼對著眼脈脈相看一會兒,噗嗤一聲,都笑了,彷如抖落在風里的樹,葉著葉,枝搖著枝。施兆庵還是上回在云林館見的,一別這些日子,早想得牽腸掛肚沒奈何,朝門口瞥一眼,走到榻上來抱。
銀屏上繡著玉蘭,凋敝的花瓣似淋淋的雨,把干燥的空氣洇潤的黏糊。韞倩也似一場綿綿的雨,落在他懷里,從前的一反骨了,生出小兒無限的態,“我不你,你怎的忽然到府里來?”
施兆庵著的耳鬢,歪著臉看,若珍寶地俯下臉來親一親,“我原是在碧喬巷與桓兄弟談事,談完出來,順便往織霞鋪去一趟,看你上回定下的裳做好了沒有。誰知老師傅說這府里有人早上就去請的,他走不開,拖著沒來。我以為是你,就換了裳過來,誰知又不是你。”
“櫻九好端端的,怎麼會你來?”韞倩輕鎖眉心,徐徐把腰端起。
“了我去,倒沒說什麼,就是量段定裳。”施兆庵也暗暗疑心,“不過提了一句,說是看我有些眼。”
“看你眼……怎麼會看你眼呢?”韞倩稍作沉思,倏地眼一錚,“我想起來,當初送我出門,一班婆子丫頭里就有!你們在門口迎親,或許是在那時候見過你。不好,要是想起來,告訴盧正元,可怎麼辦?”
施兆庵見慌了神,忙抱著哄,“別慌別慌,那日場面上糟糟的,就是恍然見過我,也記不住,無非是真有些眼罷了,哪里會想得起?況且說這話時,對我拋眼送波的,沒準兒就是句勾引的話。”
“什麼?!”韞倩愈發急躁,一霎跳起來,“瞎了的心肺,竟敢想你的賬吃!”
施兆庵笑一笑,將拽進懷里,“想我的賬,我卻不想的,急什麼呢?”
韞倩伏在他口,高高剔一眼,“長得跟個小妖似的,連盧正元那麼個老巨猾的也著了的道,你年紀輕輕的,哪有盧正元見的人多,會不想的賬?”
“你既說了,我年紀輕輕的,何苦去想的賬?”施兆庵哼出個笑,十分不恥,“我不喜歡搔首弄姿的,半點不莊重,像窯子里的姑娘,我看著煩還煩不過來呢。”
“你最好真是煩喔!”
他笑一笑,“要不我給你起個毒誓?”說著手朝天舉起來,“倘或我施兆庵對別人有一點半點的,就我天打……”
“算了算了,”韞倩忙捂他的,“哪個要你起那沒頭腦的誓,你是個世家公子,眼界高,我曉得,信你就是了。”
分寸間,四眼一笑,指端的仙花飄出淡香,似一縷波,勾得他心神漾。他握下的手,是溫熱而的,在朝局尖銳冷的今朝,像刀尖上輕紗,將他圍繞。
他把炕桌推開,溫將兜倒,在金瓶圍繞,錦繡包裹的寶榻上,要與歡好。韞倩心懷警惕,朝屏風一,推推他的肩,“有人來怎麼好?”
上涌,沖掉了施兆庵的理智,“蓮心不是在外頭守著麼?不怕。”
意迷里,誰也顧不得了,他胡地親,忽然嫌那些繁脞的裳,怎麼繞來繞去系了那麼多帶子,將像個被人藏匿的寶層層裹起來。而他又繁瑣地將解開,闖別人的境,走。
“別人的”似乎天生有某種魔力,總讓人不余力地狂想,想搶來,想占有。因此他格外賣力,像洶涌的,一浪一浪地拍打,“你想我嗎?”
韞倩只是模模糊糊地覺得,他的吻把全撕碎,把的魂魄也撕做兩半,飄忽不定的腦子里就兩個字,“想你。”
施兆庵饜足地笑笑,俯低來吻,在他濡的底將要破化一群蝴蝶,否則怎麼渾都在抖?真像是一群蝴蝶在振翅,將扇進風波里,不知什麼時候才扯出來。
像,一點點偏離和黯淡,蓮心的耳朵在喧嚷里漸漸平息,在里別的漸漸松開,抬眼一看,見對廊上一個碩的影晃過來。
忙咳嗽兩聲,站起來迎,“老爺回來了?”
“嗯。”
盧正元搖著折扇進去,施兆庵正躬著腰在圓案上量布條,揚著一條長長的木板尺,余一見他,心里有幾分鶻突,面上卻十分鎮靜地埋低了臉,笑嘻嘻打了個拱手,“老爺在家呢?許多時候不見老爺,愈發神了,瞧著竟不像五十上下的年紀,頂多三十五上下。”
馬屁拍得盧正元哈哈大樂,渾的抖起來,也不在意這麼個小人,看也不看他什麼模樣,徑直走到榻上與韞倩說話。施兆庵暗里朝韞倩遞個眼,收拾了家伙事,告退出去。
那盧正元見韞倩玉潤紅姿,似一場春雨剛洗過了桃花,比往日更嫵人,倏然心一,嘻嘻湊過大臉去親一口,“太太今日怎的這樣高興?”
韞倩的好心一霎敗完,面上不得不維持著面,與他笑一笑,“做新裳嘛,自然就高興囖。你從哪里來?”
“剛從外頭回來。”盧正元霪心輒起,挪到這邊榻上摟,“心里想著你呢,舍不得在外頭多呆。”
天暗下來,蓮心趁機進來掌燈,韞倩也趁勢推一推他,“丫頭看著呢,不要拉拉扯扯的,有事說事。”
盧正元一副老骨頭,也不好在丫頭面前失了面,因此端正起來,“要你拿一百兩銀子與我,西邊的鋪子里要進貨,掌柜來請銀子,我上一時沒現銀,只好來你開庫房。”
“曉得了,你去,我晚些丫頭送去櫻九屋里給你。”
“我不去了。”盧正元呵呵笑,兩眼像條狗盯著,直冒,“今晚就歇在你屋里,多久沒給你效力了?今朝留下給你盡盡力。”
韞倩尋著緣由推一陣,誰知盧正元今番是鐵了心要留宿在此,死活推不走。只得咬碎銀牙,咽著一肚子的恨陪著說話。
只等夜完完整整罩將下來,他就迫不及待把渾圓的胳膊重重地在肩上,摟著往臥房里去。
韞倩捱著步子,邊蹭著地,像與油的地磚相互拉扯,遲遲挪,走過的綺窗外,卻有月亮輕盈躍起,懸在枝梢,把錦簇的花瓣照落,轉瞬,一霎秋來。
云乍雨晴,好風下綠庭,天轉了涼,晚來閑暇,又把針線擱下,殘照漸收,黃昏輕到了。
奚緞云枕在榻上發呆,抬眼窗外,見奚甯走進來,在那邊屋里換下補服,穿著草黃的直裰,束著玉白的帶,那帶當中嵌著塊碧綠的翡翠,襯得人容華淡雅,骨骼風流。
地上漉漉的,奚甯眼看著窗戶上的玉人,不留心踩到一朵爛了漿的金花,腳上趔趄一下,險些倒。逗得奚緞云嘻嘻發笑,繞到外間來迎他,“你今朝怎麼這麼早回來?這些時,可都是不到二更不歸家的,可吃過飯沒有?”
“在施家吃過了,幾位大人在那里設宴議事,席散得早,我也就早回來了。”
說是議事,不過是與施尋芳衛珺等人坐在一掐算寧夏的消息。奚甯下了各不利潘懋的案子,單等著寧夏的信,仿佛是一個賭徒,將所有的賭注都下在此,心里難免有些鶻突。
猜你喜歡
-
完結294 章

將軍家的丫頭
褚隨安穿越了,為了生存下去把自己賣了,卻發現主子想讓自己當姨娘,這可不行。因此,褚隨安趁亂跑了……主子爺這下可不依了,滿世界的開始找她。這個將軍家的小丫頭不知不覺間攪起一場大風波,將軍自覺命苦啊,攤上這麼個小丫頭。
56萬字8 67125 -
完結226 章

重生后渣男他弟要娶我
世人皆道她陸寶曦心狠手辣,手段惡毒,卻不知她已然活過凄慘一世,這一世只為復仇而來。 她要毀她一生的長姐身敗名裂,她要活活燒死她的平瑤公主血債血嘗,她要一步一步地,將那些高高在上的敵人拽入地獄狠狠踩踏,哪怕是手染鮮血也在所不惜! 好在漫漫復仇之路,有他一路相伴。 上一世,他救起落水的陸寶曦后從此再也沒有出現,這一世他變成一顆牛皮糖,黏上了陸寶曦就扯不下來。 替她劈荊斬棘,護她一世周全,為她驅散陰霾,開辟出屬于陸寶曦唯一的光明未來。 “寶曦,快開開門讓為我進去,我下次還敢!”
43.7萬字8.18 31945 -
完結482 章
江山為聘
前世,她最好的姐妹為了搶她的丈夫掐死了她的親生骨肉,她的丈夫冷眼旁觀更誣陷她不貞,大年夜,滿城煙花盛放,她卻被鎖在柴房裡活活餓死。 蕭如月發誓:若有來世必要賤人和渣男血債血償! 一朝夢醒,再世為人,她重生為王府任人欺凌的小郡主,翻身成為和親公主,回故土,殺賤人滅渣男。 咦,這個奇怪的君上是怎麼回事?說好的鐵血君王呢?怎麼好像有哪裡不對勁? 腹黑君王,無良毒后,為守住這家國天下安寧,比肩攜手,山河共賞。 此文開頭有點慘烈,但那只是表象,主題是寵寵寵寵寵~~~~~~~~~~本文讀者群:559125962,敲門磚:江山為聘。 歡迎讀者姑娘們入駐。
124.3萬字8 32391 -
完結15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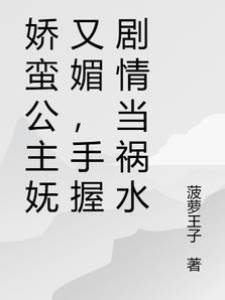
嬌蠻公主嫵又媚,手握劇情當禍水/嬌蠻公主以色爲誘,權臣皆入局
【釣係嬌軟公主+沉穩掌權丞相+甜寵雙潔打臉爽文1v1+全員團寵萬人迷】沈晚姝是上京城中最金枝玉葉的公主,被養在深宮中,嬌弱憐人。一朝覺醒,她發現自己是活在話本中的惡毒公主。不久後皇兄會不顧江山,無法自拔地迷上話本女主,而她不斷針對女主,從而令眾人生厭。皇權更迭,皇兄被奪走帝位,而她也跌入泥沼。一國明珠從此被群狼環伺羞辱,厭惡她的刁蠻歹毒,又垂涎她的容貌。話本中,對她最兇殘的,甚至殺死其他兇獸將她搶回去的,卻是那個一手遮天的丞相,裴應衍。-裴應衍是四大世家掌權之首,上京懼怕又崇拜的存在,王朝興替,把控朝堂,位高權重。夢醒的她勢必不會讓自己重蹈覆轍。卻發覺,話本裏那些暗處伺機的虎狼,以新的方式重新纏上了她。豺狼在前,猛虎在後,江晚姝退無可退,竟又想到了話本劇情。她隻想活命,於是傍上了丞相大腿。但她萬萬沒有想到,她再也沒能逃出他掌心。-冠豔京城的公主從此被一頭猛獸捋回了金窩。後來,眾人看著男人著墨蟒朝服,明明是尊貴的權臣,卻俯身湊近她。眼底有著歇斯底裏的瘋狂,“公主,別看他們,隻看我一人好不好?”如此卑微,甘做裙下臣。隻有江晚姝明白,外人眼裏矜貴的丞相,在床事上是怎樣兇猛放肆。
27.8萬字8 450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