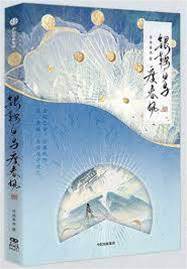《再嫁東宮》 第 59 章
沈瓊先前雖沒打算在宮中留宿,可如今太後發話,也沒有辦法拒絕,隻能乖巧地應道:“是。”
裴明徹則是笑了聲,放下茶盞,不尷不尬地蹭了蹭鼻尖:“您這裏的茶不錯……”
太後眼中的笑意愈濃,虛虛地點了他一下,吩咐嶽嬤嬤道:“讓人給咱們秦王殿下準備些茶葉帶回去,免得連個茶葉都要來蹭長樂宮的,看起來還怪可憐的。”
嶽嬤嬤湊趣道:“好,奴婢記下了。”
在場的眾人並沒傻的,哪怕沒挑明,也都明白這一來一回話中的意思。
樂央心中止不住地冷笑,飛了裴明徹不眼刀子,等到嶽嬤嬤扶著太後到室歇息後,方才忍不住低了聲音道:“你打的什麽主意?”
無論在先前在大慈恩寺別院,還是如今在長樂宮,裴明徹都未曾掩飾過自己對沈瓊的好。
樂央先前是覺著荒唐,可如今知曉當初裴明徹化名秦淮,誆騙沈瓊的舊事後,再見著他這副模樣,就怎麽看怎麽不爽了。
若不是還顧忌著這是長樂宮,樂央怕是都要拍案同他算賬了。
裴明徹裝傻:“姑母這話什麽意思?”
他原是準備揣著明白裝糊塗,然而被沈瓊抬頭淡淡地看了一眼之後,臉上的笑隨即僵住,也沒了科打諢的心思。
“你做得那些混賬事……”樂央才起了個話頭,就被沈瓊輕輕地拉了下袖,製止了。
“秦王殿下想必還有正經事要做,”沈瓊輕聲細語道,“我也想去看看娘親曾經住過的地方,姨母你帶我去好不好?”
樂央心中原本存著氣,可被沈瓊這麽聲一攪,倒是也消散了些。冷哼了聲,懶得再多看裴明徹,站起來帶著沈瓊出了正殿,往曾經住過的偏殿去。
裴明徹卻並沒急著離開,他盯著沈瓊先前坐著的那空位看了會兒,也不知在想些什麽,片刻後將杯中的茶飲盡,方才離了長樂宮。
當初在長樂宮時,樂央是同林棲雁住在一的。帶著沈瓊到了偏殿,輕車路地翻出許多舊來,順勢同沈瓊講起時的趣事來。
沈瓊聽得專心致誌,轉頭就將裴明徹給拋之腦後了。
可樂央卻始終放不下這事,等到宮送了茶來,抬手將隨侍的人都遣了出去,而後向沈瓊道:“姨母還有幾句話,想同你聊一聊。”
沈瓊放下手中的木雕,這是當年林棲雁親自手刻的,看起來栩栩如生的。心中知道樂央想問的是什麽,雖不大想聊,但也知道這事遲早要攤開來講明白,點頭道:“您說。”
“先前我遣人去查過你的世,無意中知曉了秦王與你的舊事……”樂央一提起來這荒唐事,便忍不住歎了口氣,“阿,你如今是如何打算的?”
“我沒什麽打算,”沈瓊如實道,“當年他離開錦城後,我便隻當夫君是過世了,也守了整整三年的孝。如今會在京城重逢,就全是湊巧了。”
沈瓊先前雖沒打算在宮中留宿,可如今太後發話,也沒有辦法拒絕,隻能乖巧地應道:“是。”
裴明徹則是笑了聲,放下茶盞,不尷不尬地蹭了蹭鼻尖:“您這裏的茶不錯……”
太後眼中的笑意愈濃,虛虛地點了他一下,吩咐嶽嬤嬤道:“讓人給咱們秦王殿下準備些茶葉帶回去,免得連個茶葉都要來蹭長樂宮的,看起來還怪可憐的。”
嶽嬤嬤湊趣道:“好,奴婢記下了。”
在場的眾人並沒傻的,哪怕沒挑明,也都明白這一來一回話中的意思。
樂央心中止不住地冷笑,飛了裴明徹不眼刀子,等到嶽嬤嬤扶著太後到室歇息後,方才忍不住低了聲音道:“你打的什麽主意?”
無論在先前在大慈恩寺別院,還是如今在長樂宮,裴明徹都未曾掩飾過自己對沈瓊的好。
樂央先前是覺著荒唐,可如今知曉當初裴明徹化名秦淮,誆騙沈瓊的舊事後,再見著他這副模樣,就怎麽看怎麽不爽了。
若不是還顧忌著這是長樂宮,樂央怕是都要拍案同他算賬了。
裴明徹裝傻:“姑母這話什麽意思?”
他原是準備揣著明白裝糊塗,然而被沈瓊抬頭淡淡地看了一眼之後,臉上的笑隨即僵住,也沒了科打諢的心思。
“你做得那些混賬事……”樂央才起了個話頭,就被沈瓊輕輕地拉了下袖,製止了。
“秦王殿下想必還有正經事要做,”沈瓊輕聲細語道,“我也想去看看娘親曾經住過的地方,姨母你帶我去好不好?”
樂央心中原本存著氣,可被沈瓊這麽聲一攪,倒是也消散了些。冷哼了聲,懶得再多看裴明徹,站起來帶著沈瓊出了正殿,往曾經住過的偏殿去。
裴明徹卻並沒急著離開,他盯著沈瓊先前坐著的那空位看了會兒,也不知在想些什麽,片刻後將杯中的茶飲盡,方才離了長樂宮。
當初在長樂宮時,樂央是同林棲雁住在一的。帶著沈瓊到了偏殿,輕車路地翻出許多舊來,順勢同沈瓊講起時的趣事來。
沈瓊聽得專心致誌,轉頭就將裴明徹給拋之腦後了。
可樂央卻始終放不下這事,等到宮送了茶來,抬手將隨侍的人都遣了出去,而後向沈瓊道:“姨母還有幾句話,想同你聊一聊。”
沈瓊放下手中的木雕,這是當年林棲雁親自手刻的,看起來栩栩如生的。心中知道樂央想問的是什麽,雖不大想聊,但也知道這事遲早要攤開來講明白,點頭道:“您說。”
“先前我遣人去查過你的世,無意中知曉了秦王與你的舊事……”樂央一提起來這荒唐事,便忍不住歎了口氣,“阿,你如今是如何打算的?”
“我沒什麽打算,”沈瓊如實道,“當年他離開錦城後,我便隻當夫君是過世了,也守了整整三年的孝。如今會在京城重逢,就全是湊巧了。”
“我看他對你,倒是舊難忘。”樂央這幾日反複思量過此事,也曾與邊的嬤嬤商議過,“以你如今的份,若是也還對他有意,倒盡可以明正大地嫁過去,將你二人的關係過了明路。”
其實某種意義上來講,這算是很好的選擇。
要知道如今皇上也屬意裴明徹繼任儲君,上趕著想要同他結親的世家多了去了,畢竟這親事若是定下來,後半生的榮華富貴便再不用愁了。
樂央覷著方才太後那個反應,總覺著,對此事應當是樂見其的,應當不會反對。
畢竟這一年來,太後始終在想著給裴明徹張羅親事,幾乎將世家閨秀挑了個遍,可他死活就是不肯鬆口。如今難得見他對哪個姑娘家生出興趣來,還這般主,著實是不易。
但沈瓊卻是搖了搖頭:“我與他的緣分已經盡了,也並沒再續前緣的心思。先前,我已經將自己的意思同他說得明明白白,可他卻……”
頓了頓,沒將後半截話說出口來,隻歎道:“我也不明白他在想些什麽。”
裴明徹是個聰明人,可在這件事上卻顯得格外傻。做著吃力不討好的事,哪怕被數次甩冷臉,都不肯好聚好散。
沈瓊每每想起來,都覺著難以理解。
樂央遲疑道:“你當真無意與他重修舊好?”
樂央雖氣著裴明徹當年的所作所為,但平心而論,也承認他是個一個很討姑娘家喜歡的人——天生一副好相貌,又是有真才實學的,儲君之位唾手可得,平素裏待人事也溫和知禮,幾乎挑不出什麽錯來。
這些加在一起,便足夠姑娘家癡迷的了,若是添上癡心一片做小伏低,想必沒幾個人能忍心回絕。
沈瓊毫不猶豫道:“無意。”
樂央再三確認:“若是將來他另娶他人,你也不在乎嗎?”
沈瓊沉默片刻後,解釋道:“我如今是為著娘親的事,才在京中多留了些時日,但歸結底還是要回南邊去的。屆時秦王殿下是要娶妻也好,納妾也罷,自然是跟我沒什麽幹係,八竿子也打不著的。”
“既然如此,等趕明兒若是太後問起來,我便直接替你給回絕了,不留轉圜的餘地。”樂央端詳著沈瓊的神,“可好?”
倒也不是為裴明徹爭取,但此事幹係重大,並非能意氣用事草率決定的,所以必須得確準沈瓊心中當真是如此想的,而非是姑娘家口是心非才行。
沈瓊垂眼擺弄著手中的木雕,點了點頭:“那就有勞姨母了。”
再三問過後,樂央總算是拿定了主意,不再替裴明徹爭取,而是從心說道:“當年他做的事的確太過混賬,你怨他也是理所應當的。便是我這麽個旁觀的,聽了都覺著生氣。”
沈瓊無聲地笑了笑,並沒有多做解釋,隻隨口附和道:“是啊。”
其實到如今,對裴明徹倒的確說不上怨恨,隻是倦了而已。就好比一麵無意中摔破了的鏡子,雖說也能粘粘補補盡力拚原樣,但卻不想再花費心思了。
但這其中的曲折旁人未必能理解,說了也無用,索隻字不提。到如今,也隻盼著裴明徹能知識趣些,別再在太後麵前多生事端。
太後發話後,沈瓊便在長樂宮中留了下來,就安置在生母曾居住過的偏殿,等過幾日再離宮。
猜你喜歡
-
完結137 章
東宮美人(荔簫)
楚怡穿越成了丞相千金,自問命不錯。第二個月,家就被抄了。第三個月,楚怡以妾侍身份被賜進東宮,-楚怡一看,完犢子,苦難的日子在向她招手。結果觸發的竟然是甜文劇情?
43萬字8 19618 -
完結3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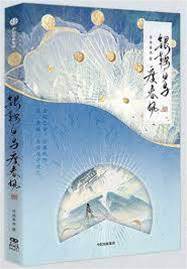
銀鞍白馬度春風
君主剛愎自用,昏庸無能,掩蓋在長安錦繡繁華之下的,是外戚當權,蟻蛀堤穴。 賢仁的太子備受猜忌,腐蠹之輩禍亂朝綱。身爲一國公主,受萬民奉養,亦可濟世救民,也當整頓朝綱。 世人只掃門前雪,我顧他人瓦上霜。這是一個公主奮鬥的故事,也是一羣少年奮鬥的故事。 ** 你該知道,她若掌皇權,與你便再無可能。 我知道。 你就不會,心有不甘嗎? 無妨,待我助她成一世功業,他日史書之上,我們的名字必相去不遠。如此,也算相守了。
55.4萬字8 1879 -
完結156 章

東宮奪歡
崔歲歡是東宮一個微不足道的宮女,為了太子的性命代發修行。她不奢望得到什麼份位,隻希望守護恩人平安一世。豈料,二皇子突然闖入清淨的佛堂,將她推入深淵。一夜合歡,清白既失,她染上了情毒,也失去了守望那個人的資格。每到七日毒發之時,那可惡的賊人就把她壓在身下,肆意掠奪。“到底是我好,還是太子好?”
28.1萬字8.18 7500 -
完結258 章

燈花笑
陸瞳上山學醫七年,歸鄉後發現物是人非。 長姐為人所害,香消玉殞, 兄長身陷囹圄,含冤九泉; 老父上京鳴冤,路遇水禍, 母親一夜瘋癲,焚於火中。 陸瞳收拾收拾醫箱,殺上京洲。 欠債還錢,殺人償命! 若無判官,我為閻羅! * 京中世宦家族接連出事, 殿前司指揮使裴雲暎暗中調查此事, 仁心醫館的醫女成了他的懷疑物件。 不過...... 沒等他找到證據, 那姑娘先對他動手了。 * 瘋批醫女x心機指揮使,日
96萬字8.33 646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