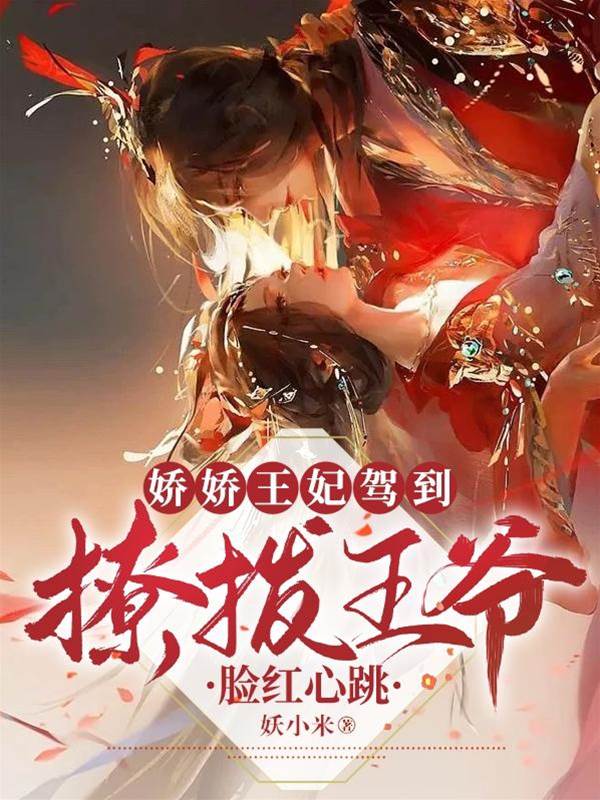《權傾裙下》 第11章 露餡
承恩殿中,已是另一番暗流洶湧。
「柳姬在說什麼,孤怎的聽不明白了?」
趙嫣面不改,出太子招牌的笑來。
「一個人想要迴避問題時,往往會拋出另一個問題來掩飾。不答反問,這樣的人要麼就是被說中要害了,要麼就是心虛有鬼。」
柳姬單手搭在案幾上,道:「你不必擔心我在使計詐你,沒有十的把握,我也沒膽破這層窗戶紙。」
於是,趙嫣眸中秋水般的笑意便淺了些。
肅王夜訪,無意將柳姬捲,早料到會有這般結果。
「但相貌如此相似的人並不好找,就連替太子死的『影子』,模樣段也做不到如你這般神似,非脈相連之人不能勝任。」
說著,柳姬稍稍前傾子,「我猜,你來自東南方千里地外。」
東南方,距京一千里,正是華行宮的位置。
趙嫣不聲不語,眸中燭跳。
還是低估了兄長同寢共枕的邊人,其敏銳聰慧,遠超常人。
將全部力放在了對付肅王上,未曾想會在一個不起眼的姬妾上栽跟頭……
不,柳姬真的只是困居後院的金雀嗎?
趙嫣僅是片刻的沉思,便做出了決定。對方既已亮出「兵刃」,也沒必要遮掩。
柳姬雖咄咄人,卻並無半點敵意。真正可怕的,是聞人藺那般笑相對,卻袖裏藏刀的狠之人。
如此想著,反倒輕鬆起來,抬手放下支撐窗扇的紅漆叉桿。
窗扇落下,在瑟瑟朔風中隔出一片的靜謐天地。
外頭的流螢聽到靜回頭,只見柳姬與太子的影子相對而坐,影影綽綽,聽不清在說些什麼。
躊躇片刻,到底沒進去打擾。
殿中,靜聞落針。
趙嫣將紅漆叉桿橫擱在膝上,面上的怯懦消散不見,隨之變得輕懶倦起來。
柳姬的話不可小覷,既然能看出端倪,說不定旁人也能看出,須得弄清楚在哪。
「我不明白,是哪裏了餡。」
趙嫣仔細回想,反思道,「是我對你的態度不夠熱忱,還是在床榻時暴了什麼?」
柳姬笑了。
「殿下放心,你裝扮得很好,若是旁人定看不出端倪。我之所以能瞧出不同,不過是僥倖得益於……我曾與太子殿下私下約定的一個。」
柳姬端起流螢送來的酒壺,大方地給自己斟了一杯酒,「這個連流螢都不知道,遑論你這個贗品。」
趙嫣凝神:「什麼?」
既是,柳姬怎肯輕易吐?
「其實自歸途中,我便猜到了是這般結局。」
柳姬一聲冷嗤,說不出是怒是嘲,握酒盞自語道,「我早說過,趙衍遲早會把他自己作死。」
說罷,像是做出了什麼決定般,當著趙嫣的面端起酒水,仰頭要飲。
趙嫣一把攥住了的腕子。
酒水晃濺出,倒映著柳姬那雙驚詫的眸。
「什麼『結局』,什麼『作死』?」
趙嫣抿,口起伏道,「柳姬,你到底知道些什麼?」
片刻的死寂。
傾倒的酒水沿著案幾邊沿淅淅瀝瀝淌下,在織花席毯上洇出暗的水痕。
空氣中氤氳著濃重的酒氣,仔細聞來,還能品出一難以察覺的苦味。
趙嫣抓著柳姬的指節不自覺用力,沉靜道:「太子是不是遭遇過什麼?告訴我。」
柳姬神複雜,只道:「殿下應該,讓我飲下這杯酒的。」
趙嫣加重語氣:「告訴我!」
面前的小殿下與太子一般纖細無二,看似瘦弱,可那雙漂亮的桃花眸出的是與太子截然不同的倔強堅忍。
柳姬眸幾番變化,終是別過頭,將手從趙嫣掌中離。
「我與太子的關係,並非你們所想的那般。」
道,「我與他打賭輸了,所以踐諾跟在他邊。他給我提供庇護之,我為他排憂解難,實在要說,更像是各取所需的關係。」
這倒像趙衍的作風。
阿兄看上去懦弱無能,卻有樣令人嫉妒不已的本事。無論他玩何種博戲,逢賭必贏。
每每見對方輸的慘烈,還要聲謙和地說上一句:「承讓了。」
趙嫣在他手中輸過不回,氣急了就耍賴皮,罵他欺負人。趙衍只是眼睛彎彎地著,寵溺笑笑,明明是蒼白脆弱的笑容,卻如春風和煦溫暖無比。
現在想想,這段飛狗跳的記憶,已是九歲之前有的甜了。
趙嫣從思緒中離:「所以,你佯做與流螢爭風吃醋,是從那時候就開始懷疑我了?」
柳姬默認,繼續敘說:「去避暑山莊時,他尋了個拙劣的借口將我支走,我雖略有懷疑,卻並未深思。直至後來聽到了一些關於東宮閉門的流言,我心中不安更甚,匆匆理完瑣事歸來,卻發現東宮侍從守衛全換了陌生面孔,方坐實猜想。」
「僅是如此?」
趙嫣將信將疑,直取重點,「你與太子約定之事,到底是什麼?」
柳姬看了趙嫣許久,忽的一笑:「我誆你的。不這樣說,你怎會替我擋下皇后的毒酒?」
趙嫣也笑了,篤定道:「你這句話,才是在誆我。」
聞言,柳姬笑意一頓,玩世不恭的眼神里多了幾分認真。
「你方才,是真的想飲下鴆酒吧?」
趙嫣擰眉,「你與趙衍到底藏了什麼,才會做好赴死的決心?」
「既是,我為何要告訴你?」
柳姬抬臂搭在支棱起的膝頭,自嘲道,「左右活不過今晚了,不將帶到墳墓里去,皇后如何放得下心?」
趙嫣知道不會說出全部實,聰明之人必不會一把擲出所有籌碼,總得留張底牌傍。
「你不會死的。」趙嫣道。
不僅不會死,還得好生護著,一切與兄長死前無異。
眼眸澄澈,僅是一瞬的思索便做出抉擇:「我用得上你。」
「你?」
柳姬上下打量了一眼,不信任之溢於言表。
連太子趙衍都無法做到的事,一個危如朝的贗品,憑甚說此大話?
趙嫣並不過多解釋,凝神片刻,向一旁書案上的棋盤道:「左相李大人教太子的那招燕尾陣,你可會?」
「啊?」
話題轉變突然,柳姬一怔,下意識點點頭。
……
長夜將明,黛藍的天際浮現出一弧微白。
燭花墜落,發出嗶剝的細響,伏在案上的趙嫣猛然驚醒,惺忪道:「我想到了。」
手中的棋子重重按在棋盤,激起一聲清脆的玉石之音。
大剌剌仰躺在榻上酣睡的柳姬一哆嗦,睜開眼起,詫異道:「你不會在此打了一晚上的棋譜吧?」
趙嫣滿意地審視棋局,但笑不語。
抻了抻酸麻的肩背,藍白的映在窗戶紙上,將纖細的形鍍暗的剪影,一時分不清是位秀氣的年還是位落落大方的。
想起什麼要事,趙嫣肩的作一頓,暗道了聲糟糕。
匆匆整理袍起,因伏案而眠的渾酸痛而皺眉吸氣,朝殿門走了幾步,又折回來,朝著支坐在榻上的柳姬攏袖一躬。
「多謝你替我保守,還有,謝謝你教的棋。」
直起,眼睛在混沌的晦暗中顯得格外明亮,「我會竭盡所能保下你。」
就像阿兄待一樣。
說罷來不及審視柳姬是何神,微微一笑,推門走那片晦暗的清寒中。
柳姬起下榻,行至窗邊,歪著腦袋看滿盤錯的黑白棋子。
最後一手白子下得極妙,燕尾陣形,如金蛟利剪刺破黑子的圍剿,反敗為勝。
一縷纖薄的晨曦自窗中灑,照在那顆收白子上,折出耀眼的芒。
柳姬抬指輕那顆熠熠發的子,閉目喃喃:「我終究是來晚了一步,趙衍。」
趙嫣出了院,果見寢殿前立著坤寧宮的。
李浮躬立侍,一臉言又止的焦灼。
趙嫣心下咯噔,加快步伐上了臺階,推開寢殿大門。
殿燭火通明,魏皇后一襲袍端坐在的寢榻上,旁邊跪著發白的流螢。
殿門再次在後關攏,趙嫣向前行了個男子禮,定神道:「兒臣給母后請安。這個時辰風寒霜重,母後來此,怎的不差人通傳一聲。」
刻意仿著趙衍的神姿態說話,這點小心機瞞不過魏皇后的眼睛。
但這次魏皇后並未心,面不改道:「你還知道回來,太子?」
那聲「太子」啞忍帶怒,是在提醒趙嫣如今的份。
「倒掉鴆酒是我一人的決定,一人擔責,與流螢無關。」
趙嫣看向流螢,低聲道,「你為太子宮婢,聽從太子號令何錯之有?起來。」
流螢跪著沒,朝主子輕輕搖頭。
趙嫣線一抿,索袍在邊跪下。
「柳姬已經看穿我的真實份。」
未等震愕的皇后與流螢回神,話鋒一轉,輕而堅定道,「但母后,我想留下柳姬。」
魏皇后眸嚴厲,問:「你知不知道你在說什麼?眼下局勢本就如履春冰,留下此人後患無窮!」
猜你喜歡
-
完結1055 章

侯府小啞女
燕云歌自末世而來,重生侯府,她給自己定了個小目標:每天吃好喝好樂無憂!然而……她爹一門心思造反,她哥一門心思造反,她嫁個男人,還是一門心思造反。燕云歌掀桌子,這日子沒發過了!
272.1萬字8 16624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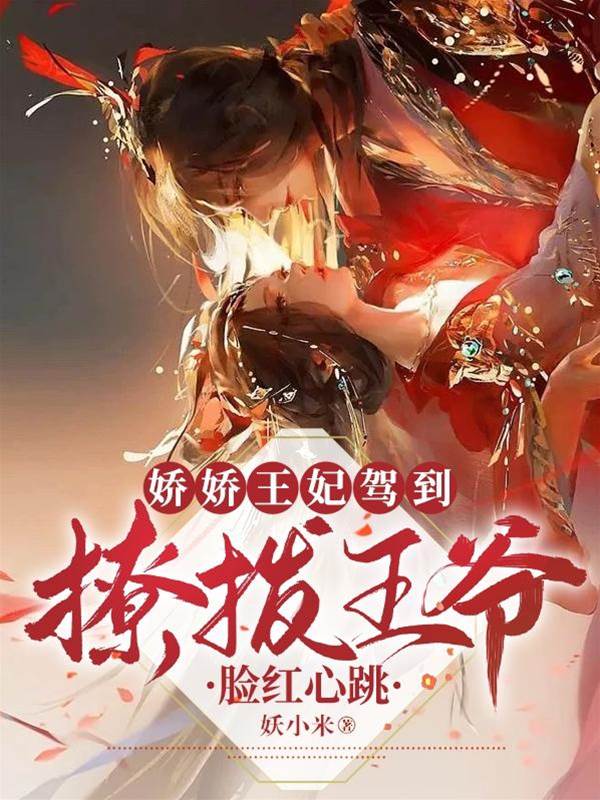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 100859 -
完結372 章

穿成短命白月光后,和反派HE了
桑遠遠穿進一本古早玄幻虐戀小說裏,成了男主那個紅顏薄命的早逝白月光。男主愛她,男配們也愛她。女主因爲長了一張酷似她的臉,被衆男又愛又虐又踩,傷身又傷心。和男主的感情更是波折重重狗血不斷,虐得死去活來,結局還能幸福HE。桑遠遠:“不好意思本人一不想死二受不得虐,所以我選擇跟反派走。打擾,告辭。”反派長眸微眯,姿態慵懶,脣角笑意如春風般和煦——“我的身邊……可是地獄呢。”她沉思三秒。“地獄有土嗎?”“……有腐地。”“有水嗎?”“……只有血。”他想看她驚惶失措,想等她尖叫逃離,不料女子呆滯三秒之後,雙眼竟然隱隱放光——“正好試試新品種!”“……”他在最深沉的黑暗中苟延殘喘,從來也沒想到,竟有一個人,能把花草種滿一片荒蕪。
57.1萬字7.92 9525 -
完結313 章
亡國后成了反賊的寵婢
姜嶠女扮男裝當了幾年暴君。叛軍攻入皇城時,她麻溜地收拾行李,縱火死遁,可陰差陽錯,她竟被當成樂伎,獻給了叛軍首領霍奚舟。姜嶠捂緊馬甲,計劃著再次逃跑。誰料傳聞中陰煞狠厲、不近女色的霍大將軍竟為她破了例。紅燭帳暖,男人摩挲著她眼角的淚痣,眸色暗沉,微有醉意,“今夜留下。”*姜嶠知道,霍奚舟待她特殊,只是因為她那雙眼睛肖似故人。無妨,他拿她當替身,她利用他逃命。兩人各有所圖,也是樁不虧的買賣。直到霍奚舟看她的眼神越來越深情,還鄭重其事地為允諾要娶她為妻,姜嶠才意識到,自己好像是在作繭自縛——
49.2萬字8 685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