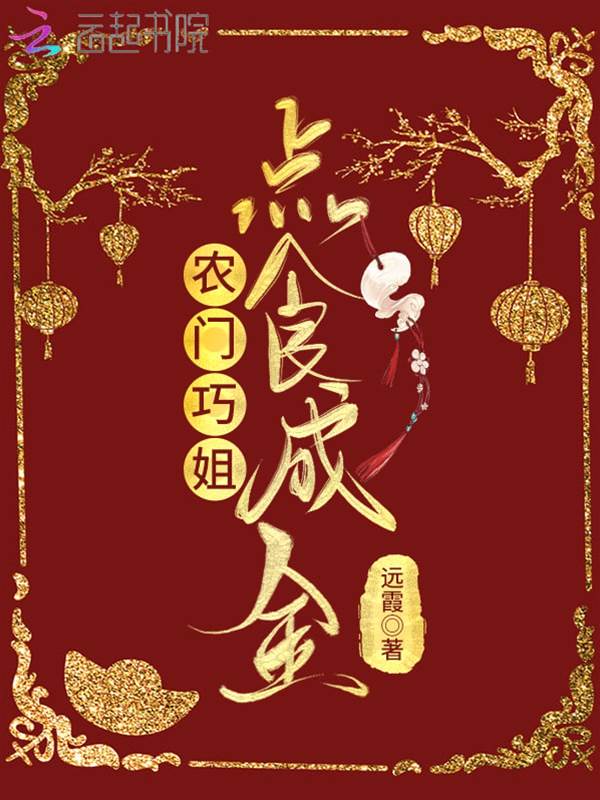《締婚》 第111章 第 111 章
「你可以只當我是你的手足,可我不能。」
發啞的聲音被風旋起,不斷地席捲在沈寧耳邊。
從來都沒有聽他說過這樣的話,有些腦袋發懵,可又有那麼一瞬間,好似到了這話里真正的含義。
紛雜散的思緒立時如同飛絮一般將攏住。
不住抬眼看住他的眼睛,漆黑的眼瞳里,彷彿有暗流涌,又似漩渦吸引。
一時間有些怔怔,沒有言語。
他卻瞧著這般神,低頭輕輕笑了一聲。
他說算了,「不懂就算了。」
此時船尾的江面旋起一陣強風,那風卷到畫案的畫布上面,直把本就一角飛起的畫布完全卷了起來,徑直往江里捲去。
項寓一步上前將飛起的畫布拉了回來,看了一眼一旁還在發獃的人,替將畫布鋪回到了畫案上,又從懷中取出一隻墨玉鎮紙。
同樣是墨玉,卻同傅源還沒送出手的那隻全然不同,上面雕著「安寧如意」四字的紋樣,也不知是何時備下的,就這樣穩穩噹噹地在了畫布上,下了肆而來的風。
似是續起方才的那句,項寓餘輕輕從上掠過。
「還是畫畫吧。」
說完,他轉頭離開了。
直到他影消失在船艙門口,姑娘才回過了神來。
他說得那句,「你可以只當我是你的手足,可我不能」,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沈寧說不清,可莫名地又被紛雜的思緒所攏,心跳快了幾分,哪怕是畫布又重新鋪在了畫案上,也沉不下心來了。
如此這般,乾脆不要畫了,可收拾起畫案的時候,卻看到了那塊墨玉鎮紙。
那鎮紙表面還殘留些許溫熱,彷彿逗留著那人的溫似得。
可他把這鎮紙在的畫布上又是何意,若是贈與又不明說,要說不是又這樣留了下來這就像他方才說了那樣的話,又道「不懂就算了,還是畫畫吧」一樣。
沈寧突然就有些生氣了,想找他,讓他把話說清楚,但莫名腳下沒敢,有種說不清的不敢直面的緒悄然蔓延。
心跳又快了些許,糟糟地胡跳著,亦顧不得這些畫布了,了丫鬟收拾,自己抓了那名不正言不順的墨玉鎮紙,悶頭就回了自己的艙室,關起了門來。
沈寧一上晌都沒有出艙門,傅源也沒瞧見姑娘坐在船尾畫畫,別說想要送些件,便是連見一面都見不到了,心裡空落落的。
他略有表現,方家姐妹就笑話他,他直接一頭扎進項寓的房裡不出來了。
他唉聲嘆氣地坐到了項寓的床邊,憂鬱地看著外面的江景,偶有一兩尾江魚躍水面,他亦無於衷。
「完了,半日而已,我就得了相思病了。」
項寓沒理會他,只不屑的哼了一聲,低頭擺弄一盤圍棋,偏傅源又問了一句。
「你說寧姑娘為什麼不出門了啊?是不自在了嗎?」
不自在
項寓指尖微頓,指間執的一顆白字磕了一下棋盤,重複了一遍那詞。
「不自在?」
若是像說的那樣,只是面對自己的手足兄弟,會不自在嗎?
項寓手下的棋子不了。
傅源卻提出了另一個問題。
「是不是因為你不自在啊?」
他問了,項寓倒也沒有否認,只是思緒不知飄飛到了何似得。
只不過在傅源看來,這一路還長著,他自然不會真的趕好友下船,但眾人若是的不自在了,便也不好了。
於是他一拍腦門,決定了,晚間吃飯,要正經介紹大家認識認識,相互之間了解了解。
這樣,他也能見到寧姑娘了
傅源學問不怎樣,但是走南闖北這麼多年,辦事還是利落的,當下就離了項寓,同方氏姐妹商議,又請方氏姐妹一定要將沈寧也一道請過來。
方氏姐妹最是熱鬧,當下聽著傅源還準備置辦一場烤魚宴,當即與他冰釋前嫌,一口應了下來。
傍晚時分,夕照日頭墜在沿江西面一無際的原野邊緣,將落未落。
天邊雲霞伴飛,半空彎月微明。
傅源了船上的廚子將魚兒烤至半,便親自上場在船尾的開闊地帶烤制起來。
方氏姐妹一左一右拉著沈寧,循著香氣就過來了。
們剛到,項寓和沈黎之也聯袂而來。
眾人相互見禮,沈寧飛快地看了項寓一眼,見他正同沈黎之說著來年春闈的事,並沒有在意自己,不知怎麼,心頭就同天邊緩緩墜落下去的夕一樣,暗了些許。
垂眸坐在竹桌邊不說話了。
方氏姐妹沒有在船上烤魚吃的經歷,當下見著這煙熏火燎的架勢,反倒覺得稀奇,前後圍著傅源嘰里咕嚕地問了許多問題,接著也跟著傅源撿了兩條小魚,試著烤了起來。
傅源這邊教過方氏姐妹,這邊就了沈寧一聲。
他不敢看,只是半側著臉輕輕一聲。
「寧姑娘,要不你也來試試?頗有些野趣兒。」
只是在他這話說著的時候,項寓也同沈黎之結束了對話,走到了烤架旁邊。
他還是沒有看,沈寧自也不會湊到他前,乾脆婉拒了傅源。
「我給大家沏茶吧。」
這麼說,沈黎之便道自己有好茶,要打發僕從去拿來,又怕僕從找不到,便親自去了一趟。
沈寧一時沒了事做,就又坐回到了竹桌邊。
新鮮又的江魚此刻被木炭火星催出難以言喻的香氣,便是素來胃口不濟的沈寧,此刻也有些被味所,不由往烤架看了一眼。
正此時,有人遞了一條魚過來。
那是一條正冒著香氣的剛烤好的鯽魚,魚焦黃,劃開的皮間還有嗞嗞冒著小泡的鮮香水。
只是姑娘抬頭看去,看到了遞過來烤魚的那人。
是項寓。
但他方才不是本就不理會嗎?
而且清晨那會,他還說「不懂就算了,還是畫畫吧」這樣「輕蔑」的話。
沈寧也說不清那算不算「輕蔑」,但就是因他不高興了。
道,「我不吃鯽魚。」
這話著實有些生,若是傅源他們聽見了,恐要驚訝,順知禮的寧姑娘也能說出這樣的話來?
好在沒有旁人聽見,沈寧說完這話,只看了項寓一眼。
項寓微頓,目上揚落在白皙小巧的下上,似乎想要繼續向上看到的眼睛里,卻還是停了下來。
「看來江南的鯽魚不好吃,這條是江北的鯽魚,約莫還是你喜歡的口味,不若嘗嘗?」
他說這話的時候,神沒有半分波,只是夕照的金日側打在他走線利落的鼻樑上,和了他的面容,為他籠上溫又富有耐心的神。
確實,沈寧從沒有不喜吃鯽魚,甚至在時的困頓年月里,還對的鯽魚有種特殊的嚮往。
可惜那時候,他們吃不起上等的鯽魚。
病臥在床榻上,看到姐姐的辛苦,一點都捨不得再開口奢求更多。
可他卻好似能讀到心裡的每一句話,當天不知去了何,晚間回來的時候,拎了一尾鯽魚回來。
姐姐驚訝不已,問他從哪兒來的。
彼時,亦從床上強撐著坐了起來,向他看去。
可他只是笑著,目不經意似得從臉上掠過,「是我饞了,借了鄰家的船跑去江上釣魚了。」
姐姐自也沒有多說什麼,將那條魚燉的湯發白,而他將魚小塊小塊地拆了,自己只留了很的兩塊,其餘都分到了和姐姐的盤中。
思及此,沈寧眼眶一熱。
這些事,在時里離得越遠,記得越清楚。
那時候的苦都不記得了,偏偏有關他的這些小事,三年間總是浮現在腦海里。
不知為何,也想讓自己不要再多想,畢竟他都向前看,把那些過去放下拋掉了。
可他既然我忘了,又說這樣的話做什麼?
沈寧微微側過了頭去,不再看他一眼。
「我不喜歡吃鯽魚,江南江北的都一樣。」
這話更了。
話音落地,周遭就靜了下來,氣氛凝滯了似得。
不風的悶窒氣氛里,他聲音極輕地問了一句。
「姑娘真不喜歡?」
「真不喜歡。」沈寧綳著一張小臉。
但這麼說了,又稍心虛地從眼角看了他一眼。
夕照的日頭越發墜落進了地平線,照在他臉上的金亦淡了下去。
「哦。」
他只道了一個音,將遞過來無人問津的鯽魚收了回去。
他真收回去了沈寧忽的心慌了一下。
恰此時,傅源拿著一條剛考好的、如他的臉一樣大的鯉魚小跑過來,匆促拿起盤子,啪嘰一下放了過去。
他徑直就要把那裝了鯉魚的盤子往沈寧臉前推,但推到一半又怯了一下,住了手。
傅源清了一下嗓子,「寧姑娘了吧?嘗嘗這大鯉魚?」
隨著他的話音,項寓亦目落了過來,但他什麼都沒說,就那麼靜靜立在那兒。
沈寧在兩雙目的注視下,手下微,不好意思地看了傅源一眼。
「多謝傅六爺,我想先嘗嘗那條鯽魚。」
說完,發現有人瞧了一眼。
猜你喜歡
-
完結1403 章

空間農女:家有悍妻來旺夫
啥?被個收音機砸穿越了?還好上天有眼,給她一個神奇空間!啥?沒爹沒孃還窮的吃不上飯?想啥呢,擼起袖子就是乾!養家,賺錢,虐渣,鬥極品,順便收了同為“後來者”的..
250.7萬字8.18 186328 -
完結4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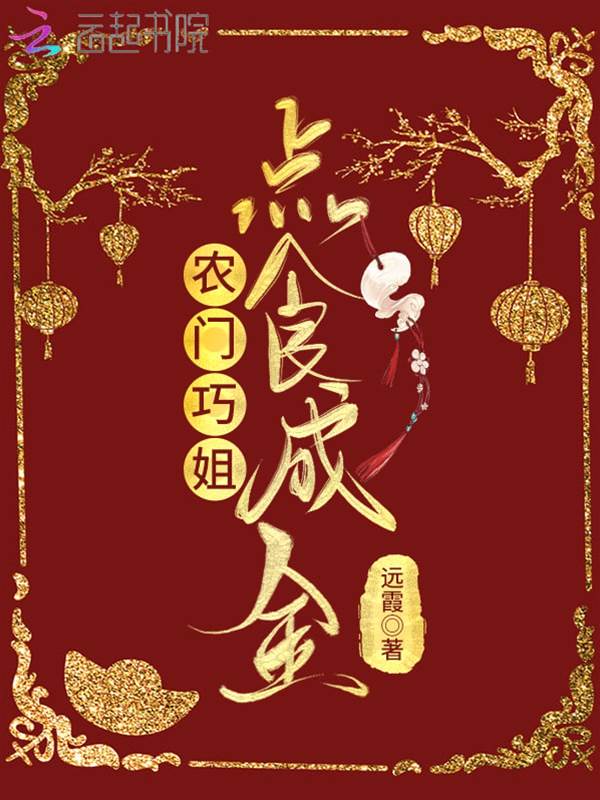
農門巧姐點食成金
高級點心師意外穿成13歲彪悍小農女-包蓉。後奶惡毒,親爺成了後爺。,爹娘軟弱可欺,弟弟幼小,包蓉擼起袖子,極品欺上門,一個字:虐!家裏窮,一個字:幹!爹娘軟弱慢慢調教,終有一天會變肉餡大包,弟弟聰明,那就好好讀書考科舉,以後給姐當靠山,至於經常帶著禮物上門的貴公子,嗯,這條粗大腿當然得抱緊了,她想要把事業做強做大,沒有靠山可不行,沒有銀子,她有做點心的手藝,無論是粗糧、雜糧、還是精糧,隻要經過她的手,那就都是寶。從此,包蓉銀子、鋪子全都有,外加一個自己送上門的親王夫君,氣得後奶一概極品直跳腳,卻拿她無可奈何。
77.6萬字8 342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