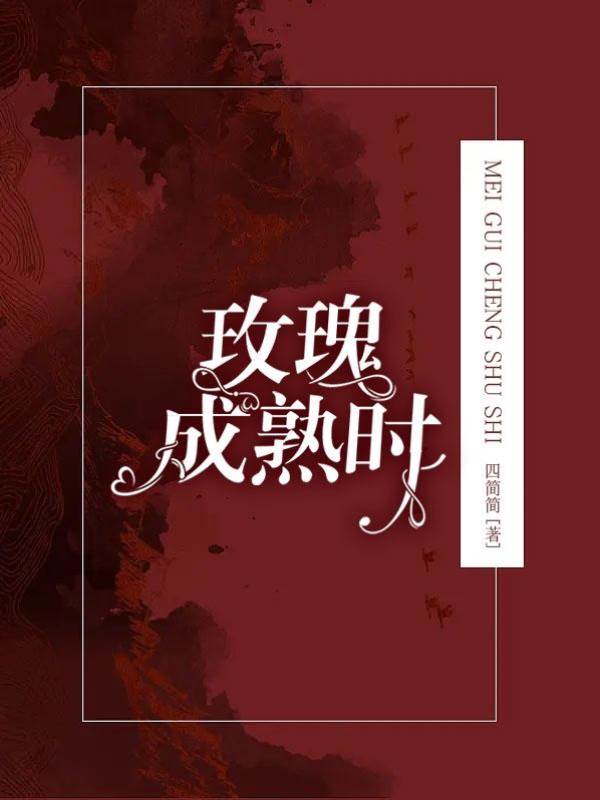《非分之想》 第31章 31.
直徑接近五米的圓形湯池,淡白熱霧飄搖籠罩,染睫凝水珠,模糊遮擋住視線,辨不清是淚意,還是被濺起的池水。
浴胡堆放在岸邊,當做臨時的枕頭,長發在上面鋪開,襯得臉頰和纖長頸項白如細釉,皮深又在一波波地湧出紅。
姜時念迷酒抬眼,隔著氤氳看他。
沈延非雖然人在池中,襯衫竟然還完整,只挽了幾下袖口,但波瀾四起的水面下,他在強勢地咄咄人。
有的人,居然一邊溫有致,楚楚冠,一邊又讓人潰不軍。
然而細碎嗚咽時,他竟還沒有真正開始。
他的耐心在此刻用到極致,寵溺再折磨,池水本就滾熱流,撥人神經,偏偏他溫更威脅,讓在全然接之前,非要先為池中再添一點水源。
電視新聞節目里姜主持人的聲調太過正經,鮮明對比著此刻。
被換到暗的床上,過床尾擺的那束純白梔子花。
屋頂有一遮板沒有拉起來,玻璃外還著暗藍夜幕上的星。
姜時念睫錯落間,只看到面前人勾外翹的一雙深邃眼睛,比窗外繁星更盛,底濃黑,折出的灼眼,扎進心裏,翻攪出無邊熱意。
世界忽然就極速收,周圍事都可以忽略不計,到只剩下一對近在咫尺的幽沉黑瞳,眼睜睜看它們在夜里清醒地野火燎原,燒掉理智。
姜時念昏昏沉沉想,怎麼這樣,這種時候多看他兩眼,都要溺斃,他又怎麼這樣,不說話也蠱人,明知後果,還害人衝地想不顧。
可跟他之間總是不公平的,都這麼凌,他還沒有徹底荒唐。
外面門鈴好像響了,對講屏幕自亮起來,溫泉酒店工作人員的聲音夾著外面的微風,恭恭敬敬大概說著過來送餐的話。
姜時念以為沈延非會暫停,時間都好像靜止了一瞬,深陷海水,怕他再一次冷靜地離開,又半途中止,淚眼朦朧地去挽他後頸,主抬頭吻他。
然後才知道。
是天真了。
沈延非本沒打算走,他的那些狂熱和瘋,是掩在薄冰之下的,一旦掀起,就再也沒有退卻的餘地。
床邊藏著的長方盒子被攥得變形,包裝撕扯開邊角。
姜時念手指用力抓著,被沈延非握住十指纏相扣,抬起來過頭頂。
「害怕嗎。」
姜時念聽到他問。
點頭又搖頭,半睜的瞳仁瀲灧河。
姜時念紅的耳朵要被他鼻息燙破,他沉沉要求:「不能後悔。」
這次搖頭又點頭。
搖頭是不後悔。
點頭是我承諾,我答應你,不管以後如何,不管心在哪裏,這場婚姻真假都沒關係,至你是熱的,能的,這一刻我甘願沉淪,只要當下,不問未來。
溫度計的水銀柱飆到最高,碩大氣球被鼓到極致,煙花點燃火四溢的引線,天穹流星帶著耀目金芒,在這一刻同時開。
深山峽谷珍稀的水源無聲過枝葉植被,溪流汩汩,船艦已經多次途徑,都不忍心急躁,但如今高大船火源四起,邊緣不能再拯救,終於調轉方向,明知自超出了,仍碾過潺潺,不再遲疑。
誰在戰慄,眼淚怔怔地懸住,又從灼熱眼角里出,嗚咽聲碎裂,被吻著吞下。
「穗穗,松一點……」
姜穗穗無可依,像在海里飄搖,他不容分說地掠取,又把筋絡搏的脖頸虔誠地給獻上,把脈付。
迷濛著張口咬住他頸側,齒間都是淚水咸,印在以前咬過的那個淋淋牙印上。
枕頭扯皺,大口呼吸也還是無濟於事,斷續嗚咽聲悶在嚨里,被他俯抱,在心臟震的前,整個人被融進臂彎里,手忍不住抬高環上他,被完全拖進漩渦。
樓下客廳的古董掛鐘嘀嗒搖擺,等姜時念被抱起洗澡,裹進被子時,餘掠過床頭兩個拆封的方塊,還有更多倒出來的,被他剋制暫緩。
離最初已經不知道過去多久了,酸得眼簾快要抬不起來,鼻尖哭出來的紅一直退不掉,只是後來自己都分不清,究竟是因為最初短暫的疼怕,還是後來激漫長的失魂。
上又被穿起簡單的新浴,沈延非把放回湯池,讓放鬆靠穩。
在飄熱泉里吸了吸鼻尖,筋骨舒展開了一些,剛想說喝,就被餵了水,喝了幾口仍然不夠,下意識微微張口,還需要。
沈延非盯著,捧臉深吻,慢聲低喃:「流的太多了,我再去拿。」
姜時念聽完一秒頭昏,想直接鑽進池裏不要面算了。
餘看到不遠,床單已經被他掀開撤下,疊好放進角落,上面的況大概有數,偶爾摻一點紅,大多明片,到底下床墊上,要是被別人看見,真不如一頭撞死,幸好是他親手整理。
沈延非再回來時,端了剛換的晚餐,姜時念這才看到時間,竟然都快零點了,過去了這麼久,投影屏幕上的電視節目都已經換到了深夜檔。
他筆直長邁進湯池,把摟過來,飯菜放到圓形托盤上飄在水面,溫啞地哄著說:「太晚了,吃油膩的容易不舒服,給你換了點清口的。」
姜時念手臂發酸,忍不住犯懶,即使,也吃了兩口就放下了,被他接過來繼續喂,搖頭說不吃了,他語氣微微沉:「太了。」
他給人的迫是骨子裏自生的,即便此刻仍然如此,姜時念眨了眨的眼睫,含著鼻音,乖乖要聽話,他見不得這樣表,又收回去,緩緩覆上,吻過去,引著願意再吃些。
吃到最後水中的托盤開始礙事,被青筋凸顯的手隨意端走,在熱水裏盪開,翻爬在池邊,埋頭咬著手臂面紅耳赤。
夜徹底深了,沈延非把姜時念抱到樓上主臥整潔的床上,掀被子把蓋好,自然地側過去,他躺在後,把圈進手臂中間,嚴合,不能分割。
姜時念迷迷糊糊背對他,他撥開長發,輕吻後頸骨節。
早就睡得很沉,有時不自覺一下鼻音,著累的輕綿委屈。
沈延非抱得更用力。
在夢裏含糊抗議,不過氣地想掙扎,被他攬著轉了個,面對面摟。
今天之前,他不知道自己會對這事熱衷上癮,以前高中,他不敢的心面對,分開這些年,他自己料理的次數都很有限,除了想的時候,本不會,更不可能被這些控制挾持。YushuGu.COm
結婚以後,雖然親昵接有過不止一次了,但因為在步步導,習慣抑自需求,也就以為他可以控制。
或許本來是可以的,但真的婉轉在懷裏,他沒有那麼高潔克制的神,做不到自抑。
什麼都可以拋開,想為瘋魔,做盡一切,烙他痕跡。
好像只有這件事,能整夜地證明,這不是大夢一場,他在真實地擁有。
沈延非幾乎沒合眼,天亮時姜時念睡得正穩,他手機震了震,被他及時扣下。
他作輕緩地起,又親了親頭髮,給掖好被角,床頭桌放了水,才掀被下床,隨手披上服,擰開主臥門下樓。
一樓門口的電子屏幕上有留言提醒,沈延非不用看,直接開門拿進放在門外置籃里的紙盒,掀開掃了眼藥名和詳細說明,又蓋上放到茶幾邊,隨後轉走到另一個方向。
客廳左側是湯池,右側一個通道過去,通過一扇法式角門,裏面是間獨立的活室,兼備影院和小型靶場的功能,跟別墅裏面連通也獨立,可以從客廳進,也可以單獨從外面的側門進,互不影響,兩道口。
沈延非微一揚手,帶上這道隔音門,經過佔據整面牆的靶場,他似乎只是順便拾起了一把通黑的擊用槍,從固定上拆下來,在線條分明的手指間隨意轉了轉,閑散把玩。
他腳步沒停,長包裹的雙不疾不徐,繼續走向影音區,風平浪靜坐在第一排的皮長沙發上,沙發旁擺著深矮幾,茶溫正合適,他放下擊槍,扣著細瓷杯耳抬起,水流過間,他才朝正對面抬起眼。
前方本該是觀影的巨大熒幕,屏被升起,變一片缺照的空地,現在空地中央,四五個人沉默站著,沒有多餘舉,無形圍住臉慘白的男人。
他出一點聲,膝蓋就被從後面狠重踢彎。
想發出的痛音效卡在嗓子裏,生生忍住。
沈延非邊似是而非地抬了抬:「原來商總也會學聰明?怎麼不繼續了。」
商瑞左膝在地板上,吃力抬起來,死死瞪著面前的人。
他以前也怕沈延非,無論這個人本,還是他站的位置握的權,加上只有自己知道的那段過去,他都自知招惹不起。
猜你喜歡
-
完結80 章

我終于失去了你
十歲那年,許諾撞見父親出軌,父母失敗的婚姻讓她變得像只刺猬,拒絕任何人親近。高考完的一天,她遇見了莫鋮,這個玩世不恭的少年對她一見傾心。莫鋮與許諾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一個熱情如火,一個患得患失,卻在不知不覺中,許諾慢慢動了心。不料,一次生日聚會上的酒後放縱,莫鋮讓許諾失去了所有,包括心中至愛的親人。剛烈的許諾選擇了一條讓所有人都無法回頭的路,她親手把莫鋮送進監獄。多年後,兩人在下雪的街頭相遇,忽然明白了,這世間有一種愛情就是:遠遠地看著我吧,就像你深愛卻再也觸摸不到的戀人。 一場來不及好好相愛的青春傷痛絕戀。十歲那年,許諾撞見父親出軌,父母失敗的婚姻讓她變得像只刺猬,拒絕任何人親近。高考完的一天,她遇見了莫鋮,這個玩世不恭的少年對許諾一見傾心。莫鋮:你向我說后會無期,我卻想再見你一面。許諾:全忘了,我還這麼喜歡你,喜歡到跟你私奔。洛裊裊:我永遠忘不了十七歲的夏天,我遇見一個叫趙亦樹的少年,他冷漠自私,也沒多帥得多驚天動地,可怎麼辦,我就是喜歡他,喜歡得不得了……趙亦樹: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什麼時候去,我只知道,我想見她,見到她會很開心。
33.3萬字8 6890 -
完結320 章

總裁娶妻套路深
原本只想給家人治病錢,沒想到這個男人不認賬,除非重新簽訂契約,黎晴沒得選擇,只能乖乖簽字,事成之后……黎晴:我們的契約到期了,放我走。傅廷辰:老婆,結婚證上可沒有到期這一說。--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86.9萬字8 37855 -
完結476 章

偏要
楚意沒名沒分跟了晏北傾八年,為他生了兩個孩子。 病得快死的時候,問晏北傾,能不能為她做一次手術。 卻只得到一句,你配嗎? 而他轉頭,為白月光安排了床位。 這個男人的心是冷的,是硬的。 瀕死的痛苦,讓她徹底覺悟。 身無分文離開晏家,原以為要走投無路,結果—— 影帝帶她回家,豪門公子倒貼,還有富豪親爹找上門要她繼承千億家業。 再相見,晏北傾牽著兩個孩子,雙眼猩紅:楚意,求你,回來。 楚意笑笑,將當年那句話送回: 晏北傾,你不配。
66萬字8 58645 -
完結1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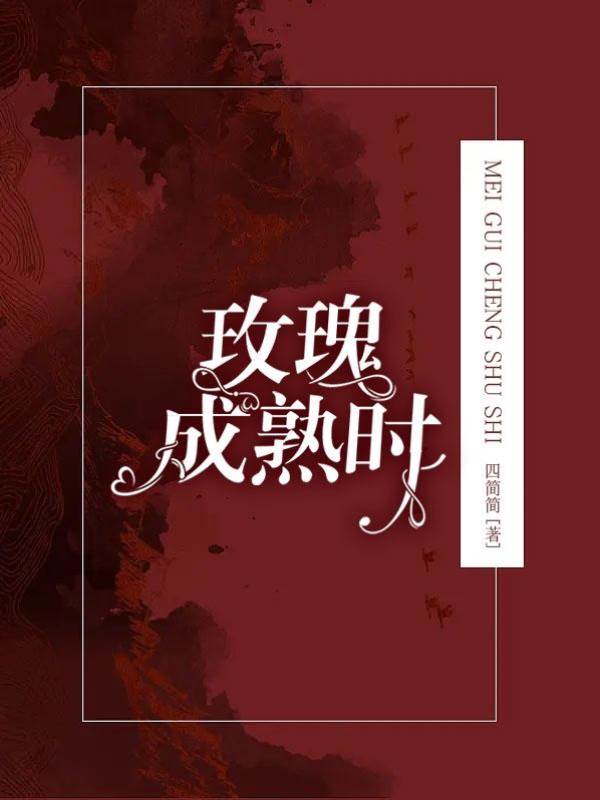
玫瑰成熟時
蘇落胭是京北出了名的美人,祖籍南江,一顰一笑,眼波流轉間有著江南女子的溫婉與嫵媚。傅家是京北世家,無人不知傅城深是傅家下一任家主,行事狠辣,不擇手段,還不近女色,所有人都好奇會被什麼樣的女人拿下。蘇落胭出國留學多年,狐朋狗友在酒吧為她舉辦接風宴,有不長眼的端著酒杯上前。“不喝就是不給我麵子?我一句話就能讓你消失在京北。”酒吧中有人認了出來,“那個是蘇落胭呀。”有人說道:“是那個被傅城深捧在手心裏小公主,蘇落胭。”所有人都知道傅城深對蘇落胭,比自己的親妹妹還寵,從未覺得兩個人能走到一起。傅老爺子拿著京北的青年才俊的照片給蘇落胭介紹,“胭胭,你看一下有哪些合適的,我讓他們到家裏麵來跟你吃飯。”殊不知上樓後,蘇落胭被人摁在門口,挑著她的下巴,“準備跟哪家的青年才俊吃飯呢?”蘇落胭剛想解釋,就被吻住了。雙潔雙初戀,年齡差6歲
23.5萬字8 17103 -
完結166 章

頂不住了,傅總天天按住我不放
[頂級豪門 男主冷傲會撩 女主嬌軟美人 後續男主強勢寵 雙潔]時憶最後悔的事情,就是招惹渣男未婚妻的小叔子。本來吃完就散夥,誰知請神容易送神難。一場意外,兩相糾纏。“傅先生,這事不能怪我。”傅霆洲步步緊逼,“ 所以你必須,我想你就得願。”傳聞中桀驁不馴的傅霆洲步步為營想偷心,其實最先入心的是他!
61.1萬字8.18 402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