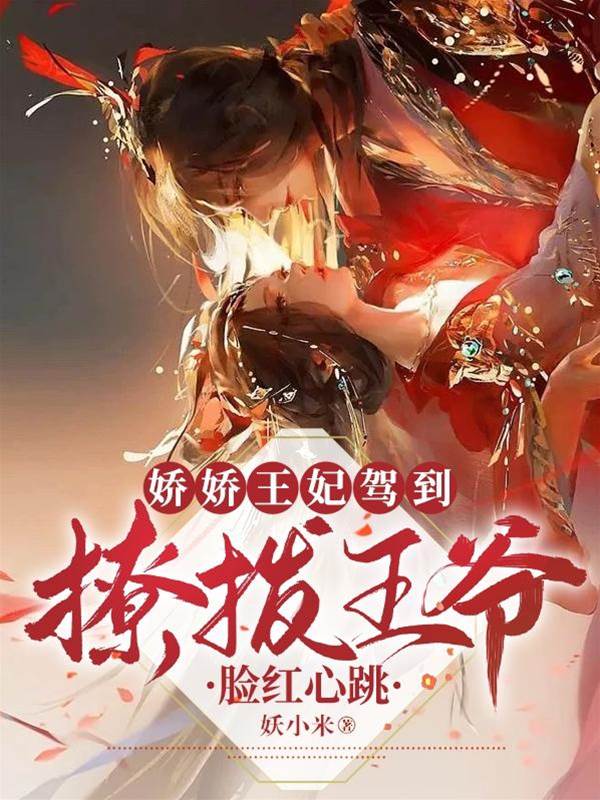《鬢邊待詔》 番外十·獻玉(6) 他能體會陛下待他的好。
南晉起,是從司馬泓繼位之初開始的。
司馬泓借世家的力量登基,卻沒有反制世家的能力,各大世家為了爭權奪勢,使出毫無底線的手段來侵占民田、迫良民為家奴。等到司馬泓晚年時,南晉寒門與貴族間的矛盾已經不可調和,屢屢鬧出世族以屠殺寒民為樂,寒民以報複世族為快的醜聞。
曾幾何時,南安北,大魏百姓攜家帶口渡過汜水,前往南晉安居,不過一十年的景,大魏建康一帶日益繁華,而南晉去,十室九空。
西亭議事時,有人說道:“眼下是最好的出兵時機,南晉皇室部生,只要控制住南晉皇室,這場仗就贏了一半,若是能離間南晉世族,或以利相,或以勢相,則此仗必贏,南晉必將歸于大魏。”
“若是南晉百姓起反抗,該如何是好?”
“此不足為患,上溯一百年,北魏南晉是一家,緣親厚與漢夷不同。且南晉有又有膽量反抗的百姓早已與南晉世族鬥得元氣大傷,更無力抵抗我大魏軍隊。”
“民心向背,得失之鑒,不可大意。”
“……”
紫竹林西亭裏從早議到晚,最終由清麟帝拍板決定了盡快對南晉發兵的事宜。加封王瞻為大司馬,由他擔任南伐主將,王旬暉擔任後勤轉運員,又點了幾個朝中新銳隨軍,以提振士氣,獎掖後進。
裴初以監軍的份隨軍南下,謝及音與清麟坐鎮。
九月底,大軍開拔,十萬鐵騎在前,一十萬步兵在後,沿著汜水,浩浩朝南晉行進。
宮裏,清麟偏要搬去顯宮,與謝及音一起睡。
識玉姑姑打趣了幾句,說眼見著陛下長獨當一面的帝,一見了母親,還是像小姑娘一樣黏著不放手。
十四五歲時聽了這種話,清麟尚會紅著耳朵反駁幾句,如今卻乖乖認了,早早上床,滾到裏側,占了謝及音本來的位置。
奈何生得貴,換床以後睡不著覺,翻來覆去幾回後,一只手輕輕拍了拍的肩膀。
謝及音聲道:“我人點兩支安神香,是鄭君容配的方子,安神助眠的效果不錯。”
清麟卻是心中有事,枕在肩頭問道:“娘,你當年為什麽要救我爹?”
謝及音微愣,笑道:“大半夜不睡覺,怎麽突然問這個。”
“是因為那時就喜歡他了嗎?”
謝及音半晌不語,過金綃帳的隙看向窗邊。
今夜月明星疏,流如水,照窗戶,人牽念遠行人,一時心生惆悵。
慢慢回憶著從前事,與清麟訴說:“……我像你這個年紀的時候,膽子很小,不敢與我爹說想嫁裴七郎。但人心的確很奇怪,我沒有膽子嫁給他,卻有膽子救他,比起喜歡他,最開始可能是憐憫更多一些。”
“憐憫……”
清麟著帳頂,腦海中浮現出司馬鈺的面容。
也覺得很奇怪,司馬鈺不是第一個能討喜歡的郎君,卻是唯一一個令牽念的人。除了欣賞他的姿容與才外,有很多次,見他坐在案前默默寫字,想起有關他的經歷與傳言,清麟會覺得心中一陷,微微酸。
原來這種緒是憐憫,竟比喜歡還要磨人,領教到了。
“那父皇騙過你嗎?”清麟問。
不知想起了什麽事,謝及音竟笑了,“騙過。”
“後來他做了什麽才求得你的原諒?”
謝及音輕輕搖頭,小聲說道:“我知道他騙我,但是從來沒有生他的氣,那時候,我只想讓他好好活著。”
當年裴七郎假死從公主府中,又中途折返,騙過許多次。或許是生過氣的,但一十多年過去後,記憶裏只剩當初最深刻的,才發覺那時就已他很深。
謝及音默默回憶從前事,聽清麟問道:“可我是大魏的君主,倘有人騙了我,是十惡不赦的欺君之罪……娘,你說我該原諒他嗎?”
謝及音轉頭看向,了的鬢發,“你是在糾結那位南晉太子的事嗎?”
清麟輕輕點頭。
“你分明早就猜出了他的份,如今又為了不讓他在你與故國之間為難,甘願出面做個壞人,將他在德宮。你待他這樣周全,莫說原諒不原諒,或許從來就沒恨過他騙你。”
清麟不想承認這點,道:“我大魏兒郎不缺胳膊不缺,憑什麽要待他這麽好。”
謝及音笑道:“阿凰,人可以欺你,但你不能欺心。”
這回清麟不說話了。
這死鴨子的格有些像謝及音年的時候,看清麟,仿佛看年輕時的自己,十分徹分明。
謝及音聲對說道:“咱們阿凰長了這麽大,一向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你若是願意為了誰曲藏心意,那一定是十分喜歡他,這是他的造化,你也不必委屈自己瞻前顧後。”
清麟問:“他若是不記我的好怎麽辦?”
“好與不好是用心就能會到的,”謝及音說,“他若待你有心,就一定能會你的好。”
有謝及音從旁勸開解,清麟的心開朗了許多。
南方戰事吃,南晉軍隊傾巢列于汜水南岸,意圖阻止大魏軍隊渡河。兩方僵持了近一個月,裴初帶一千銳在大霧的遮掩下渡汜水,令騎兵馬後拖著樹杈在山頭狂奔,作出沙塵飛揚、浩浩的氣勢,裝作要與汜水北岸的魏軍首尾包抄。
這并非什麽高明到讓人難以預料的計策,只是此計兇險,若非走投無路,一般人不敢行此險計。大魏此番占據攻勢,司馬鉞以為對方會慢慢熬,所以一邊派人擋在汜水南岸,一邊去周邊部落夷族借兵。
孰料他前腳離開南晉,後腳就被人“包抄”。虛虛實實,實實虛虛,南晉頓時作一團。
戰訊傳回大魏時已是十月,天氣轉涼,夜裏點燈看摺子時,不斷有飛蛾抖著翅膀往燈盞上撞。
德宮的侍過了傳話,被雪凝擋在了外面,兩人在廊下竊竊私語,被清麟瞧見,認得那侍是派去照顧司馬鈺的人,于是他到跟前回話。
侍說司馬鈺病了,“郎君說是風寒,不讓奴才驚擾陛下,只去太醫署拿了兩湯藥,可總不見好,近日整夜咳嗽,今早見帕子上有,奴才嚇壞了,不得不來驚擾陛下。”
清麟聞言蹙眉,思忖片刻,擱下筆道:“朕去瞧瞧他。”
自搬去顯宮與謝及音一起住後,德宮裏變得冷清。司馬鈺被在德宮一座小院裏,因的令,有宮人在這邊徘徊,推門只見滿地紅葉,吱呀聲驚起滿院棲息的鳥雀。
隨行的宮人都候在門外,清麟獨自走進屋裏,隔著一扇素紗落地屏風,約聽見床榻間傳來的咳嗽聲。
“是李人嗎?勞煩幫我倒杯水……太醫署那邊不必再去求,免得惹人閑話。”
司馬鈺昨夜久咳難眠,如今正面朝裏躺著,說話也有氣無力。
一杯溫熱的金銀花茶遞進帳中,遞茶的手瑩白如雪,染著紅蔻丹,司馬鈺驀然轉,撞檀香襲人的懷裏。
釵間流蘇垂落頸間,拂得人微,司馬鈺不可置信,握住了的袖子。
“陛下……怎麽到這裏來了?”
清麟的手過他側臉,發覺數月不見,他是真的消瘦了。
司馬鈺目不轉睛地著,雙目因含而顯得昳麗迫人,廓分明如削,五又添男子的英氣,清冽如山間泉,人既憐又。
不相見時,只在心裏念著他,孰料這牽掛日益積攢,如今乍見,積羽沉舟。
突然的落下的吻讓司馬鈺怔愣不敢彈,疑心這是久病癔癥,如夜夜夢中那般,只要他手就會消散。
環佩叮當作響,舌尖闖進來,嘗到清苦的藥氣後,緩緩蹙起眉心。
見要走,司馬鈺下意識回擁,他發燒了,上燙得嚇人,像一個火爐。
“朕疏于過問宮,他們竟敢如此怠慢你,”清麟著他的鬢角,問道,“怎麽病這副模樣?”
司馬鈺低聲道:“的秋天冷得太快,忘了添,夜間了點風。”
“你是想家了嗎?”
握在袖間的手收,他無力地哀求道:“不要趕我走,我會盡早養好病的。”
清麟嘆息,問道:“太醫署怎麽不來看診?”
司馬鈺不願在面前學舌,清麟將李侍喊來過問,李侍哭訴道:“姜醫正說司郎君本是賤民,用不慣宮裏的藥材,所以只隨意抓了一把藥渣子給奴才,也不許奴才找別的太醫問藥。”
這位姜醫正是姜還恩的弟弟,他們姜家一直想往帝邊塞郎君,記恨乞巧宴上被一個沒有來歷的窮小子了風頭。
“賤民嗎?”清麟聞言冷笑,李侍去太醫署傳旨,“以後姜家同輩子弟見了子玉,須得三步外叩首行禮,違者杖三十。”
李侍去太醫署傳旨,雪凝姑姑帶了掌院來看診,清麟坐在外室,品了一口茶後,宮人把這院子裏奇外外都換一遍。
猜你喜歡
-
完結1055 章

侯府小啞女
燕云歌自末世而來,重生侯府,她給自己定了個小目標:每天吃好喝好樂無憂!然而……她爹一門心思造反,她哥一門心思造反,她嫁個男人,還是一門心思造反。燕云歌掀桌子,這日子沒發過了!
272.1萬字8 16625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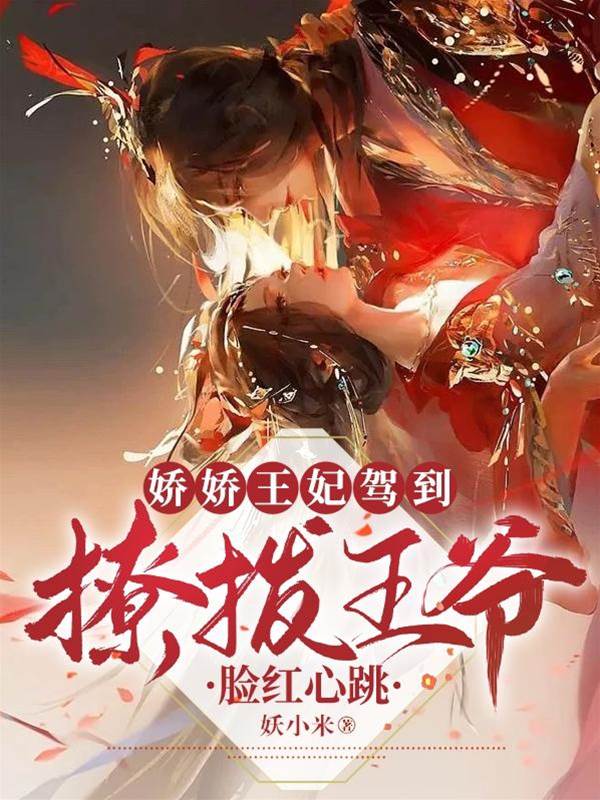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1576 -
完結372 章

穿成短命白月光后,和反派HE了
桑遠遠穿進一本古早玄幻虐戀小說裏,成了男主那個紅顏薄命的早逝白月光。男主愛她,男配們也愛她。女主因爲長了一張酷似她的臉,被衆男又愛又虐又踩,傷身又傷心。和男主的感情更是波折重重狗血不斷,虐得死去活來,結局還能幸福HE。桑遠遠:“不好意思本人一不想死二受不得虐,所以我選擇跟反派走。打擾,告辭。”反派長眸微眯,姿態慵懶,脣角笑意如春風般和煦——“我的身邊……可是地獄呢。”她沉思三秒。“地獄有土嗎?”“……有腐地。”“有水嗎?”“……只有血。”他想看她驚惶失措,想等她尖叫逃離,不料女子呆滯三秒之後,雙眼竟然隱隱放光——“正好試試新品種!”“……”他在最深沉的黑暗中苟延殘喘,從來也沒想到,竟有一個人,能把花草種滿一片荒蕪。
57.1萬字7.92 9525 -
完結313 章
亡國后成了反賊的寵婢
姜嶠女扮男裝當了幾年暴君。叛軍攻入皇城時,她麻溜地收拾行李,縱火死遁,可陰差陽錯,她竟被當成樂伎,獻給了叛軍首領霍奚舟。姜嶠捂緊馬甲,計劃著再次逃跑。誰料傳聞中陰煞狠厲、不近女色的霍大將軍竟為她破了例。紅燭帳暖,男人摩挲著她眼角的淚痣,眸色暗沉,微有醉意,“今夜留下。”*姜嶠知道,霍奚舟待她特殊,只是因為她那雙眼睛肖似故人。無妨,他拿她當替身,她利用他逃命。兩人各有所圖,也是樁不虧的買賣。直到霍奚舟看她的眼神越來越深情,還鄭重其事地為允諾要娶她為妻,姜嶠才意識到,自己好像是在作繭自縛——
49.2萬字8 68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