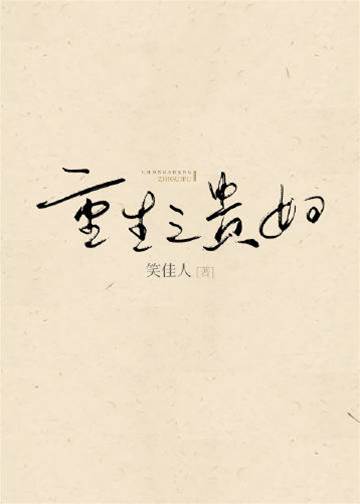《千山青黛》 第 125 章(八百道隆隆的暮鼓聲中,一...)
八百道隆隆的暮鼓聲中,一隻早便聞聲不驚的昏收翅半闔眼皮,高高停在一座崇宮峻殿的頂上。琉璃碧瓦反夕,令鳥背上的一片漆羽也耀著一層金緋的浮。
“周畫師今日也沒畫完嗎?”
一名灰小宮監抱膝坐在崇天殿前的一道文石臺階角落裏。他瞇眼眺著遠宮牆後那即將消失的半夕,順口向著邊同伴發問。
殘紅斜照,鋪滿了大半的宮階。在日暮影裏,宮階之上這座殿宇廓影顯得愈發巍峨宏偉。正如它的宮殿之名,等到啟宮的那一天,它將會如天樞星辰般憑淩長安,著來自四圍的拱拜和景仰。這兩名趁著傍晚在此躲懶小歇的宮監影,在此宮殿之前,更是渺小得更是如同兩隻微蟻。
然而,這大一片看起來如爐火一樣的紅,照在人的上,卻是冷的。
便如這了冬的長安,人覺不到半分的暖意。
同坐的另名小宮監撮撚幾下自己凍得發冷的手指,扭頭看了眼後那麵半開的雕雲龍紋殿門,用帶了幾分抱怨的語氣道:“可不是嘛!想是又要畫到半夜三更了!”
從早到晚,無論幾時,中那繪壁畫的畫師若是不走,他們這些在此值事的宮監便也不能離開,須隨時應命。
因為公主重視,對畫師也極是禮遇,上命下達,加上此事的重要不言而喻,故從壁畫開畫以來,對這裏的供奉,便極為細致周到。
這兩名小宮監,一個在此專門司炭,另個則是司茶。
原本這是他們職責。然而周畫師的卻有幾分清高,日常對著他們這些小宮奴,雖不至於頤指氣使,卻分毫也不掩藐視之態,說話必遠隔三尺,且不拿正眼看人——不但對他們這些不起眼的小閹奴是如此態度,連此宮管事曹宦,他亦是不大搭理。
雖然閹奴人輕視是天經地義,但想到從前公主為畫師時的風度和待下,兩相比較,小宮奴們私下抱怨幾句,也就在所難免了。
“你有沒聽人說,聖人或將取消萬壽之慶?”
“聽說了,也不知是真是假。”
“我瞧周副直這幾天好似有些心神不寧,連作畫都慢了幾分,莫非此事是真?他好不容易得到公主賞識,才有此臉的機會,若真取消萬壽,豈不是空歡喜一場?”司茶宮監將聲音得極低,語氣帶了幾分幸災樂禍。
司炭的小宮監膽小些,不敢多談這些,隻道:“走了走了,這和咱們也是無關。天也快黑,別坐了!我去瞧瞧炭爐,加些炭吧。天氣愈發冷了,也不知今歲第一場雪何時才來。若凍壞周畫師的手,被曹公公知曉,我可吃罪不起!”
他率先起,撣了撣自己那遭石階寒意沁而變得冰涼骨的,呼同伴往裏去,發現沒有跟來,轉頭,看見他已朝著西側的方向趴跪了下去,去竟見大宮監楊在恩伴著一頂兩人抬的小輦正往這邊行來,輦中之人,看去應是公主。
沒有儀仗和隨扈,公主上也隻係了一領暗紫厚緞連帽披風。殿前廣場空闊,暮風大作,戴著帽擋風。輦遠遠停在了西側的一道便階前,從輦中下來,落帽,隨即沿著便階往上,向大殿行去。
小宮監醒神,急忙也原地下跪,叩拜迎接。
隨公主的不期而至,日暮沉寂被打破了。早有另外看見的人去報給了曹宦。曹宦飛奔趕來,帶著值事的眾多宮監拜迎。
絮雨停在一道宮廊之中,含笑示意眾人起。
記得上回來時,太子和康王仍各安好,誰知隨後便出了那樣翻天覆地的大事,後來又傳,竟連駙馬也卷了進去。
餘波尚未散盡,就在近日,宮裏又有個說法,朝廷或將取消原定的即將到來的萬壽之慶。
聖人連失二子,值此龍國皆是不寧之際,取消萬壽,是理所當然。隻是如此一段實在算不得長的時日裏,變忽然如此之大,仿佛炎夏直轉嚴冬,當此刻再次見到公主到來,此宮之人,上從曹宦,下到方才那兩名雜役小奴,人人難免都有幾分恍若隔世之。
曹宦扭頭發現後迎接的隊列之中還一人,急忙吩咐近旁一個閹奴:“快去把周鶴來,拜迎公主!”道完,又解釋:“公主勿怪。他有幾分古怪,作畫之時,不許人在近旁。奴婢遵公主先前的吩咐,全部照他喜好服侍,倒將他慣得目中無人,以作畫為由,敢連公主都不敬了!”
這曹宦雖也是閹人,但好歹是司宮臺裏有頭有臉之人。此前因了公主的緣故,他對周鶴的侍奉也可謂是盡心盡力。但那畫師麵對他時,雖不至於象對一般閹奴那樣不假辭,卻也仍掩飾不住發自心的疏離。他又不是呆愚之人,豈會沒有知覺?私下也不止一次暗忖,這周鶴沒士人之命,卻竟也如士人那般自高,瞧不起他們閹人,心中早就不忿,便趁此機會告狀。
絮雨阻止:“不必打擾他。你們也無須跟來,該休息的去休息。我來隻是想看下壁畫進展。”
了崇天殿,撲麵映眼簾的,是從殿頂梁柱一直垂落到地麵的一圍巨大的帳幕,將全部未完工的壁畫遮得嚴嚴實實。
雖然或是阿公並無這樣的作畫習慣,但出於對新畫的保護,或是畫師單純不願人看見自己尚未完工的作品而有此設置,也很是正常。
無論外間曾掀起過怎樣的腥風雨,在這間寧靜的大殿裏,帳幕之後,隔出了一個由線條和彩繪所構造的輝煌而神聖的世界,畫師徜徉天上和人間,這是何等靜好的一件事。
不驚擾到或正在潛心作畫的周鶴,走到帳幕之後,輕輕揭開一角,向裏看了過去。
有些時日沒來了,今日終於得空再來,和想的一樣,壁畫已完工大半。此刻呈現在麵前的,是一副主已,填也過了半的即將完的作品。
確實沒有錯看人,周鶴是個極才華、又有能力將設想通過畫筆作完全展現的畫師。
在他正式落筆之前,他曾向詳細描述過關於壁畫創作的全部構想,並以此,確定了一個創作的大框架。
對這個構想和框架,絮雨是認可的,而一旦認可,出於惺惺相惜之念和對自己眼的信心,便沒有作任何的幹涉,許他隨心創作。
此刻展現在麵前的,雖然還隻是一副並未全部完工的壁畫,但無論是畫中神仙群像的布局還是山水城池的表現手法,皆極到位,整恢宏之餘,於細節又不乏描。恍惚之間,絮雨看到了幾分阿公畫作的風範。
隻有一點有點意外。周鶴並未如曹宦所言的那樣,在作畫。地上淩地散落著幾支沾滿料的用過的畫筆,他就胡坐在工案前的地上,垂首,背影一不,乍看仿佛倦了,坐地正在休息,然而再看,卻又似正沉浸在某種思慮當中,背影著沮喪和萎靡之態。忽然,他仿佛覺察到後有人,起初大約以為是某個宮監,麵帶不悅地回過頭,待看清是,一愣。
很快,他回了神,從地上飛快爬起,連忙下拜。
“不知公主駕到,失禮了!請公主恕罪!”
他比剛宮時看起來憔悴了不,頭發淩,麵生胡須,雙手和不知幾日沒換的上沾滿了幹結的料殘痕,眼裏更是布著。
如此一段時日,便能將這幅作品畫到這種程度,不用問,絮雨也知他必在趕工,辛苦是不用說的。笑著他起。
周鶴終於依言從地上爬起,察目落到壁畫之上,反應了過來,急忙指著後壁畫介紹:“公主請看,這便是我這些時日畫出來的。原本早想請公主前來指教,隻也知公主近來應當有事,怎敢打擾,又不敢耽誤進度,隻能自己著頭皮胡畫下去了,也不知是否能用。公主此刻駕到,實在如同天降甘霖,倘有哪裏不合公主心意,或是沒有畫好,請公主不吝賜教,我立刻修改,改到公主滿意為止。”
從和周鶴結識以來,絮雨便有一種覺,他雖長久鬱鬱不得誌,甚至一度潦倒到了被趕出旅館的地步,但此人在多多應是有著幾分自負的。不但如此,越有才華的畫師,對自己落筆所作的畫作往往也越自信,因知曉何以如此落筆,要表達的又是何。完全聽從別人意見修畫,結果對畫作未必就是有利,修改之後,反而可能不如原畫。
猜你喜歡
-
完結181 章
鳳隱天下
洞房夜,新婚夫君一杯合巹毒酒將她放倒,一封休書讓她成為棄婦!為了保住那個才色雙絕的女子,她被拋棄被利用!可馳騁沙場多年的銀麵修羅,卻不是個任人擺布的柔弱女子。麵對一場場迫害,她劫刑場、隱身份、謀戰場、巧入宮,踩著刀尖在各種勢力間周旋。飄搖江山,亂世棋局,且看她在這一盤亂局中,如何紅顏一怒,權傾天下!
17.9萬字8 43254 -
完結418 章
鳳逆九天:一品毒妃傾天下
她是將軍府的嫡女,一無是處,臭名昭著,還囂張跋扈。被陷害落水後人人拍手稱快,在淹死之際,卻巧遇現代毒醫魂穿而來的她。僥倖不死後是驚艷的蛻變!什麼渣姨娘、渣庶妹、渣未婚夫,誰敢動她半分?她必三倍奉還。仇家惹上門想玩暗殺?一根繡花針讓對方有臉出世,沒臉活!鄰國最惡名昭著的鬼麵太子,傳聞他其醜無比,暴虐無能,終日以麵具示人,然他卻護她周全,授她功法,想方設法與她接近。她忍無可忍要他滾蛋,他卻撇撇唇,道:“不如你我二人雙臭合璧,你看如何?”【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109.7萬字8 73395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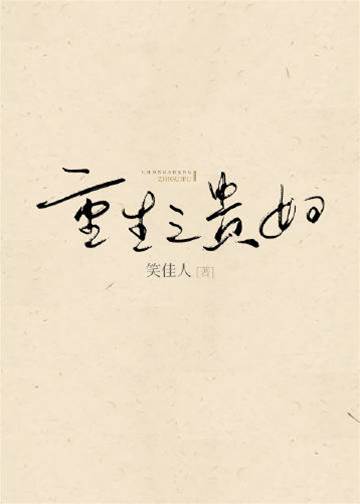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1 18727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