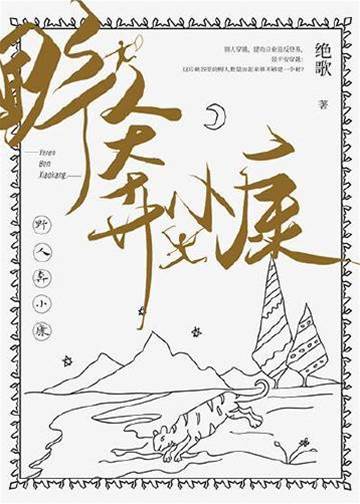《隔壁的小書生》 第105章 更
饒是像白星和廖雁這種肚子里沒什麼墨水的人也覺得眼前的景致極了,腔中仿佛瘋狂翻滾著某些陌生的,想說卻又說不出來。
若說下雨天最適合干什麼?那肯定是睡懶覺。三人一路奔波也算辛苦,草草用了午飯之后便去房中歇息。
原本是打算稍事休息后便出門轉一轉,省得辜負好韶,奈何不知怎的,天上就飄過來兩朵烏云,把日頭遮了大半。
舒適的床鋪,不不晴的天氣,細細的溫雨聲……一切都是那麼適合睡覺!
三人只覺得床鋪上好像出無數只小手,將他們的每一寸都牢牢鎖定,數次掙扎都無濟于事。
眼皮好沉吶,腦袋好昏啊,好乏呀,不如就再睡一會兒吧……
這一睡就到了傍晚,三人先后醒來時,紛紛大驚失,一度懷疑店家之前提供的茶點茶水中是否下了迷魂藥……
這家客棧本就是一座大園林,里面又細分了九個院落,每一個院子都是單獨的兩進或三進小院,非常寬敞安靜。
他們住的這個院子碧塘池,只有兩進,頗為小巧,但亭臺樓閣應有盡有,可謂五臟俱全。院子中心還有一從西湖引進來的活水構建的小池子,里面養了不大的鯉魚。
孟就指著那池子笑道:“這下雁雁想吃鯉魚可方便了。”
廖雁才要說話,外面就有伙計敲門,詢問他們是否需要用晚飯。
孟笑道:“這銀子沒白花呀,當真周到。”
以往住在別家客棧時,店家可不管你吃沒吃飯。
飯自然是要吃的,然后那伙計又問他們是要在院子里吃,去前廳吃,還是索坐著畫舫游船去西湖上吃。
他們仨哪經歷過這個?一時都來了興致,當即異口同聲的說要去湖上吃。
去湖上吃也有多種選項,可以去大畫舫上跟其他人拼桌,類似于水上修建的餐廳;若是手頭寬裕,財大氣的,則可以自己單獨包一條游船。
白星白姑娘自然是后者,于是不過短短一天時間,就扔出去將近三百兩。
孟簡單的算了一筆帳,得出結果后,不倒吸一口涼氣。
果然好東西都貴,好日子也費錢……
掙錢掙錢,攢錢攢錢,自己也不能花星星的錢呀!
只是他也難免十分懷疑,此生自己掙錢的速度,究竟能不能趕上星星花錢的速度?
此時金烏西墜,云霞滿天,那場來的突然的雨,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正好出游。
西邊天上的太仿佛一顆大火球,金大盛之外,又將整片天空都涂赤紅玫紫,怎一個轟轟烈烈了得。
那一片一片濃烈的火燒云悉數倒映在寬闊的湖面上,將一池湖水染得通紅。平靜的湖面上時不時有水鳥掠起,尖尖的中銜著扭的小魚:天要黑了,它們也該帶著晚飯家去啦!
太尚未落下,東邊的月亮卻已迫不及待升起來,一時間天空中日月同輝、彩霞爭艷,襯著這萬里荷塘、清香滿天,好一個人間天堂。
不過他們才剛出來,就遇見了一件不大痛快的事。
在前方不遠有一艘兩層的畫舫,足有三四丈長,從頭到尾都雕刻著的花紋,涂抹著均勻的朱漆,哪怕是租,一天也要不銀兩。
且那畫舫之中不斷有竹之聲傳來,顯然船上還有隨行侍奉的樂人,想必乘船者非富即貴。
原本這畫舫跟白星他們也沒關系,只是才走出去沒多遠,就見畫舫之中突然出來一只纖纖玉手,二話不說就掐了一朵剛盛開的荷花。
雖說這西湖之中的荷花屬無主之,但不管是本地居民還是過往游人都十分惜,等閑不會隨便掐。即便要掐花,也必然等到大片荷花怒放時,而非眼下這三兩朵零星。
再退一步說,掐花畢竟沒有犯法,若果然用心對待也就算了,偏那子拿在手中賞玩一會兒,竟又把手一松,任憑那可憐的荷花墜湖中,隨著水波飄遠了。
就聽咯咯笑幾聲,又往遠指了指,也不知說了幾句什麼,那兩層畫舫就又朝著幾支荷花駛去。
三人看的眉頭直皺,饒是廖雁那個糙漢也覺得不大舒坦。
再看時,卻見那子又陸續掐了丟,丟了掐,接連禍害了三四朵,最后才捧著一朵大紅的回船艙去了。
孟看得心塞,接連嘆了好幾口氣,又船家換個方向劃,避過那艘畫舫去。
罷了罷了,眼不見心不煩,多一事不如一事……
正好船家也對那子的行為十分不滿,不得一聲,得了命令之后立刻調轉船頭往另一個方向去了。
早有人準備好了熱飯熱菜,三人將剛才的曲撇開不管,對著西湖晚霞又吃又喝,不覺興致高漲。
孟不詩興大發,一張就嘰里呱啦念了七、八首詩詞出來。
白星和廖雁無點墨,對此狗屁不通,自然聽不懂里面飽含了多典故傳說,更不知道若是流傳到外面去,又會引來多追捧和稱頌。
只是他們覺得十分工整對仗,而且句句押韻,落在耳中,倒也不比唱曲差多,便都很給面子的鼓掌好。
那撐船的水手載多了文人雅客,常年耳濡目染,也煉出幾分耳力,當即笑道:“小先生好文采呀,來日必能高中。”
若放在以前,白星和廖雁聽了這話必然忐忑,生怕孟景生。只是出來之后經歷了許多事,孟的心境遠比以前更加開闊,心態也更加平和,如今倒也不必擔憂了。
果不其然,就見孟靦腆一笑,擺擺手道:“文武第一,武無第二,我還差得遠呢。”
幾人才要笑時,卻聽不遠忽然有人說:“這位小公子實在過謙了。”
三人轉頭去,腦海中登時浮現出一句話:
真是討厭什麼來什麼。
可不就是剛才那艘兩層畫舫嗎?
就見從船艙里走出來幾個青年男,都是十來、二十出頭年紀,顯然是結伴游湖的。
他們的穿戴打扮都十分致,后還跟著許多侍從,顯然非富即貴。
廖雁當場就哼了聲,孟也實在不愿意跟這些人打道。
雖說掐花的是那個子,但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同伴毫未加制止,想必也非善類,還是遠離的好。
他很敷衍地朝他們拱了拱手,“不敢不敢。”
“這有什麼不敢的,”一個跟白星差不多年紀的孩卻笑道,“要我說你的詩詞就作的很好,可比那些什麼沽名釣譽的才子厲害多啦。”
一雙眼睛都牢牢釘在孟上,里面明晃晃著意,顯然對他十分有好。
此言一出,圍繞在邊的幾個年輕人臉頓時不好看起來。
只是那和邊略年長幾歲的青年便如眾星拱月般站在人群中央,有以他們為首的樣子,誰也不敢說什麼。
孟見手上擎著一只大紅的荷花,便知道這就是剛才掐花的子,越發沒了好,“姑娘謬贊,只是我們用完飯要回去休息了,告辭。”
此言一出,剛還笑盈盈的孩子卻突然掛下臉來,抬手就將那朵紅的荷花丟湖中,兇道:“你竟敢瞧不起我!”
平心而論,柳眉杏眼量窈窕,生得十分麗,可惜脾氣壞的很,生生將麗的容貌打了個對折,約有點面目可憎起來。
孟最怕跟不講道理的人打道,頓時一陣頭大,一邊示意船家趕走,一邊胡道:“姑娘實在說笑了,你我之前素未謀面,互不相識,又何來瞧得起瞧不起一說呢?”
那姑娘還沒說什麼,后站著的幾個男子卻先不樂意了,紛紛出言搶白道:“那你跑什麼?”
“黃姑娘跟你說話,那是瞧得起你,你別給臉不要臉!”
孟還沒怎麼著呢,白星的臉已經完全沉下來。
右手往桌面上一抹,就將兩只酒杯抓在指間,手腕一抖,酒杯就嗖的飛了出去。
但聽得兩聲悶響過后,剛才說話的兩人便哎呀哎呀的,捂著痛呼出聲。
那位黃姑娘和他邊兄長模樣的青年齊齊回去看,恰好看到一縷縷鮮順著那兩人的指流出來。
青年的眼睛一瞇,用力將其中一人的手拉下來一瞧,這才發現他的牙齒竟都被人打碎了。
好厲害的功夫!
此時天微黑,兩艘船隔的也不算近,想同時打中兩個人的并不容易。
他自小習武,自問已經小有所,卻也不敢保證一定能做到。
想到這里,他忍不住看向白星,“這位姑娘好俊的功夫,不知是何名號?”
這麼年輕,好像比自己的妹妹也大不了幾歲,竟然有這樣的手,杭州地界上什麼時候出了這樣厲害的人?
白星懶得跟他們說話,直接對船家道:“回去。”
那船家臉上卻流出一點驚恐的神,抓著船槳的手都有點抖了,“姑娘,你怎麼就手了呢?”
白星約意識到什麼,“你認識這些人。”
船家點了點頭,又朝那艘畫舫撇了眼,眼神十分復雜。
而那位黃公子見白星不回答,多有點丟面子,語氣也不如剛才好了,“這位姑娘,我不管你是何方神圣,我的朋友只不過說了兩句話,你就下此狠手,未免有點太過分了吧?”
“打的就是你們!”廖雁嗤笑道,“既然不會說人話,那就干脆別說了。”
猜你喜歡
-
完結488 章

重生七零做團寵大佬
【空間+年代+甜寵】末世研究院大佬重生成了70年代小村花。幾年後,京都上層圈子轟動了,桀驁不馴的顧家太子爺竟看上了一名村花。聽說,這村花還是個村霸,又懶又兇沒文化,全家都是極品!村姑怎麼能和上層圈子裡的女孩相提並論?眾人齊齊嘲諷宋楚。然而……養殖、種植大咖;餐飲業大亨;教育機構創始人;全國首富……爭先恐後表示:「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靠我妹妹宋楚!」眾人集體懵逼:真的嗎?我不信!誰知當天,國內最高生物製藥研究院官宣:「祝賀宋楚博士拿到國際製藥金獎,同時感謝宋博士帶領我們成為全球最先進的製藥機構。」緊跟著刊登了花樣讚美的文章,還有一張她拿著獎盃的照片。看著膚白貌美氣質出眾的宋博士,一眾人驚掉了眼鏡,說好又土又沒文化的村姑呢?這明明是又美又帥又有才華的人生贏家……顧家太子爺兼科技大佬也在同一時間找上了宋楚:「敢不敢先對我負個責……」
89.2萬字8 41468 -
完結20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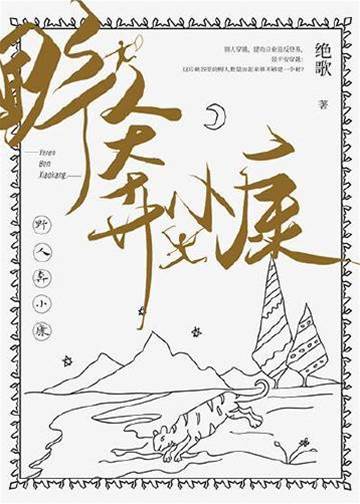
野人奔小康
景平安在職場上辛苦打拼,實現財富自由,卻猝死在慶功宴上,悲催地穿越成剛出生的小野人。有多野?山頂洞人有多野,她就有多野,野人親媽茹毛飲血。鉆木取火,從我開始。別人穿越,建功立業造反登基,景平安穿越:這片峽谷里的野人數量加起來夠不夠建一個村?…
80.8萬字8 5279 -
完結748 章
我真不想當菜農啊
廚神唐豆奪冠后,給自己放了幾天假,偶得玉牌,獲得傳承、在靈雨的加持下,種草藥,建農場,帶領村民一起致富。唐豆突然想起,自己明明是廚神啊,怎麼被迫種菜了吶?
132.4萬字8 120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