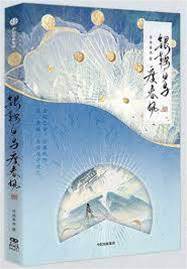《掌上嬌卿》 第92章 晉江正版92
程楚云抱著雙膝坐在床榻角落, 江年還在安。
安人的方式當然就是痛罵謝斐。
沈嫣進門的時候,看到程楚云凌的碧綠的外, 微微怔忡了下, 然后上前坐到右手邊,拍了拍的后背。
“阿楚,對不起。”沈嫣想了想,還是輕輕地說了這一句。
江年立刻抬眼糾正:“阿嫣, 此事與你無關, 都是謝斐的錯!還有那下藥之人, 佛門凈地做這種禽事, 菩薩不會饒恕他的!”
話雖如此,可看到程楚云這一, 沈嫣也能猜到謝斐或許是把當自己了,謝斐喜歡青碧, 從前時常這麼穿。
出了這種事,子永遠是被世人詬病的那個,除了一聲抱歉, 沈嫣不知道還能說什麼。
程楚云沒有回應, 只是暗暗咬著牙哭,一張清麗的臉蛋哭得通紅。
“玉嬤嬤, 真是你?這藥你怎麼解釋!”
小沙彌在指認玉嬤嬤之后, 護衛當即上前搜, 果然在玉嬤嬤的指甲里發現了殘留的催--藥。
玉嬤嬤這下百口莫辯,謝斐更是詫異, 凌安直接破口大罵:“你自作聰明什麼?誰給你的膽子給主子下藥!”
屋三人聽到靜, 也是同時一驚。
江年也聽說過玉嬤嬤, 沈嫣親之后, 便知道鎮北王府有個時常為難的刁奴,借著謝斐娘的份拿喬。
方才江年在屋聽到一個娘寺還覺得奇怪,原來就是下的藥!
江年冷笑一聲,“看來不是著了外人的道,應該蛇鼠一窩才是!”
怕沈嫣剛來不解,復又解釋:“方才你沒聽見,原本這下了藥的茶水是要送到我屋子里的,這老毒婦怕是以為咱們三個在房里,好讓主子占咱們的便宜呢!尤其是你,阿嫣,幸好你沒在這兒,否則你若是被謝斐欺負了,這輩子都擺不了他了!”
沈嫣還不知其中竟有這些彎繞,一時還有幾分后怕。
倘若今日不去玄塵大師,們三個的確有可能會在一起吃茶,一旦玉嬤嬤謀得逞,中了藥,主投懷送抱,再與謝斐有了夫妻之實,那麼這半年的避讓都有可能被惡意解讀為拒還迎,后果不堪設想,甚至連江年也可能被連累。
從前只知玉嬤嬤為人苛刻,不想竟是如此歹毒。
側人輕輕泣了聲,江年才覺失言,趕忙寬道:“阿楚別擔心,今日這麼多雙眼睛盯著,鎮北王再想偏袒自己的兒子也不的,我就算去求姨母,也定要讓謝斐給你個代!”
外面又是一陣喧嚷,應該是那護衛首領還在搜查取證。
沈嫣輕輕嘆息一聲,拍了拍程楚云的肩膀,“我出去瞧瞧。”
江年點點頭,提醒:“你小心謝斐,他的藥還沒解呢。”
沈嫣道聲“好”,才走到門外回廊,一道凌厲赤紅的目立刻落在上。
便是不想注意,這樣的目也不容忽視。
謝斐知道自己現在非常狼狽,渾燥熱難當,衫不整,發髻凌,他在眼里應該是個齷齪不堪之人吧。
不過跟他老子比,這也不算什麼了。
這對夫-婦做出的丑事才是真正的齷齪不堪,天理不容!
謝斐雙手被人反扣在背,突然狂笑起來,笑夠了,又仰起頭,盯著眼前之人,“沈嫣,別拿這種眼神看我,你自己又是個什麼——”
話音未落,倏忽“嘭”然一聲,當一腳,生生將那句謾罵了回去。
跟著院中響起一道婦人的驚呼。
謝斐還未反應過來,口驟然傳來碎裂般的疼痛,整個人被踹飛出去,重重摔在地上!
連扣住他手臂的兩名護衛都沒能承住這樣的沖力,不僅人沒抓住,手腕都被這力道震得抖不止。
院響起此起彼伏的叩拜聲,玉嬤嬤更是嚇得腦中空白,方才那一聲完全是下意識的尖。
現在渾劇烈地發抖,連滾帶爬地跪到那著玄袍的男人面前,“王爺!不是世子爺的過錯,您罰老奴吧,是老奴豬油蒙了心!與世子爺無關!”
謝危樓看一眼沈嫣,確認無事之后,才轉過頭冷冷掃視一圈,目最后落在這個毒婦上。
他手一抬,立刻有兩個護衛將人扣在地上,玉嬤嬤雙手被反剪在后,左臉被侍衛一腳抵在地磚上不能彈。
謝斐被踹出一丈多遠,捂著心口直氣,他沒想到謝危樓今日也在此。
他果然還是來了!沈嫣在哪,他便去哪,他怎麼會放過這大好的私通機會!
謝斐抹去角漬,挪一下都是劇烈的疼痛,這一腳將他所有因催--藥而混沌的意識全部聚攏起來,快將他心臟都震碎了!
他垂頭看向自己微微敞開的口,這塊皮幾乎模糊,心口疼痛裂。
“將謝斐帶過來!”
聽到他那好父親冷聲示下,連名帶姓地稱呼他,謝斐冷笑了聲。
他還知道他姓謝,還知道他是他親兒子啊。
謝斐被人拖上前,一口鮮噴在青石磚上,頃刻就是斑斑點點的跡,他艱難地仰起頭,目慢慢向上,猛然注意到謝危樓腰間所掛的香囊,那百福駢臻的樣式……
瞬間瞳孔驟!
原來還不止那金蟬,沈嫣那日在玲瓏繡坊拿回家的繡樣也是給公爹繡香囊的。
謝危樓連避都不避,天化日之下,將與兒媳私相授的香囊掛在腰間!
謝斐搐著,想要說些什麼,卻發現自己心口劇痛難當,痛達間,幾乎開不了口,他死死盯著那香囊上的繡紋。
謝危樓面容淡漠冰冷,轉過看向沈嫣,聲音放低,用僅有兩人聽到的嗓音:“先進屋。”
沈嫣遲疑了一下,點點頭,相信他能理。
一進門,看到程楚云坐在榻上,眼淚不停地往下流,沈嫣的心也微微揪了起來。
經此一事,謝斐的真實份怕是離昭告天下不遠了,他的親生父母若是有權有勢倒還好,可倘若來日堂堂世子爺跌落云端,一無所有,又該如何給阿楚一個代呢?
這麼多年,雖啞,卻不盲。
永遠有一道拘謹但熱切的目注視著自己的丈夫,又豈會半點都察覺不出來?
謝危樓看著進去,然后朝一旁的住持方丈等人拱手,“幾位大師,本王治下不嚴,連累佛門莊嚴清凈地染污,還請諸位大師見諒。今日之事,本王定會嚴懲不貸,給玉佛寺一個代。”
寺中老僧紛紛頷首,謝危樓睨一眼謝斐和玉嬤嬤,眸繼而掃過一院子歪七扭八的僧人,“既然下藥之人已經查明,便請大師將諸位師父好生安置,莫要驚擾寺其他眷。出了這個院子,任何人不得胡言語,否則,本王定以散播謠言之罪論。”
一旁的監院躬應道:“多謝王爺。”便指揮僧眾將吸過毒煙的和尚帶下去安置。
索眾人中藥不深,念幾個時辰的清心咒也能支撐過去。
此事畢竟發生在自家后山,玉佛寺到底有監察不嚴之責,他們也不想此事鬧大,讓流言蜚語辱沒佛門清凈,鎮北王能出手制再好不過。
待僧人有序退離,院中便只剩謝斐、玉嬤嬤等人,住持方丈朝謝危樓頷首,“王爺家事,貧僧等不便干預,這里還是給您來置吧。”
謝危樓淡淡道了聲“多謝大師”,幾位和尚便陸續離開了。
頭頂的腳步聲漸行漸遠,耳邊靜得仿佛凝滯,沉沉的威勢漫卷而來,玉嬤嬤心中的懼意登時如同水般涌上。
早在二十年前,那位貴人就提醒過,這人不是普通人。
從年時就已經百戰沙場,文治武略都是當世獨一,就連對子教養極其嚴厲的太宗皇帝都十分認可這個年紀最小的兒子,年時的鋒利霸道歷經歲月的砥礪,慢慢沉淀為威冷森嚴的上位者氣勢,他在的地方,令人如墜冰窖。
謝危樓冷冷盯著地上的人,隔了許久,久到玉嬤嬤心臟幾乎停跳,這才緩緩蹲下,仔細審視著被抵在石磚上的右臉,漫不經心地問了一句。
“你知道穢佛門凈地是什麼罪名麼?他是你什麼人,值得你不惜命也要用這種下作手段來幫他,嗯?”
正午日灼熱,黏膩的空氣里有濃郁的腥氣息,可玉嬤嬤卻覺得寒意如同毒蛇般爬上背脊,浸骨髓,一口咬住慌不已的心臟。
什麼,他是你什麼人?
鎮北王府做事這麼多年,玉嬤嬤早已錘煉出一顆強大的心臟,當年作為新府的母面對嚴格的盤問時,保持著足夠的鎮定,甚至屢次與這雙冷戾眸四目相對之時,也從未有過此刻的慌張。
猜你喜歡
-
完結137 章
東宮美人(荔簫)
楚怡穿越成了丞相千金,自問命不錯。第二個月,家就被抄了。第三個月,楚怡以妾侍身份被賜進東宮,-楚怡一看,完犢子,苦難的日子在向她招手。結果觸發的竟然是甜文劇情?
43萬字8 19606 -
完結3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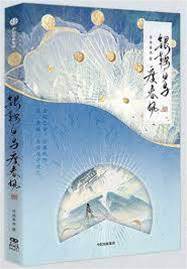
銀鞍白馬度春風
君主剛愎自用,昏庸無能,掩蓋在長安錦繡繁華之下的,是外戚當權,蟻蛀堤穴。 賢仁的太子備受猜忌,腐蠹之輩禍亂朝綱。身爲一國公主,受萬民奉養,亦可濟世救民,也當整頓朝綱。 世人只掃門前雪,我顧他人瓦上霜。這是一個公主奮鬥的故事,也是一羣少年奮鬥的故事。 ** 你該知道,她若掌皇權,與你便再無可能。 我知道。 你就不會,心有不甘嗎? 無妨,待我助她成一世功業,他日史書之上,我們的名字必相去不遠。如此,也算相守了。
55.4萬字8 1872 -
完結156 章

東宮奪歡
崔歲歡是東宮一個微不足道的宮女,為了太子的性命代發修行。她不奢望得到什麼份位,隻希望守護恩人平安一世。豈料,二皇子突然闖入清淨的佛堂,將她推入深淵。一夜合歡,清白既失,她染上了情毒,也失去了守望那個人的資格。每到七日毒發之時,那可惡的賊人就把她壓在身下,肆意掠奪。“到底是我好,還是太子好?”
28.1萬字8.18 7428 -
完結258 章

燈花笑
陸瞳上山學醫七年,歸鄉後發現物是人非。 長姐為人所害,香消玉殞, 兄長身陷囹圄,含冤九泉; 老父上京鳴冤,路遇水禍, 母親一夜瘋癲,焚於火中。 陸瞳收拾收拾醫箱,殺上京洲。 欠債還錢,殺人償命! 若無判官,我為閻羅! * 京中世宦家族接連出事, 殿前司指揮使裴雲暎暗中調查此事, 仁心醫館的醫女成了他的懷疑物件。 不過...... 沒等他找到證據, 那姑娘先對他動手了。 * 瘋批醫女x心機指揮使,日
96萬字8.33 637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