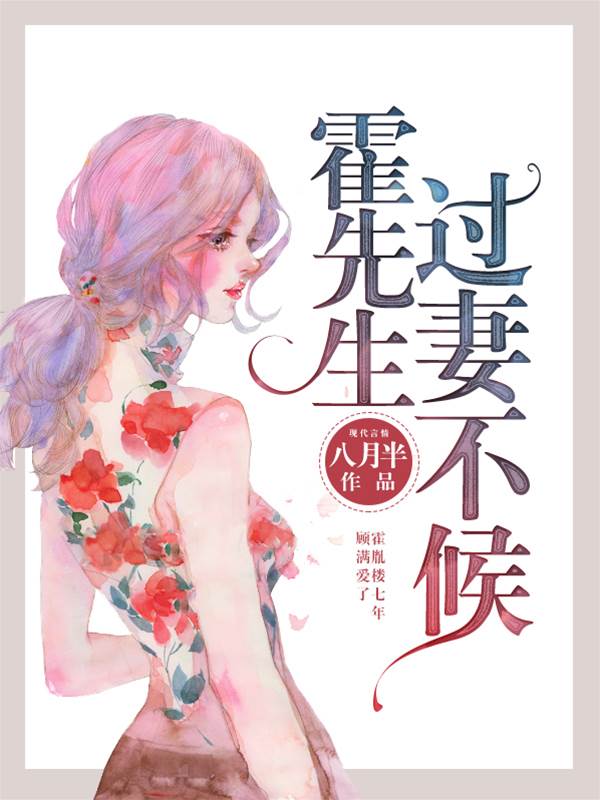《杳杳歸霽》 第17章 奶鹽
里有酒, 他落下來的氣息里也有,蘇稚杳頭腦郁郁沉沉, 閉著眼睛呼吸, 更暈了幾分。
蘇稚杳就沒怎麼喝過酒。
頭回還是小時候頑皮,喝媽媽釀的梅子酒,不懂事, 酒嘬了不, 還吃掉半罐梅子,在酒窖睡得四仰八叉,最后了涼,反復高燒半個月,家里就把酒窖鎖起來,不許再靠近。
蘇稚杳那時候委屈, 天天躺床上難不說,還得頓頓喝苦藥, 哭得上氣不接下氣。
媽媽總會著頭, 溫地說:“我們杳杳是世界上最乖的小寶貝,喝完藥明天就能活蹦跳了。”
那次退燒后,如同落下病, 養了一燒起來就不易退的質。
第二回喝酒就是現在。
兩杯高度特調,足以到極限, 醉到這程度, 聽覺約,思考和理解能力近乎喪失。
耳朵里的嗡鳴聲中,有他不可言喻的一句, “別的男人”。
眼皮沉沉的, 蘇稚杳瞇開一條, 努力思考他的意思,也不曉得懂沒懂。
腦袋一歪,渲開笑臉。
“你最好——”
拖著滴滴的語調,像拉的棉花糖。
賀司嶼深了眸,淡不可聞地一哂。
敷衍他。
“冷……”蘇稚杳慘兮兮,圈住他腰的胳膊慢慢勾,人往他前湊。
半張臉還沉在他一只手心里,這姿勢,像是被他托起下調.教。
而無比乖順。
沒得到回應,又重復了遍,語氣得不樣子:“賀司嶼,我冷。”
賀司嶼不自覺松了指勁。
蘇稚杳趁虛,一下鉆進去他懷里。
再回神,這姑娘已經把自己連子帶腦袋,全都裹進他的大里取暖了,跟只藏起來的小袋鼠似的。
賀司嶼幾經想拎開,手都抬到發頂了,卻是沒再像前兩回那麼果斷,思來想去,心放過了。
他給徐界電話,司機把車開到湖邊。
手機剛從耳邊放下去,聽見黏抱著他的姑娘發出哼嗚的聲音,不知道在嘀咕什麼。
賀司嶼低下頭,耳畔靠近。
依稀聽明白,嗚嗚嗚的,是在哭肚子。
賀司嶼翹了下。
空腹就敢上酒吧這麼喝,到底是個涉世未深的小姑娘。
他故作冷淡地吐出一個字:“該。”
“你又兇我……”蘇稚杳悶聲控訴,就要哭給他看的語氣,隨后不高興地哼了聲,突然張,往他膛“啊嗚”咬了一口。
沒咬著他,咬了一馬甲的呢面布料。
蘇稚杳那時候醉糊涂了,肆意妄為,哪還管得著他是不是那個讓人聞風喪膽的大老板,一口沒咬到,不死心地往別繼續咬。
一連好幾口下去,從馬甲咬到襯衫領。
個子不夠高,扯住他領子,借力踮腳,.一徑往上走,一下啃著了他下。
“嘶……”賀司嶼皺眉,頭抬到夠不著的高度,避開啃的牙齒。
結果仰起的脖子暴在了面前。
蘇稚杳眼前是重影,神志不清,雙手想也不想地攀上去,抱住他脖子,朝他的脖頸一口咬下去。
“啊嗚——”
牙齒磕到一塊凸,下意識牢牢叼住。
回應的是男人一聲沙啞難抑的悶哼。
在靜謐無人的黑暗里,這樣的聲音算不上清白,聽得人臉紅心跳,牽引著浮想出一幕幕不堪目的畫面。
倏地,湖面有不明源一閃。
賀司嶼當時闔了雙眸,電流從結到神經末梢,刺.激得他猛地揚起頭。
那陣麻一過去,他立刻掐住兩腮,迫使松開牙齒。
命門被扼住的覺退去,賀司嶼重重一,結敏.地不停上下滾,幸虧孩子的咬合力較輕,造不傷害。
但也讓他短暫呼吸困難,異常沸騰,支配與臣服倒錯,介于窒息和之間。
賀司嶼深幾下緩過氣息,手加重了力道掐下,一把抬高,沉的臉近,嗓音剛過激,嘶啞得厲害:“再咬?”
蘇稚杳被得雙嘟起,話出聲含糊不清,像小魚吐泡泡,全了嗚咽。
可能是他聲線太冷,惡狠狠的聽著嚇人,也可能是臉被他掐痛了,蘇稚杳眼眶頓時濡了一圈,仿佛下一秒就要哭出來。
賀司嶼蹙眉,撤開桎梏。
他一松手,的哭腔就溢了出來,嚶一聲埋下頭去,胳膊也從他頸后下來。
模樣委屈得,倒他欺負人了。
司機開著車不知何時已經停在路邊。
賀司嶼不再兇,孩子發酒瘋足夠麻煩了,弄哭了更棘手,他呼吸還留有不穩的低,語氣放平和:“乖了沒有?”
“嗯……”
悶著鼻音,肩膀微,犯錯后很是溫順,他的不悅也就無從發作了。
“上車。”他說。
蘇稚杳再“嗯”一聲,懵里懵懂地蹲下去,撿起手機抱在懷里,站回起時酒勁一沖,又撲了他個滿懷。
賀司嶼嘆氣,撈過雙.,一把抱起。
今晚對,他自認是用盡了好脾氣。
徐界和司機都愕然了,從車里的角度看,這兩人完全是在耳鬢廝磨,尤其他們上司親自抱著人坐進車里后,第一句話就是“暖氣調高”。
“先生,是先送蘇小姐回家,還是……”
徐界想說是否要去國貿開間房,上流圈男歡.就那麼回事,老板再清心寡,調到了這地步,也不可能沒有生理反應。
座椅放平,蘇稚杳上蓋著男人的大,剛躺下時還聲氣地哼著聲,一暖和起來,沒兩分鐘就睡著了。
總算是不再鬧騰。
賀司嶼了眉心,考慮片刻,說:“梵璽。”
睡著前死活不要回蘇家,他再絕,也不可能把醉到不省人事的孩子一個人丟在酒店。
徐界怔住兩秒,忙不迭回答明白。
前段時間因京市行程頻繁,為便他在寸土寸金的梵璽大廈置辦了一套頂層住宅。
別說那里他自己都還沒住過幾回,就是在常居的港區別墅,這麼多年徐界也沒見他帶任何回去過。
徐界回首答話時,余下意識留意了眼后座的姑娘。
躺著眠,男士商務大掖到肩頭。
俗話說英雄難過人關,徐界頭一回覺到,他這六清靜的上司,有正常的活人氣。
但沒必要大驚小怪。
他也是男人,是男人就不能免俗。
車子暢通無阻,一直開到梵璽。
大廈最頂部整整一層,都屬于賀司嶼套房的獨.立空間。
房門打開,廊道至客廳的燈帶自亮起。
賀司嶼抱著蘇稚杳,把人放到沙發,孩子重量輕得很,他氣都沒一下。
蘇稚杳睡得也深,一路被抱上來都沒醒。
賀司嶼居高臨下看著,下西服外套,解掉襯衫袖扣,丟在一旁,開始挽袖子。
上輩子一定是欠了什麼。
否則他不會把一個喝醉的人帶回住,現在還得親自去客臥給鋪被套。
賀司嶼前腳剛踏進客臥,后一秒,蘇稚杳迷迷糊糊轉醒,明亮的水晶吊燈灼得睜不開眼。
酒意仍上頭,蘇稚杳并沒有清醒,著眼睛,慢慢坐起來,不舒服地蹬掉靴子。
半夢半醒的狀態下,赤腳踩上地毯,夢游似的,從客臥門口一而過,尋著味,推開另一間臥室的門,無聲無息飄了進去。
等賀司嶼再出來,想抱去客臥時,沙發上空空無人,只有他的大一半歪著,一半拖地。
一圈都沒看見人。
直到他目落到主臥虛掩著的門上。
賀司嶼皺眉,朝著主臥過去。
門口過渡廳的燈亮起,線延.進寬闊的臥室里,逐漸暗沉下來。
遠遠看去,鉛灰被褥下鼓起一團。
賀司嶼一步一步輕輕走到床邊。
果不其然,這姑娘正舒坦地躺在他的床上,雙手住被子蓋到鎖骨,只出一顆漂亮的腦袋,和一點彎曲著的白里暈的指尖。
溫馴地闔著雙眼,睫很長,.潤地覆在眼瞼,睡安安靜靜。
即便是他也不可否認,畫面十分養.眼。
真是會挑地方睡。
賀司嶼扯了下,呵出一聲無奈的氣笑。
他俯,從手指頭里出那一截被沿,被子往上輕拽,蓋過肩頭。
正要起,胳膊突然被抱住。
蘇稚杳臉蹭蹭他小臂,眉眼舒展開,睡夢中愉悅呢.喃:“香香……”
“不準咬。”賀司嶼下臉警告。
不知是聽進去了話,還是又睡過去,下的人倒是安分了會兒,沒再蹭,只是雙微微翕,發出模糊的聲音。
因高,這麼躬著不舒服,賀司嶼不得不在床沿坐下,依稀聽清話:“賀司嶼……都不加我微信……”
“說過了,我不用微信。”他隨口應了句。
猜你喜歡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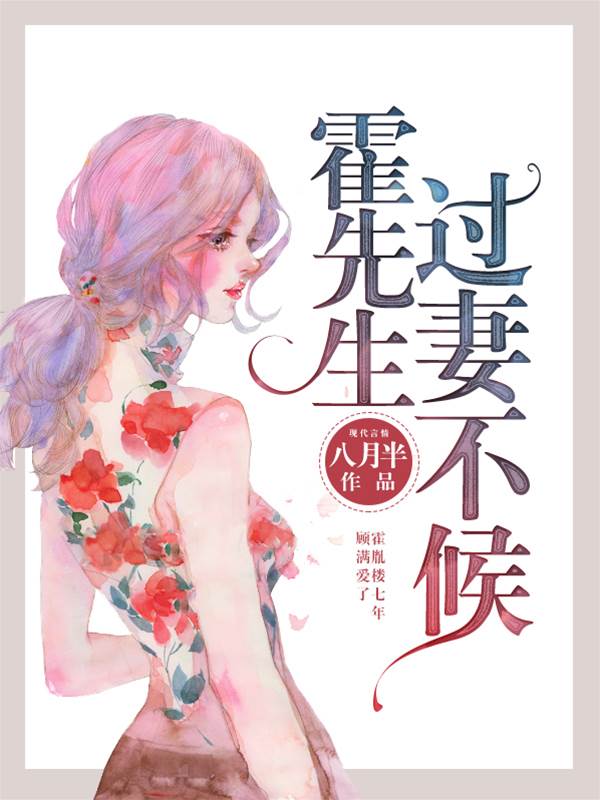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3312 -
完結283 章

獨占偏寵
葉奚不拍吻戲,在圈內已不是秘密。一次頒獎典禮上,剛提名最佳女主角的葉奚突然被主持人cue到。“葉女神快三年沒拍過吻戲了,今天必須得給我們個交代。”面對現場追問,葉奚眼神溫涼:“以前被瘋狗咬過,怕傳染給男演員。”眾人聽後不禁莞爾。鏡頭一轉來到前排,主持人故作委屈地問:“秦導,你信嗎?”向來高冷寡言的男人,笑的漫不經心:“女神說什麼,那就是什麼吧。”*人美歌甜頂流女神VS才華橫溢深情導演。*本文又名《返場熱戀》,破鏡重圓梗,男女主互為初戀。*年齡差五歲。*男主導演界顏值天花板,不接受反駁。
52.6萬字8.18 6384 -
連載372 章

少帥既然不娶,我嫁人你哭什麼
楚伯承像美麗的劇毒,明明致命,卻又讓人忍不住去靠近。可他們的關系,卻不為世俗所容。姜止試圖壓抑感情,不成想一朝放縱,陷入他的牢籠。他步步緊逼,她節節敗退。一場禁
66.8萬字8.18 18832 -
完結507 章

離不掉!高冷佛子為我墜神壇
【追妻火葬場 雙潔 假白月光 虐男主 打臉發瘋爽文】“離婚吧。”傅樾川輕描淡寫道,阮棠手裏還拿著沒來得及給他看的孕檢通知單。整整四年,阮棠把自己活成一個笑話。一場車禍,阮棠撞到腦子,記憶停在18歲,停在還沒愛上傅樾川的時候。麵對男人冷酷的嘴臉,阮棠表示:愛誰誰,反正這個戀愛腦她不當!-傅樾川薄情寡性,矜貴倨傲,沒把任何人放在心裏。阮棠說不愛他時,他隻當她在作妖,總有一天會像從前那樣,哭著求他回頭。可他等啊等啊,卻等來了阮棠和一堆小鮮肉的花邊新聞。傅樾川終於慌了,將人堵在機場的衛生間裏,掐著她細腰,聲音顫抖。“寶寶,能不能……能不能不離婚?”
88.1萬字8.18 1843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