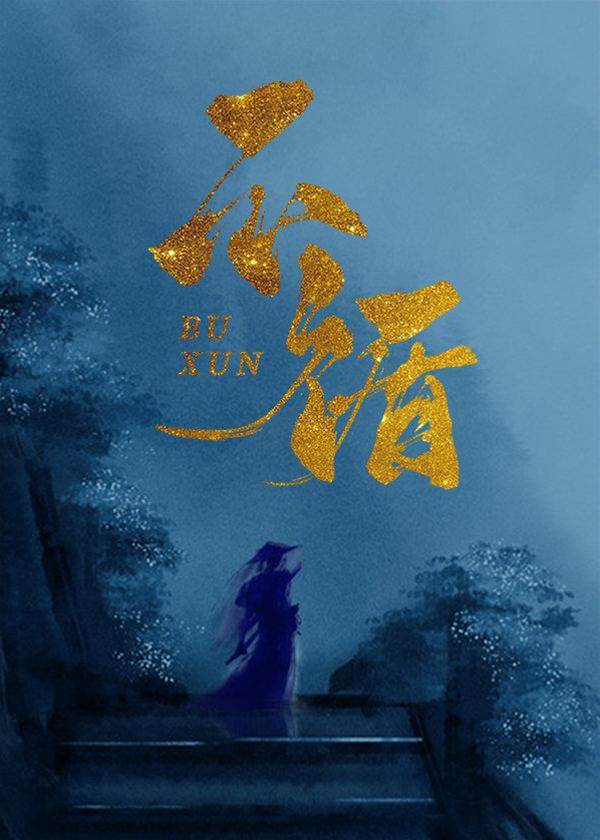《我心昭昭》 第五十二章 重雲蔽日1
孩子睡得一張小臉白裏紅。他以為對很悉了,可每回看到的臉,還是會,心裏還是會不由主地充滿他都覺得陌生的。他的手不自地出去,想一那明豔,可剛到胳膊,就醒了。
清辭睡眼朦朧間看到了蕭煦,立刻清醒過來,“大哥哥。”然後注意到自己在外頭的手臂,兩腮紅意更盛,慌得去解襻膊。可越急越解不開,抬起手臂時,那胳膊得也越多。
蕭煦鬼使神差地俯去幫解襻膊,目所及之,一片雪白玉潤的。想起小時候也總是解不開繩結,他那時是不肯靠近人的,自然也不會幫。解得一肚子火氣,最後還是要剪子。那襻膊上便有了許多的結。這時候,他才恍然覺察,“繩千結絆人深”,那死結早結在了他心上。
結扣終於解開了,清辭低著頭把袖子理好,也將那玉藕似的手臂遮藏住。似是不習慣他這樣親近,清辭斜避著,“大”字剛出口,又變了,照規矩向他行禮,“奴婢見過陛下。”
這疏離的客氣規矩,他心底那一掃而。到底是如今大了,懂得了男大防,還是,生分了?
蕭煦直起,一手負在後,聲音也冷了下來,“免禮,平吧。”
“謝陛下。”
清辭說完這些,心裏既替他歡喜,心頭又籠著淡淡的哀愁。清楚地明白,那個大哥哥,可能再也沒有了。不懂謀略權,可因為比旁人讀過更多的史書,所以明白,一個帝王是不可以被輕慢的,不管是誰。
蕭煦坐下,“看我給你帶什麽來了?”然後拍了下手,有侍抱著什麽東西垂首進來。清辭一看,竟然是的貓。
“二敏!”
清辭欣喜得忘了禮數,上前去把貓抱進懷裏。二敏已經是一隻極老的貓了,因為懶怠,又長胖了許多,抱在懷裏沉甸甸的。二敏很快就認出了主人,“喵”了一聲,了,又放鬆地窩在懷裏了。
蕭煦終於在的臉上看到了曾經的模樣。看著抱貓的樣子,一恍惚,仿佛又回到澹園。那時候,他是個“瞎子”,隻能對著“視而不見”,但現在,他可以肆意地著。
似乎覺到了他的視線,清辭覺察到自己失態,忙斂起粲然的笑,無措得不知道是該向一個帝王求恕失儀之罪,還是該向大哥哥撒,但卻是發自心道:“謝謝——”頓了頓,還是道:“陛下。”
“以後沒有外人在,朕還是你的大哥哥。”
清辭莞爾,“嗯”了一聲,“大哥哥,你為什麽把二敏帶進宮給我?”
“你不是想它嗎?聽說,你剛進宮的時候,想貓想得掉眼淚。”
清辭訝異極了,大哥哥怎麽什麽都知道。
“你在澹園用慣的那些東西,我也會人給你送過來。”
清辭臉上閃過愕然,咬了咬。
“怎麽?”
“我反正是要回去的呀,不用費事搬來搬去的。”低聲道。
“不是說好了要陪著大哥哥嗎,怎麽,改了主意?”
清辭被他問得有點慌,“不是的。大哥哥,我進蓮溪寺前,已經從宮策裏除了名字。我已經不是宮裏人了呀,自然要回澹園的。”
“這是什麽難事嗎?”他笑問。
可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小栗子了啊,也有自己的人生;他亦不是當初落魄年,他是九武至尊,是大周萬民的君父,是這後宮萬千子的唯一的男人。也聽說了,新帝登基,清流一派厥功至偉。鄭太後為蕭煦廣選名門淑,充盈後宮。甚至看到了清玥的名字……
他們今日咫尺對麵,可早已是非異,山川難越了。但不知道怎麽跟他說,說出來,像是背叛了他一樣。
借貓的作垂下眼,掩了心緒,“大哥哥,你現在是皇帝了,可不可以把紀家的書送回澹園?”
蕭煦心頭驟冷。還是想離開他,從什麽時候起,已經不再像從前那樣全然依他?旁的人和,早已經占據了的心,讓他變得無足輕重了嗎?
“雖然我是皇帝,但也不能為所為啊。那書是先帝要留存文祿閣的。我剛繼承大統,若把書送出去,那些翰林史們會怎樣說我?你也知道,那些書是文人的命。小栗子,你也不會讓大哥哥為難,讓大哥哥背上不孝的罵名,對不對?”
見神微變,他的聲音卻越發溫起來,“那些書就在文祿閣裏,你想看哪本,想抄哪本,朕會司禮監發準條腰牌給你,你可以隨意出。”
貓的手停了下來,臉上滿是濃濃的失落,既不點頭也不搖頭,隻是咬著不說話。
“往後,待朕得空了,允你去挑選工人宮,一起幫你摹寫影刻,這樣朕既不會落人口實,你對三叔公也能有所代。如何?”他不知道自己哪裏來的耐,這樣哄騙一個人。
清辭默不作聲,氣氛有些冷。但他最知道如何拿的心緒。
外頭響起侍的聲音:“陛下,時辰不早了,該回宮了。”
“候著。”
那應諾便不再出聲。
“大哥哥,你有事就先回去吧。”
蕭煦微微一笑,拍了拍邊的位置,示意坐過來。“不急。你上次不是想問小火的事嗎?”
清辭抬起頭,果然神了。
“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說。”
清辭這才抱著貓緩步走過去,在他邊坐下,卻也隻是虛坐著,留著餘地。他不喜歡這種覺,又想,或許因為他如今是皇帝,對他也產生了畏懼。
清辭一直等著,過了半晌方才聽他道:“皇貴妃和小火,意圖毒殺父皇,假造聖旨,被發現了。”
“假造,聖旨……?”
清辭的手在袖子底下狠狠掐著自己的手指,努力不失態,可聲音還是有些抖,“怎麽會,被發現的?”然後忽然意識到失言,又忙改口:“是怎麽發現的?”
蕭煦佯作沒發現的異常,“原來父皇已經寫好傳位給我的詔書,兩份詔書同時出現,難辨真偽,不過最後還是翰林院的幾個老翰林給辨出來了。”
“怎,怎麽辨認真偽的呢?”
“小火的名,那個‘焎’字。父皇寫‘焎’字時,會將‘斤’的那一豎與第三點相連。但傳位給小火的詔書上,這個‘焎’字——”
他想了想,“太匠氣。怕是出於高超的摹寫之手。接著,太醫又發現父皇其實是中毒而亡。端景宮的一個宮人到大理寺去狀告皇貴妃投毒,而那毒藥,就混在王芣的胭脂裏。王芣還曾把這胭脂賜給過惠嬪,說是父皇極的東西,伴駕時用。那毒藥當時不會斃命,但天長日久——”
他不再說下去,隻見得清辭的臉白得沒有一點。他關切地問:“小栗子,你怎麽了?”
清辭的了,眼眶漲得難,“大哥哥,你不要殺小火哥哥好不好?”
“放心,大哥哥不是會手足相殘的人,可我也必須堵上朝廷裏的幽幽眾口,隻得將他廢為庶人。皇貴妃、小火、阿嫣,雖然都是庶人,但我仍舊允他們住在宮裏。我聽說你在宮裏時,小火對你很好。你放心,我不會為難他的。”
清辭點點頭,心裏早掀起了驚濤駭浪。小火被害慘了,怎麽對得起小火啊?
看不說話,蕭煦又問:“國事繁忙,也不能日日來看你,還有什麽要問大哥哥嗎?”
他想,若開口問韓昭,那麽說明心中坦;但若不問他,私下裏去打聽,那麽便是心裏有鬼。他在這件事上,真正與先皇心意相通:自己的東西,可以賞人、可以拋棄、可以毀滅,但不可以被覬覦,更不允許背叛。
他雖然一直知道同韓昭的事,也知道兩人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但他一直以為,一切不過是韓昭見起意,自小無人寵,所以才貪別人的好。他長久不在邊,才讓韓昭有機可乘。他能原諒一時糊塗的意迷。他從來都沒想過,他們是兩相悅。
怎麽敢心悅別人?!
清辭想問一問韓昭,可因為知道大哥哥不喜歡自己和韓昭在一起,那貿然問他,豈不是惹他不快?
抿了抿,微微牽了一個笑,“沒有,我沒有要問的……大哥哥,太晚了,你也早點歇息吧。”
蕭煦眉頭幾不可見地蹙了一下,點點頭離開了綏繡宮,心裏卻騰起難以名狀的慍怒。
隨侍的太監跟著,小心道:“陛下,從宮外尋的養鳥人已經把姑娘的鳥給治好了,奴才明天就人給姑娘送來。”
那鳥,他知道是韓昭送的,若珍寶,走時給了蕭嫣,他回來後就人把鳥給要回來了。因為疏於照料,那鳥病得很重,這才派人去尋人給鳥治病。
此時忽然想起那回太監拎了鳥來時,那鳥雖病懨懨的,說話的聲音卻十分清晰。“臭韓昭,臭韓昭。”兒家的聲被那鳥兒模仿得十十,讓人能想見孩逗弄鳥兒時嗔喚郎的態……
猜你喜歡
-
連載771 章

心有瑤光楚君意
陸瑤重生後,有兩個心願,一是護陸家無虞,二是暗中相助上一世虧欠了的楚王。 一不小心竟成了楚王妃,洞房花燭夜,楚王問小嬌妻:“有多愛我?” 陸瑤諂媚:“活一天,愛一天。” 楚王搖頭:“愛一天,活一天。” 陸瑤:“……” 你家有皇位要繼承,你說什麼都對。 婚前的陸瑤,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未來的皇帝老子楚王。 婚前的楚王,奸臣邪佞說殺就殺,皇帝老爹說懟就懟。 婚後的楚王扒著門縫低喊:“瑤瑤開門,你是我的小心肝!” 眾大臣:臉呢? 楚王:本王要臉?不存在的!
114.1萬字8 7671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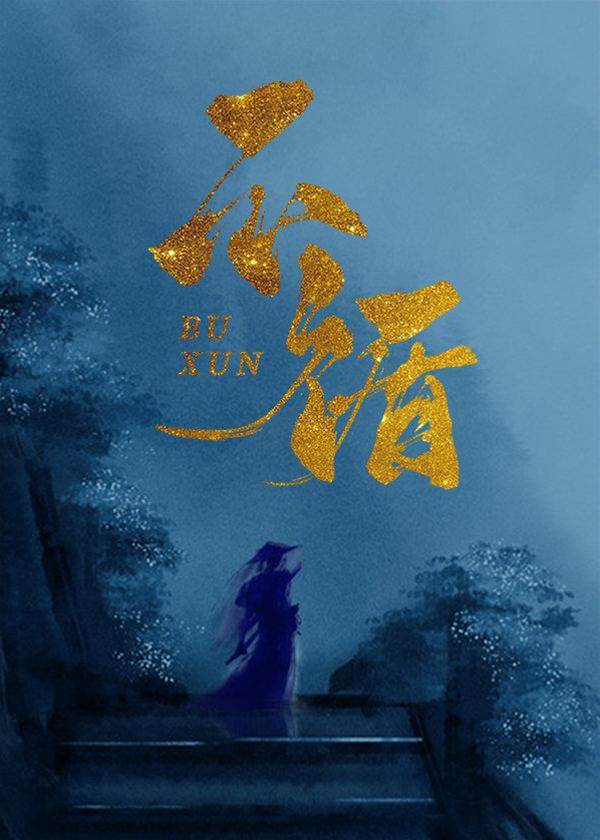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4584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